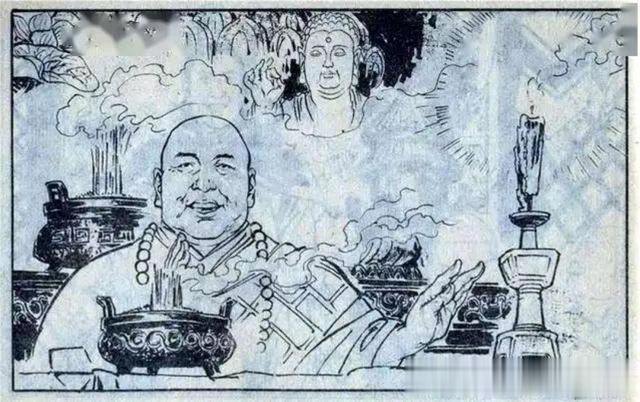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向来以“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著称,而《顾生》一篇,却以一场眼疾为引,编织出一场超现实的时空迷局。
江南顾生的一场眼疾,竟让他闭目即入幻境,睁眼已历百年。红毡铺地的巨宅、转瞬老去的王子、婴儿与老妇的诡谲交替,短短一梦间,生死荣枯尽显。这不仅是志怪小说中的奇谭,更是一则关于时间、存在与虚妄的哲学寓言。

顾生客居济南时突患眼疾,疼痛难忍。十余日后,每当他闭目,眼前便浮现一座巨宅,门庭洞开,人影绰绰。这看似寻常的病症,实为通往异界的“钥匙”。生理的痛苦与精神的幻视,在此形成诡异的共振。
顾生入幻境后,受邀参加九王世子的庆宴。席间鼓乐喧天,演《华封祝》三折,现实中却仅是一顿午餐的时间。当他重返幻境时,王子已从少年变为“颔下添髭尺余”的老者,戏目已过七折。宴席上的推杯换盏,实为时间的加速器。学者吴九成指出,这种“一宴百年”的设定,暗合了“黄粱一梦”的东方时间哲学,将人生的须臾与永恒压缩于一场病中幻境。
幻境中,顾生初见满屋婴儿,再返时却见“数十媪蓬首驼背”。蒲松龄以极简笔墨,勾勒出生命从初生至衰朽的瞬间蜕变。婴儿的纯真与老妇的衰颓,恰似时间洪流中不可逆转的宿命。这种对比,令人联想到《庄子·齐物论》中“方生方死”的辩证——存在与消亡本是一体两面。

顾生的幻境并非全然虚幻:眼疾痊愈后,他的现实与梦境彻底割裂,但幻境中的经历却治愈了肉体之痛。这种“以幻治实”的手法,暗示了精神世界对现实的反向塑造力。
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提出,“梦境是灵魂的居所”,而蒲松龄早在三百年前便以文学实践呼应了这一观点。
宴席中“三折戏文”对应现实中的“一瞬”,王子须发骤长,婴儿转瞬成妪。蒲松龄以奇幻笔法,揭示了人类对时间的感知不过是主观的幻觉。这与爱因斯坦相对论中“时间膨胀”的物理概念形成跨时空对话——在高速运动的坐标系中,时间流速本就不同。
顾生的眼疾,恰似《红楼梦》中贾瑞的“风月宝鉴”——肉身的痛苦,成为勘破虚妄的媒介。当他在幻境中经历时间错乱后,最终被狗舔油锅的声响惊醒,眼疾痊愈,幻象消散。这种“病愈即悟”的结构,暗含禅宗“破执”的智慧:唯有放下对幻相的执着,方能回归本真。

在效率至上的当代社会,许多人正如顾生般陷入“时间焦虑”:短视频刷过三日,恍如隔世;加班熬夜数年,青丝成雪。蒲松龄的奇幻故事,恰似一记警钟:我们是否也在病态的时间感知中,错失了生命的实相?
顾生最终因“目疾若失”而回归现实,暗合佛家“烦恼即菩提”的顿悟。正如六祖惠能所言:“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当我们停止追逐幻境中的华宴,或许才能看见窗前真实的月光。
《顾生》的结尾,狗舔油锅的声响打破幻境,一切归于平静。这令人想起《金刚经》的偈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蒲松龄以志怪之笔,写尽浮生虚妄,却也在故事尽头留下一线光明:唯有直面现实之粗粝,方能超越时空之桎梏。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该如顾生般,在睁眼闭眼的刹那芳华间,学会与时间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