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希腊与齐国的医术交辉
公元前400年,希腊科斯岛上的希波克拉底忙着给病人治病。他手里攥着一把青铜医刀,刀刃闪着冷光,对准一个抑郁症患者的手臂轻轻一划,皮肤破开后,黑乎乎的血就顺着刀口慢慢淌出来。血流得不快,但每次放血都得持续好一会儿,地上很快就积了一小摊。
他身边放着几个陶罐,专门用来接这些血,罐子边缘还有些干涸的血迹。希波克拉底一边操作,一边盯着血的颜色,时不时皱眉观察。他信奉的是“四体液学说”,觉得人身体里有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四种东西,哪样多了少了都不行。

这回他认定患者抑郁是因为黑胆汁太多了,得放点出来才能恢复平衡。刀子划完,他用一块粗布擦擦手,然后拿来一块亚麻布给患者裹上伤口,动作熟练得很。患者坐在那儿,脸色本来就不好,放完血后更白了,走路都得扶着东西,腿软得站不稳。
可惜这法子没啥用,病人不仅没好起来,反而越来越虚弱,身上没力气,连日常干活都费劲。时间一长,脸瘦得跟骷髅似的,眼窝深陷,皮肤干巴巴的,村里人见了都绕着走,觉得这人怪得很。有些地方甚至传出闲话,说这种模样是被神诅咒了,搞得患者出门都不敢抬头,日子过得孤零零的。

希波克拉底这边忙着放血放得不亦乐乎,手底下已经治了好几十个这样的病人,用的工具还是那几把刀,每次用完就拿水冲冲,晒干接着用。他还记下每次放血的时间和血量,说是要研究规律,可病人还是一个接一个地虚下去。
与此同时,远在两千公里外的齐国王宫里,医者文挚正琢磨着怎么治齐闵王的抑郁症。齐闵王这阵子被国事烦得够呛,整天吃不好睡不香,宫里的人都说他脾气越来越怪,连朝会都不愿去了。
文挚的怒疗奇招
公元前291年,齐国临淄的王宫里,医者文挚开始了他那套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治病法子。齐闵王那段时间正被国事烦得焦头烂额,整个人像是被堵住了气,整天吃不下饭,脾气也越来越怪,连宫里伺候的人都得小心翼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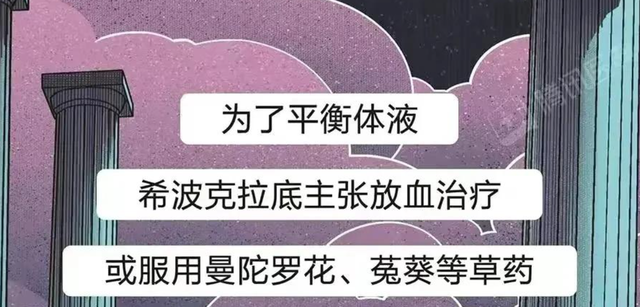
文挚奉命来治他的抑郁症,可他没带药也没带工具,倒是先干了件出格的事。他跟齐王约好见面,结果连着三次都没去。第一次约在早上,齐王等了一上午没见人影,派人去问,文挚就说有事走不开。第二天又约在中午,还是没来,宫里的侍卫跑了好几趟,文挚还是那句话,应付着打发走人。到了第三次,他干脆连个理由都不给了,直接放了齐王的鸽子。齐王这下可忍不了了,气得让人把文挚硬拖进宫。
文挚总算来了,脚上踩着一双脏鞋,鞋底满是黑泥,裤腿上还挂着几块干土。他也不管宫里那铺着厚锦缎的床多干净,直接一脚踩上去,鞋印子清清楚楚留在上面,旁边站着的侍卫都看傻了。齐王气得跳起来,指着他鼻子骂了半天,嗓子喊得都沙哑了,满屋子都能听见他的吼声。

文挚呢,也不吭声,等齐王骂够了才慢悠悠起身,抖了抖衣服上的灰,拄着根木杖走了出去。结果没几天,宫里就传出消息,齐王居然缓过来了,饭也吃得下了,朝会也开始正常上了,处理政事的时候眼神都亮了不少。
文挚这招是看准了“怒胜思”的道理,觉得人要是发一通火,那股郁闷劲儿就憋不住了,非得跑出来不可。他随身带着一卷竹简,上面写满了这种医理,平时没事就翻翻看看。这法子虽说最后把他自己搭进去了,因为齐王事后想想还是咽不下这口气,把他给砍了,但这事在中医史上可留下了名。
越鞠丸的丝路传奇
中世纪的时候,波斯湾的港口老热闹了,商船来来往往,拉着各种货,其中就有中国的越鞠丸。这药是个褐色的小丸子,拿香附、川芎、神曲这些药材磨成粉做出来的,专治那种胸口堵得慌、喘不上气的郁症。

商船到了港口,卸下一箱箱木盒子,里面装满了这种药丸,盒子上还贴着红纸条,写着药名和用法。当地阿拉伯医者一看这东西挺靠谱,拿回去研究了几天,决定加点自己的料。他们找来藏红花,碾碎了掺进药里,颜色变得红亮亮的,味道也多了点香气,觉得这样更适合当地燥热的天和病人多汗的情况。
改良完的越鞠丸传开后,沿着丝绸之路往西走,卖到了好多地方,商队里的人都把它当宝贝疙瘩,路上还得小心护着,别让颠坏了。这药的发明者是朱丹溪,金元四大家之一,他在义乌赤岸镇开了个小医馆,常年给人看病。

他那儿病人不少,有回一个男巡按跑来,说自己老觉得胸闷气短,朱丹溪瞅了他几眼,也不问太多,直接说他是月经不调。这话一出口,巡按愣了愣,然后哈哈大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足足笑了一个多月,病还真好了,之后逢人就讲这事。朱丹溪平时不光治病,还爱写东西,他在《格致余论》里提出个“相火论”,说人要是情绪乱了,肝火憋着不动,脏腑就得跟着遭殃,得想法子疏通才行。这书用竹简抄了好几份,传到各地医馆,大家伙儿看了都觉得有道理。
康熙朝的医道交融
1693年,紫禁城里康熙帝病得挺重,疟疾一来就烧得他躺床上起不来。宫里忙得乱成一团,太医们围着转,法国传教士也跑来凑热闹。他们带来一小包金鸡纳霜,用白纸包着,纸上还写着拉丁文用法,摆在康熙的案头上,说这东西能退烧。

太医院那边也没闲着,拿出一盒越鞠丸搁旁边,盒子是木头做的,里面整整齐齐码着褐色小药丸,每颗都用蜜裹过,闻着有点香附味儿。这两样东西摆一块儿,一个是西洋来的,一个是自家制的,看着就挺有意思。
那时候欧洲治抑郁症还挺吓人,他们觉得人是“恶魔附体”,得拿烙铁烫,把那股邪气逼出来。烙铁烧得红彤彤的,病人身上烫出一块块黑印子,疼得直哼哼,可病还是没好,反而更虚了。清朝这边可没这么野蛮,太医们早学会了“五志相胜”的法子,用情绪治情绪,省力又管用。御医顾世澄就在《疡医大全》里记了个事儿,说有个王妃因为儿子死了,天天哭得饭都吃不下,整个人瘦得只剩骨头。
太医琢磨了几天,决定试试惊吓的招儿。他让人找了个大瓷瓶,青花纹的那种,平时装水用的,趁王妃睡着时,让侍女故意摔地上。瓶子碎了一地,哗啦一声响,王妃直接从床上蹦起来,愣了半天才缓过神。之后几天,她那股悲劲儿居然慢慢散了,能吃东西了,脸色也好看了不少。
上海租界的市井智慧
19世纪末,上海租界里热闹得很,豫园茶馆里天天挤满了人。传教士合信跑那儿喝茶时,发现一件新鲜事,写进了《西医略论》。茶馆里有个说书人,嗓子洪亮,手里拿块醒木,讲《三国演义》讲得活灵活现。底下坐着一圈茶客,有几个是抑郁症患者,平时走路都没劲,来了这儿就盯着听。

说书人讲到关羽温酒斩华雄,醒木一拍,讲他怎么一刀下去血溅三尺,茶客们就鼓掌叫好。讲到诸葛亮草船借箭,七百只船趁雾天划出去,回来时箭插满船身,大家伙儿又笑得拍桌子。这些病人听着听着,脸色慢慢变红润了,坐直了身子,有些还跟着哼几句。合信记下来,说这比他知道的西医法子早多了,弗洛伊德那套精神分析到1890年代才搞出来,这儿早半个世纪就有了。
他还写了个例子,有个商人病了好几年,生意也不做了,天天在家躺着,家人没办法就带他来听书。说书人连讲了三天,从赤壁之战讲到空城计,商人听完第三天,自己站起来,说要去找老朋友喝茶。之后他开始出门走动,跟人聊生意的事儿,精神头完全变了个样。

茶馆里用的桌子都是老木头做的,上面刻着些划痕,茶壶是紫砂的,泡的是龙井,茶客们边喝边听,故事讲完一拨人散了,下一拨又来。说书人每天备好书稿,挑最精彩的段子讲,有些病人听上几次,回家路上脚步都轻快了。这法子不用药也不动刀,就靠故事把人郁闷劲儿带走,合信看了直夸中国人的脑子灵。
逍遥丸的环球之旅
19世纪末,苏州河边的雷允上药铺忙着改良逍遥丸,把老方子改成丝线蜜丸。这药治肝郁脾虚特别管用,药铺的匠人们干活一点不含糊,挑上等的茯苓和白芍,用石臼磨成细粉,再拿蜂蜜裹上,做成一个个小丸子,药效稳,味道也好。以前的逍遥丸容易散,保存不了多久,这回改成蜜丸后,能放上好几个月都不坏。

药铺每天熬蜜时都得盯着火候,蜜熬得太稀裹不住,太稠又太硬,火大了还容易糊,得慢慢熬出金黄色的蜜汁才行。做好后,他们把丸子装进小木盒,盒子上贴红纸条,写着用法和药名,码得整整齐齐。改良后的逍遥丸在国内卖得火,苏州城里的人排队买,连外地商人都跑来进货。后来这药漂洋过海,搭上商船去了欧洲,成了最早出口的中成药之一。
船上装了几百箱,路上颠了一个多月,到了欧洲港口,卸下来就被抢购一空。当地药商拿去卖,病人吃了说胸口不闷了,胃口也好多了,口碑传得挺快。雷允上药铺的匠人们听说后,又加紧赶制了几批,挑最好的药材,连夜磨粉熬蜜,发往海外的货越来越多。那时候欧洲还在用放血和烙铁治抑郁,放血得用刀划开皮,血流一地,烙铁烫得病人皮开肉绽,疼得直叫唤,可病还是没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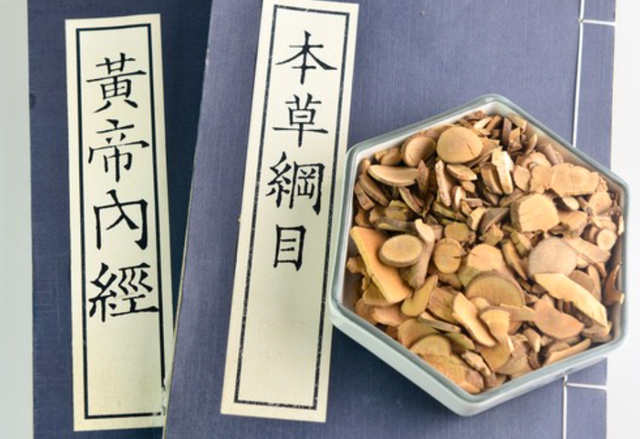
中国这边用逍遥丸,丸子一吃下去,慢慢调理,病人舒坦了不少。药铺还改良了包装,用锡纸裹一层,外头再套个小布袋,防潮又好看,欧洲那边收到货都夸包装讲究。逍遥丸传出去,靠的是真本事,中医的影响也跟着大了,跟西医的粗暴法子比,真是高下立见。
参考资料:[1]刘文臣,刘飞,刘俊丽.中医药治疗卒中后抑郁研究进展[J].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2025,49(1):184-1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