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将的中兴(43)】
【主笔:闲乐生朱晖】
话说公元74年那会儿,东汉王朝又琢磨着把西域这块地界拾掇起来,于是整了个西域都护府。第二年,西边打仗的哥们儿风尘仆仆地回来了,那叫一个风光。可他们一走,嘿,匈奴单于带着车师国的叛军,浩浩荡荡好几万人,又把疏勒城给围了个水泄不通。这一围就是一年,耿恭他们粮食吃光了,救兵也没影儿,最后没办法,连弓弩、铠甲上的筋皮带子都扯下来,煮巴煮巴填肚子。单于一看,这家伙挺倔,想用高官厚禄加美女来诱惑,结果呢,耿恭他们硬是一点儿没动心,死也不投降。可巧不巧,这时候汉明帝驾鹤西游了。按汉朝的规矩,皇上没了,国丧期间谁也不能动弹,更别提发兵了。再加上这皇权交接,乱得跟一锅粥似的,朝廷自己还顾不过来呢,哪还有心思管远在天边的耿恭他们!这样一来,救西域的事儿,自然而然就被扔到一边凉快去了。耿秉、窦固这些大臣心里头那个急啊,可这时候也只能干瞪眼,没辙!
嘿,您猜怎么着?就这么一眨眼,时间溜达到了公元76年的门槛上,疏勒那边还是老样子:北匈奴那帮家伙,脚跟儿钉在地上似的,愣是不挪窝;东汉朝廷答应的救兵呢,也跟玩儿捉迷藏似的,连个影儿都没见着。
难道说,朝廷真的就把这些铁打的汉子、一心为国的中国大兵给晾一边儿去了?是盼着点儿好呢,还是直接死心?是咬牙活下去呢,还是干脆一闭眼算了?耿恭和他那最后几十号汉家兄弟,现在是走到了天涯海角,前无去路,后无退路。除非啊,老天爷开眼,给咱来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公元七十五年腊月里,汉明帝的后事一忙活完,太傅赵熹、太尉牟融、司空第五伦、司徒鲍昱这四位大佬牵头的新一届朝廷班子也搭台唱戏了,洛阳城里头这才算是消停了些。这时候,边疆那点事儿又被翻了出来,汉章帝一招手,把满朝的公卿大臣都叫到一块儿,开起了大会,商量起一件本该二百天前就该扯扯嗓子的事儿——那就是派兵去救西域戊己校尉那俩部队的事儿。
救呢,还是不救?这事儿在朝廷里头可炸了锅,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争得面红耳赤。两拨人意见不合,跟斗鸡似的,谁也不让谁,还都觉得自己那套才是真章,这可把章帝给愁坏了,左右为难啊!
您瞧瞧,以司空第五伦带头的那一拨人啊,他们琢磨着:救那几百号人,跟扔钱打水漂似的,不值当!为了几个生死不明的家伙,再派大军长途跋涉,万里迢迢,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嘛!再说了,都快一年光景了,耿恭、关宠他们啊,八成是见阎王去了。眼下朝廷还得掏大把大把的银子,说不定还得搭上无数条人命,跑到那老鼻子远的地界儿,到头来,救的是人是鬼都不清楚,没准儿是给人家收尸去了!这买卖,咋算咋亏本,您说是不?!
哎哟喂,您瞧瞧,这一年啊,京师洛阳,还有兖州、豫州、徐州那些地界儿,愣是碰上了百年难遇的大旱,整个中原跟翻了个底朝天似的,乱糟糟一片。朝廷忙着给老百姓填肚子还填不过来呢,哪有那多余的银子和闲工夫,去操心西域那边儿那些个芝麻绿豆大的小事?
嘿,您听听这个,校书郎杨终更也开腔了:“皇上啊,咱这些年北打匈奴,西拓三十六国,老百姓是一年到头没完没了地当差,这路上的花费,啧啧,可多了去了。再说那伊吾、楼兰、车师、戊己校尉那地界儿,远的嘞,士兵们想家想得心都快碎了,边境上怨气冲天。您说这日子苦的,老天爷看着都得掉眼泪。皇上您可得好好琢磨琢磨这事儿!”他倒好,营救的事儿提都不提,直接给北伐整个儿亮了红灯,还劝章帝,西域那块儿咱就甭惦记了,回来让大伙儿歇歇脚,养精蓄锐得了!
章帝啊,他跟明帝可不一样,天生的心慈手软,不爱打仗。一听那话,嘿,干脆一拍大腿,说西域咱不玩了!可话说回来,西域那边还有耿恭、关宠那些兵呢,咱也一块儿撤了?得了,这事儿你俩说了算,司空第五伦、司徒鲍昱,你俩官儿最大,好好合计合计,给咱拿个主意吧!

老司空第五伦琢磨着,咱还是别伸手去救了。眼瞅着西域那块地儿咱都不打算要了,何必再去撩拨那帮匈奴爷们儿呢?大伙儿消停过日子,它不香吗?和平万岁,何乐而不为呢?
老五伦啊,这家伙,西汉刚开头那会儿,从齐国溜达到关中来的,田家的后代嘛(因为是第五拨搬家的,就这么姓了“第五”),还真是把老祖宗田齐那套孤家寡人的做派学了个十足。一说到打仗,他就跟躲猫猫似的,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省心得很。再说了,这帮从有钱地方来的儒家官老爷,眼界短得跟豆子似的,心里头就认一个理儿——经济为王。要是啥事儿不能立马换银子回来,就算是保家卫国的钱袋子,他们也觉得那是瞎花。
司徒鲍昱可真是个倔脾气,非得说要救,救定了!他还扯着嗓子说了那么一席贴心窝子的话:“你想啊,把人家搁到那么个凶险的地方,一眨眼就不管了,这不是明摆着让蛮夷那帮家伙更嚣张嘛,咱自家的忠臣烈士也得寒了心。这时候要是不伸手拉一把,万一哪天匈奴又溜达过来捣乱,皇上您上哪儿找忠心耿耿的将领去?再说,那两队人马拢共才几十号人,匈奴围着他们转悠了老鼻子天都没啃下来,这不是明摆着他们人少力薄,但拼尽全力了嘛!”
瞧瞧这个国家,瞅瞅这个政府,要是对那些在战场上拼死拼活的将士们没点心疼劲儿,对那些为了保家卫国打仗的老兵、伤了残了的兵哥哥们,既不关怀也不给点儿实惠,您说,这样的国家还能有啥奔头?还能拢得住人心?大伙儿还能拧成一股绳,一块儿对付难关,抗击外敌吗?
这年头,朝廷咋就狠心把自家的远征猛将晾在一边,不管不顾了呢?这不是明摆着让他们自生自灭嘛!你说,那匈奴胡虏知道了,心里头得怎么想?咱们汉家的全体将士,心里头又能痛快吗?还有那些老百姓,他们能没意见?
国若不疼民,民咋能不爱国呢?鲍昱心里琢磨着,得给那年轻的汉章帝好好说道说道这事儿。你说说,要是国家不把百姓当回事儿,百姓心里还能热乎乎地向着国家吗?鲍昱琢磨着怎么把这理儿给汉章帝讲明白。他得让那小子知道,国家跟百姓,那得是心连着心的,不然,国家可不就成了没根儿的树,摇摇晃晃站不稳嘛!鲍昱打算,今儿个非得用些通俗易懂的话,让汉章帝那脑袋瓜子开窍不可。他得让他明白,国和民,那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谁也别想单蹦跶!
所以嘛,要是西域那儿还剩下一个活着的汉兵,咱们中国说啥也得派人去搭救他!不能让英雄的一腔热血凉了,也不能让将士们那颗红心寒了!这事儿啊,它不单单是划算不划算的小账本问题,而是一个国家得给自己的百姓和子弟兵亮明立场的大事!就算这些英雄们已经为国捐躯了,咱们也得去把他们遗体找回来,把英魂带回家,这样大伙儿心里头才对国家有那份归属感、认同感。这理儿,咱们老祖宗两千年前就琢磨透了!
然后呢,鲍昱这家伙又琢磨出个救西域的妙招,他说:“咱当兵的,讲究的是先声夺人。干脆,让敦煌、酒泉那俩太守,各自带上两千精兵快马,多扯些旗帜,跟飞似的赶路,去给他们解围。匈奴那帮累得跟狗似的兵,哪敢跟咱硬碰硬啊?估摸着,四十天,咱就能凯旋而归了!”
得了,事儿就这么定了,汉章帝最终被鲍昱那一帮子大臣磨得没了脾气,答应出兵去救自家的将士们,不过啊,他那放弃西域的主意还是铁了心不改。紧接着,章帝就打发谒者王蒙和皇甫援俩人,带着圣旨快马加鞭地赶往凉州边境,找那位新上任的征西将军耿秉,让他带兵进驻酒泉,坐那儿指挥大局。随后,章帝又派骑都尉秦彭(这事儿吧,有的史书上说是酒泉太守段彭,有的说是骑都尉秦彭,咱也弄不清谁对谁错)火急火燎地去调集张掖、酒泉、敦煌三郡的六千骑兵,再加上刚归顺咱们大汉的鄯善国的一千胡骑,拢共七千人马,浩浩荡荡往柳中城集合,西域救援大戏这就开场了。王蒙和皇甫援这俩谒者还兼职监军,跟着一块儿去。还有那位耿恭先前派出去求援的小吏范羌,这回也当上了向导,带着大军一块儿上路了。

哎哟喂,东汉那帮大军啊,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没日没夜地赶路,结果呢,等他们第二年,就是公元76年那会儿,正月里风尘仆仆地赶到柳中城城根儿底下,嘿,黄花菜都凉了!您猜怎么着?匈奴跟车师那联军,早一个月前就手拉手把柳中城给端了,咱们的校尉关宠,还有他那几百号铁血男儿,全都拼了命,成了忠魂。现在汉朝的援军啊,能干啥呢?也就干两件活儿:一是给关宠他们这些好汉收尸,好歹让人家的魂魄能回老家转悠转悠;二是咬咬牙,狠狠心,跟那些匈奴小子干上一仗,给被害得那叫一个惨的同袍们出口恶气,讨回公道!
没过几天,汉朝的大部队浩浩荡荡开到了交河城底下,那交河城啊,就是车师前国的老窝,现今吐鲁番西边十来公里地界的雅儿乃孜沟里。
这场仗啊,简直就是明摆着的事儿,没啥好猜的。
瞧见了柳中城那惨样儿,汉军的小伙子们心里头那股子憋屈劲儿,简直就要炸开锅了。正巧碰上那帮子年老体衰、疲惫不堪的匈奴兵,嘿,这下可好,跟猫见了鱼似的,一顿猛扑猛打。那架势,就像是瀑布从天而降,直愣愣地往下砸,愣是把匈奴军给冲得七零八落,跟割韭菜似的,一刀下去,三千八百颗脑袋就搬了家,还活捉了三千多人,外加三万七千多头牲口,什么骆驼啊、驴子啊、马儿啊、牛儿啊、羊儿啊,应有尽有。匈奴兵呢,吃了这么个大亏,哪儿还敢恋战,只好各自为政,撒丫子就跑,天山南麓那边儿,连个影儿都不剩了。车师前国一看这阵仗,心里头那个怵啊,立马儿又乖乖地投降了汉朝。
嘿,您瞧这事儿,仗也打赢咯,仇嘛,也报了,遗体都拾掇好了,架子也端够了,说到底,任务就算圆满落幕了。那几位汉军的头头脑脑一合计,嘿,干脆利落,耿恭那头儿咱就不管啦,直接卷起铺盖,打道回府,乐呵乐呵回京城交差去喽!
您可别埋怨大伙儿心狠,事儿明摆着呢:关宠那帮子人被围的时间比耿恭他们还短一截,都没能挺到救兵,照这么看,耿恭他们能活下来的希望,简直是比针尖儿还小。再加上这数九寒天的,大雪把门儿堵得严严实实,路都走不成,再冒这老鼻子风险,多窜出去几百里地,那不是瞎折腾嘛!万一咱大军也让山给困住了,或者让天山北边的匈奴大军给抄了后路,那不就更惨了吗?眼瞅着差不多就收手,这不是挺“聪明”的一招儿?

交河城那疙瘩,汉军大营里头静得吓人,就听见耿恭那老战友范羌,在那儿呜呜咽咽地抹眼泪呢。大伙儿都憋着,就他忍不住,小声抽泣着。
好容易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帮手,只要咱们翻山一过,就能把兄弟们从鬼门关拽回来。可你们倒好,一句话不救,就不救了?我这心里头,那是一万个不乐意,真真的无法接受啊!
将领们一个个耷拉着脑袋,心里头就琢磨着一个字——怯!没错,就是怕!
嘿,他们心里头那个忐忑哟,就跟走在薄冰上似的,生怕一不留神,“噗通”一下,到手的鸭子飞了,千古恨啊!这胜利眼看着就要揣兜里了,再撒手那可不成,他们哪儿敢担这责任呢!
可范羌这家伙,胆子壮得跟山似的,耿恭手下,哪儿找得出半个孬种!这便是当将军的给队伍注入的那股子魂儿,它像风一样,能吹进每个兵的心窝子里,让他们浑身上下都是胆儿,不管遇上啥难事儿,心里头总琢磨着:奇迹嘛,说不定就来了!就这么着,一个个咬牙挺着,嘿,奇迹还真就让他们给撞上了!
哎哟喂,瞧瞧这事儿,范羌那小子,面对着一帮子软脚虾和无情的家伙,愣是不听话,直接往大帐门口一站,双腿一弯,扑通一下,就跟大地来了个亲密接触,磕头磕得那叫一个响,脑袋瓜子跟地面一摩擦,血花儿都溅出来了。汉军的头儿秦彭,一看这架势,没辙了,只能慢悠悠地站起身,长叹一口气,对着范羌就来了一句:“我说范羌啊,你醒醒吧!耿校尉他们,早见阎王去了,哪儿还能活蹦乱跳地回来?为了救几个注定没救的人,再搭上咱汉家兄弟的性命,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咱能不能理智点儿?”
得了,话一落地,他连头都不扭一下,直奔账篷后边溜达去了。
范羌一溜烟地跪爬过去,紧紧搂着秦彭的大腿,说啥也不撒手,就跟粘了胶水似的。几个士兵见状,连忙一拥而上,又是拖又是拽,想把范羌给弄出去——瞧瞧这大帐里头,哪个将领的级别不得比你范羌高出老鼻子去,哪轮得到你在这儿撒泼打滚啊?
黑漆漆的夜里,静得吓人,突然范羌扯着嗓子,嚎啕大哭起来:“秦将军啊,您就让我瞅瞅那疏勒城吧!我心里头有数,耿校尉那家伙,铁定还在那儿带着兄弟们死扛呢!他们中肯定还有喘气的!就算真不幸都去了,我范羌也得跟他们凑一块儿,黄泉路上有个伴儿!”

嘿,你猜怎么着?耿恭这家伙,此刻还真就硬朗着呢,活得倍儿精神!不光是他,整个疏勒城里,加一块儿有二十六个好汉,正咬牙切齿地,用他们那最后一丁点儿的气力,跟死神较着劲儿,硬是不让自个儿的命灯给吹灭了。
打从那天,大伙儿喊着“饿得慌也要吃敌人的肉”开始,嘿,这都十多天了,嘴里愣是没沾过一粒米一星儿面。再加上这鬼天气,冷得跟刀割似的,手指头都快冻掉了,皮都裂得生疼。大伙儿被折磨得跟霜打的茄子似的,站都快站不稳了。可你猜怎么着?咱们还是咬牙挺着,心里头那股子劲儿,就盼着能创造个生命的小奇迹呢!
嘿,说实在的,他们那股子死磕到底的劲儿,说到底,不就是还剩那么点儿面子、心里那点爱国火苗子,再加上求生的本能嘛。至于汉朝的援兵,他们心里头早跟那断线的风筝似的,没指望了。下回匈奴一来,或者太阳照常升起那会儿,估摸着就是他们跟这世界说拜拜的日子了。眼下,他们能咋整?就等着呗。活着的时候跟夏天的花儿一样耀眼,走的时候跟秋天的夜晚一样安详,这或许就是他们的命数吧!
疏勒城里城外,雪花跟不要钱似的往下撒,一股脑儿地越下越大。你瞧,这雪下得一阵比一阵急,跟赶趟儿似的。我猜啊,等这雪消停的时候,准是匈奴那帮家伙最后来攻城的关键时刻了。

到了夜里头,雪总算是歇了。瞧瞧那轮亮堂堂的月亮,跟天山对上了眼儿,整个山头啊,被雪裹得跟银子似的,漂亮得没法说,简直让人看不够!
天山头上挂亮堂,大雪纷飞白茫茫,抬头瞅瞅那月亮,低头心里想家乡。月亮圆又亮堂堂,雪地宽又广无边,一望月亮心就痒,思乡情绪涌心田。
耿恭这家伙,打小就成了没爹的孩子,刚冒头儿那会儿,他爹就撒手人寰了,全靠他娘一人,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大。眼瞅着到了这节骨眼儿上,他心里头最惦记的,还是老家院子里头那位老娘。这一年多,也不知道她老人家身子骨儿硬朗不硬朗,过得舒心不舒心。
哎哟喂,您说这事儿,自古以来,忠孝俩字儿就跟油和水似的,愣是难搅和一块儿。老妈子,您得多担待担待您这不争气的儿子,我没法儿活蹦乱跳地跨过那玉门关,再回来围着您老人家转,给您逗乐子!
正琢磨着呢,冷不丁远处轰隆隆地响起一片,像是千军万马在闹腾。抬眼一瞅,嘿,那马儿们在雪地上撒欢儿,蹄子底下跟踩着烟儿似的,腾起老高一片白蒙蒙的雾气。粗粗一估摸,少说也得有个千把号人,浩浩荡荡地朝着疏勒城奔来。
那些个还能勉强站稳脚跟的汉军兄弟们,一个个跟斗鸡似的,硬撑着爬了起来。脸上那神情,一半是吓得脸色发白,一半是豁出去了的狠劲儿,真够瞧的。
嘿,将军,咱们是不是到了揭锅底的时候了?咱是豁出去跟那帮匈奴崽子干一架呢,还是说,咱自个儿抹了脖子,省得被逮住,成了后人口里的千古大笑话?
耿恭哈哈一笑,摆了摆手:“急啥呀,咱就让这雪景儿,美得跟画儿似的,陪着咱们的青春梦想一块儿埋土里得了!”
得了,就这么着:那些个没力气再打的,自个儿找个地儿歇菜去吧。还有把子力气的,都跟我上前头去,跟敌人死磕到底,拼到最后一口气,投降?门儿都没有!咱哥几个,说好的一块儿来,一块儿走,可不能半道上散了伙儿。
嘿,您瞧好了,二十六个汉子,一个个跟斗鸡似的,战刀出鞘,就等着耿恭大哥那一嗓子——“杀”!只要话音一落,管他呢,是自己人还是对头,反正刀光剑影,开干就是了。
嘿,你猜怎么着?就在这节骨眼儿上,城底下那帮“匈奴大军”里头,冷不丁远远地飘来一嗓子,听着倍儿耳熟:“我是范羌啊!汉朝派兵来接校尉大人啦!城里头还有咱汉家的哥们儿在吗?”

哎哟喂,那句话来得可真是掐准了点儿,就差那么一丁点儿,耿恭那儿的好几位兄弟可就要挥刀抹脖子啦!晚半秒,嘿,那可就热闹喽!
范羌生怕城楼上的哥们儿耳朵不利索,扯着嗓子又嚎了一嗓子。话音还没飘远呢,城头上就炸开了锅,虽然声音透着几分虚弱,但那股子激动劲儿,喊出的“万岁”声,听着倍儿带劲!
瞧瞧耿恭那铁打的汉子,此刻虎眼里也泛起了泪光:嘿,咱们算是熬出头了,救兵到了,祖国的队伍来接咱们回家啦!皇上心里还惦记着咱们呢,朝廷可没忘了咱这帮小子。这一年多,跟在地狱里煎熬似的,等啊等,总算是没白熬!
城门敞亮儿一开,两边的人马跟炸了窝似的聚到一块儿。甭管是熟人还是生面孔,一个个伸着手就搂到一块儿去了,蹦跶着,嚷嚷着,眼泪鼻涕一块儿往下淌,笑得跟哭似的,哭得又像在乐。将士们啊,这一年多,风里雨里啥苦没吃过,啥难没熬过,硬是一滴眼泪没落过。嘿,这会儿可好,眼泪跟不要钱似的,跟疏勒那泉水一样,咕嘟咕嘟往外冒,汇成一条河了!

好一阵子闹腾,大伙儿的心情才算安定下来。这时候,援军大摇大摆进了城,立马生起火堆,摆开宴席,喝得那叫一个痛快,笑得合不拢嘴。嘿,疏勒这座死气沉沉的城市,算是活过来了!从没人影儿到热闹非凡,从阴曹地府回到了阳间,这变化快得跟做梦似的。
耿恭好不容易跟范羌碰了头。这一见,简直是死里逃生后的头一遭,俩人心里头那个激动啊,跟揣了窝兔子似的,蹦跶得厉害,可偏偏一句话也挤不出来。直到酒过三巡,耿恭这才捋顺了心思,开口问起了前因后果。范羌一拍大腿,竹筒倒豆子般,把事儿的前前后后给抖搂了个干净。
嘿,您知道吗?范羌那小子,愣是用他那股子倔强劲儿和实心眼的忠诚,把秦彭那些个汉军大佬们给打动啦!他们一合计,得嘞,破个例吧,就让范羌这么个不起眼的小军吏临时挑大梁,单枪匹马领着两千汉军勇士,翻那天山跟玩儿似的,去完成那场压轴的救援大戏。至于剩下的哥们儿,则护着柳中城关宠他们的骨灰盒,还有打匈奴得来的那些宝贝疙瘩,哼着小曲儿往回撤啦!
范羌他们这一路,嘿,那叫一个难走!连着多少天的大风雪,把天山给埋得跟个大雪堆似的,雪深得都能把人给埋喽。走一步,喘三喘,不少战士愣是因为体力跟不上,脚下一软,就这么倒下了。这简直就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风雪大冒险,为了把自个儿的兄弟给救出来,他们是豁出去了,付出的代价,啧啧,可真是不小啊!

可您瞧,到头来这些个辛苦钱儿花得真值!为啥?它不光亮堂堂地摆那儿,象征着股子劲儿,还眼瞅着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儿成了真,编出了一段儿英雄谱!往后啊,班超那小子单枪匹马在西域晃荡了几十年,啥妖魔鬼怪都不带眨眨眼的,根儿就在这儿呢。您说说,榜样这玩意儿,力量大得吓人!汉军跟匈奴一开打,心里头有了这底儿,那就跟吃了秤砣似的,铁了心越打越来神儿!
这么说吧,人嘛,有时候得学会放手;但放手不代表撒手不管,更不意味着打退堂鼓。好比一条道儿,咱要么打一开始就别迈腿,一旦踏上了,那就得咬牙走完,这样活着,心里才踏实,老了也不带遗憾的。那些动不动就打退堂鼓的主儿,嘿,可真叫人瞧不起!
得嘞,您瞧,耿恭范羌他们那危险啊,还跟屁股后头追着呢。为啥?就因为那数万匈奴大军,跟疏勒城边上候着呢,巴巴地等着雪一化,好去城里头捡便宜呢。虽说眼下局势有了点变动,汉朝派了两千援兵来,可北单于他能轻易放手?他要是一松手,这一年多围城的辛苦不就成了笑话一桩?那以后,匈奴人在西域还怎么抬头做人啊!
哎,您瞧,那欢庆的小劲儿一过,耿恭、范羌他们几个,拍拍身上的尘土,喘口气儿,二话不说,扭头就往中原奔。得嘞,归家的路啊,他们这就踏上了。

北匈奴那头单于,一听这消息,火冒三丈,哪能咽下这口气!立马就吆喝着手下,说啥也得追上去,得把面子给找回来。
这一年多,耿恭可真是经过了火里水里的一番磨练,硬是从汉军里杀出了一条血路,成了最能啃硬骨头的家伙。更别提他现在手下有两千多精兵强将,骑着大汉的好马,装备顶呱呱,跟以前比是天上地下了。所以啊,就算数万匈奴大军围追堵截,耿恭也不带眨眨眼的,他悠悠哉哉地躺在担架上,跟指挥家常便饭似的,一边打一边撤,愣是打了好几场精彩绝伦的反击战。那匈奴人啊,被收拾得那叫一个惨,一个个灰头土脸,直喊着老天爷不公平。
——跟汉军打硬仗占不到便宜,那也算了。就连咱们最拿手的在平原上放开手脚干一架,居然还是拿耿恭那两千来人没办法!还让他们顶着大雪,千里迢迢地溜出去,跟玩儿似的没人挡得住。这不是比以前还栽了大跟头嘛!真是太不值当了。
打那以后啊,北匈奴一瞅见汉军,那脾气就跟被猫挠了似的,全没了。往往还没动手呢,心里头就先哆嗦上了,耿恭这家伙,对他们那民族自信心,简直是来了个连锅端,打击得那叫一个狠哪!
要是说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将来没了盼头,那离散摊子可就指日可待喽。您瞧瞧那匈奴,在亚洲地界上威风凛凛了好几百年,到头来,嘿,不也走上了穷途末路嘛!
公元76年那春儿,耿恭带着两千汉家儿郎,好家伙,终于颠儿颠儿地到了玉门关。这一路啊,饿的、病的,再加上老天爷不赏脸,路又难走,那二十六位在疏勒城拼到最后一口气的勇士,愣是只剩下一半,活着瞅见了老家的天儿。算上耿恭自己,回到中原的,也就十三个哥们儿,准确地说,是十三个快成了皮包骨的哥们儿。他们身上那衣服,破得跟渔网似的,鞋子露着脚趾头,脸跟霜打的茄子一样,瘦得跟竹竿儿相仿。可就算这样,那股子倔强劲儿,还是藏不住,活脱脱是从地狱里爬回来的英雄好汉,给人世间来了个晴天霹雳,消息跟长了翅膀似的,嗖的一下子就传遍了整个中国,轰动得全世界都知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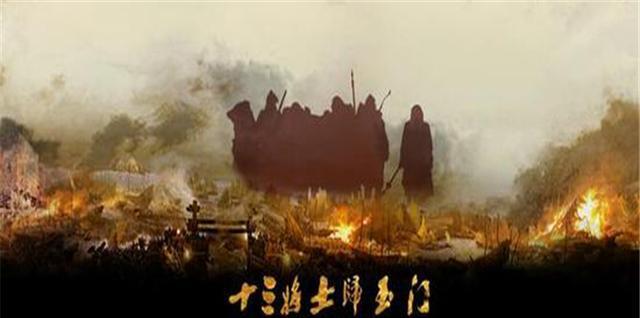
嘿,您猜怎么着?朝廷那位大人物,中郎将郑众,他脚底生风地赶到了玉门关,专为给那十三位好汉接风呢!这一路上风尘仆仆的,得好好款待一番,欢迎咱们的英雄回家嘛!您瞅瞅,这十三位爷,一个个铁骨铮铮的,站在那儿就跟玉门关的石头似的,硬气!郑众和玉门关的将士们一看,心里头那个佩服啊,嗖嗖地往上冒,干脆利索地,一个个都挺直了腰板,给这十三位来了个最地道的军礼,那场面,庄重又热烈,感情深着呢,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就这么简单直接,啥也不多说,都在礼里头了!
接着,郑众乐呵呵地把耿恭那十三位兄弟迎进了大营帐,自己动手给他们洗了个痛快澡,又换上了新衣裳。随后,他火急火燎地找人给他们瞧病养身子。打那以后,郑众算是彻底被耿恭给迷住了,尽管他这官儿可比耿恭大多了,但他心里头,耿恭那就是他的偶像。
等耿恭他们一行人被安全送回到洛阳,嘿,那粉丝数量噌噌往上涨啊!整个洛阳城炸了锅,老百姓们跟不要钱似的往外涌,街道上挤得满满当当,就为了亲眼瞧瞧他们心目中的大英雄长啥样。万人空巷,那场面,比过年还热闹!
打从王莽那小子把汉朝搅和乱套以后,汉朝这面子啊,是一天不如一天。虽说光武帝费老鼻子劲又给大汉续上了命,可塞外那块地界儿,咱还是没露过啥大脸。老百姓心里头那个憋屈啊,盼星星盼月亮,就想瞅见一位能在塞外耍威风的大汉英雄。嘿,这不,耿恭大哥凯旋而归了!他不光带着一身塞外征战的赫赫威名,还扛回了咱汉家子弟兵那股子魂儿!你说说,老百姓能不乐呵得跟过年似的嘛!
没多久,耿恭的头号粉丝郑众,给皇上写了封信,大力吹捧他的偶像:“您瞧瞧,耿恭那小子,就一个人带着几个兵,愣是在那孤零零的城里头,跟匈奴大军硬扛了好几个月,都快一年了!他心力交瘁,还得凿山找水,连弓箭都煮了当饭吃,简直就是九死一生啊!就这样,他还愣是干掉了匈奴成千上万的人马,自个儿愣是没撂挑子,没给大汉丢脸。耿恭这忠勇、这节义,古往今来,找不出第二个!皇上,您得给他封个大官儿,好让其他将领也学学!”

郑众那小子往上一递折子,嘿,朝中那些个大臣们立马儿就跟上了节奏,纷纷叫好。就连司徒鲍昱也跳出来说,耿恭那家伙,忠贞劲儿直逼当年的苏武啊,得嘞,咱得给他整个高官厚禄,好好奖赏奖赏!
哎,您瞧瞧,一个人守住气节,那不难,跟玩儿似的。但要带着一大家子兵马,一整支队伍,都守住气节,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那孤零零的城里头愣是一整年没出一个二五仔,嘿,这可就是真本事了!由此可见,咱们这位耿恭大哥,不光是爱国爱到骨子里的硬汉,指挥打仗的天才,守城的行家里手,他还是个搞定人心的高手,思想政治工作做得那叫一个绝!这样的将帅之才,简直比大熊猫还稀少,不用他,用谁啊?得赶紧提拔重用才是!
嘿,您瞧这位刚坐上龙椅没多久的汉章帝,对那打打杀杀的事儿可没啥兴趣,所以啊,耿恭这位战场上威风凛凛的大英雄,在他眼里也没那么金光闪闪。于是乎,皇帝老儿大手一挥,给耿恭整了个“心灵鸡汤奖”——虽说“显爵”没捞着,但您也别挑,封侯这事儿,可不是街上的大白菜,想拿就拿;不过呢,官职嘛,咱还是可以动动手脚,提拔提拔,骑都尉这位置就挺合适,俸禄跟两千石大米似的,够厚实了,这可是看在他老耿家祖辈都是开国功臣,一门心思尽忠报国的面子上,才给的面子活儿。
嘿,说起来,那守城的另外十二位大兄弟也得拉扯拉扯嘛!饿着肚子愣是挺了那么久,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得给他们来点甜头鼓鼓劲儿——就说耿恭手下的司马石修吧,给他整个洛阳市丞当当,养老嘛,这市丞啊,就是市令市长的得力助手,帮着管管城里的大小事务,还有市场交易啥的,保证物价不乱蹦跶。俸禄二百石,手下还有三十六个小弟呢。虽说官儿小了点,但胜在轻松自在,小日子滋润着呢。还有那个司马张封,给他安排到雍营当司马去,那可是中央军的编制,比之前在边防军那会儿可风光多了,是吧?再说说军吏范羌,这家伙功劳也不小,提拔提拔,让他去共县当个县丞,俸禄四百石呢。至于剩下的那九个兄弟,起点低了点儿,那就给补个羽林的缺吧,好歹也是在宫里混饭吃了,不用再跑到边塞去喝西北风啃雪疙瘩了。
说真的,将士们心里头压根儿没往那方面想,瞧瞧那些没能踏进家门一步的兄弟,他们算是捡了条大便宜。可老百姓们啊,一个个还是唉声叹气个不停,总觉得自家心里的英雄受了多大的冤枉似的。
后来啊,章帝一道圣旨下来,说戊、己校尉和西域都护府都得撤了,还叫班超打包回国,打算把整个西域的事儿都撂挑子,这事儿后来人们管它叫“二绝”。可您猜怎么着?耿恭那股子劲儿,愣是把班超给镇住了,他没听那道圣旨,铁了心要把自己的活儿干完。就这么着,班超一个人在西域硬扛了快三十年,最后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那叫一个前无古人,后也难有来者!具体咋回事儿,咱后头再细说,这儿就先卖个关子。
另一边儿,耿恭愣是没去当那个新官。咋回事儿呢?就在耿恭带着兵马死守疏勒那会儿,耿恭他老娘因为想儿子想得厉害,身子骨儿一弱,说走就走了,连儿子最后一面都没见着。耿恭一听这消息,心如刀绞,眼泪哗哗的。心想,自己是出息了,可这都是兄弟们用命换来的;自己是出息了,老娘守了大半辈子寡,图啥了呢?反正吧,这心里的悲痛劲儿,让耿恭对着那些荣誉半点乐呵不起来。他二话不说,立马奔回家,给老娘办了丧事,还在坟头边儿上盖了个小屋,一守就是三年,好让心里头那点儿伤慢慢愈合。当官的事儿,先搁一边儿凉快去吧!

哎,您瞧瞧,这世事无常啊,耿恭刚在家里猫了不到一年的光景,本想好好休养休养,谁承想朝廷那边儿急匆匆地就派了五官中郎将马严,哦,就是马援他侄子,来了还带着牛啊酒的,一进门就喊:“得嘞,老兄,别在这儿哭丧着脸了,赶紧拾掇拾掇,跟我上朝去,新官职、新任务等着您嘞!”
您瞧,打从马援那家伙辞了陇西太尉的官儿,咱们汉朝西北边儿上的那些官员啊,真是一个比一个不靠谱。说好的为老百姓做点实惠事儿吧,没影儿!倒是对那些西羌搬过来的百姓,动不动就“狠劲儿欺负、活儿往死里派”(我给您按汉明帝那诏书的意思大白话说了啊)。这一来二去的,边境上的乱子就跟炸了锅似的,他们还不知道怎么收场,愣是把西北那片儿搞得越来越乱套。到了汉明帝中元二年秋天那会儿,陇西太守刘盱跟烧当羌干了一仗,结果五百号人就这么打了水漂。朝廷一看,得嘞,赶紧派张鸿带着兵去帮忙,结果呢,全军覆没,连泡儿都没冒一个。再说说明帝那时候的几个护羌校尉,窦林啊、郭襄啊这些人,本事不咋地,闯祸倒是挺在行。这羌乱啊,就这么越闹越大。到了章帝建初元年,耿恭那小子刚回家奔丧没多久,那些地方官还是老样子,欺负西羌百姓跟玩儿似的。这下可好,老百姓的火气攒够了,“砰”地一下就炸了锅!
事儿啊,得从金城郡安夷县,就是如今青海乐都县东边那块儿说起。那儿有个汉朝的小芝麻官,手里攥着点儿小权力,就跟土皇上似的,老爱欺负羌族的老百姓。老百姓嘛,斗不过官,忍气吞声也就罢了。可这小子,欺负人上了瘾,胆子比天还大,大白天的,愣是抢了个民女,还是西羌部落里一个有主儿的妇人。这事儿,可真够缺德的!
您瞧,这事儿明摆着,天底下哪儿有爷们儿能咽下这口气?那位羌家汉子,眼见着老婆被人抢了,立马火冒三丈,带上几个铁哥们儿,直愣愣冲进官府,咔嚓一下,那小官员的脑袋就搬家了。他们夺回嫂子,大摇大摆地走了,一溜烟儿跑回卑湳部落老家,躲了起来。嘿,这事儿干得,真够利索!
安夷县的县长宗延,一听手下被砍了,那火儿“噌”一下就上来了,也没跟郡里打个招呼,直接带着队伍冲出塞外。羌民们一看,宗延带着大队人马,那架势跟要吃人一样,心里头直嘀咕:这汉军该不会趁机来个大扫荡吧?这么一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大伙儿反了,把宗延他们一锅端了。紧接着,他们又拉上附近的勒姐、吾良两个羌人部落,一块儿出兵,浩浩荡荡地朝着金城郡杀过去了。
一件刑事小事儿,愣是让那帮东汉的糊涂官儿给搅和大了,先整出民族疙瘩,再一鼓捣,羌人兄弟们不干了,直接起义,乱子闹大了!这事儿,要搁现在,那得叫“小事变大乱,无脑官员在作怪”。烽火连天那么一报,汉章帝一听,火儿“噌”一下就上来了,龙颜大怒,那叫一个不爽!
——汉羌两家,那老账可多了去了,你们还非得往上头撒把辣椒,这不是逗乐子嘛!动刀动枪的事儿,我头疼得紧,真真的,最烦这一出了!
得嘞,眼瞅着这事儿没法躲了,仗嘛,不打也得硬着头皮上了。赶紧的,派陇西那疙瘩的太守孙纯,带着他的人马,快马加鞭去帮金城郡解围。还有,再把那以前当过度辽将军的吴棠老兄请出山,让他挂上护羌校尉的头衔,跑到安夷去,把那一摊子乱麻给理顺喽。
卑湳嘛,说到底就是个小疙瘩部落,汉朝的大军一到,立马就蔫儿了。就那么一仗,脑袋瓜子嗖嗖地掉了好几百,立马就老实巴交了。
卑湳羌这家伙虽然消停了,可那战火一旦被撩拨起来,就跟燎原的火苗子似的,拦都拦不住。西边那帮羌人里头,最厉害的烧当羌又开始磨刀霍霍,心里头的小九九转悠得欢呢。
建初二年那年夏天,烧当羌的头儿迷吾一吆喝,金城郡那片的西羌部落们,嗖的一下子全翻过边塞闹事去了,凉州那边可炸了锅。金城太守郝崇一听,急眼了,带着手下就往外冲,想逮住他们。结果,到了荔谷那儿,羌人们跟埋伏好了似的,给汉军来了个突然袭击。这一仗,汉军惨喽,丢了两千多号人,郝崇呢,就骑着一匹马,拼了老命才逃回来,算是捡了条命。
哎哟喂,瞧瞧那羌乱,闹得是越来越欢实了。边防的老把式,护羌校尉吴棠,这回可是愁得眉毛都快烧着了,愣是一点辙没有。汉章帝一看,火大了,啪叽一下,下了道圣旨,直接把这老兄的官帽给摘了,换上了谁?嘿,那可是守边守了二十多年,打过无数硬仗的老江湖,武威太守傅育!这下,看看局面能不能给咱扭转过来。
傅育一拍马屁,就坐上了那把交椅,可没成想,他这老江湖中的老油条,也照样没法把烂摊子给拾掇起来。迷吾那家伙,势力跟吹气球似的,噌噌往上涨,还拉上了西羌那头大号部落“封养羌”的头头布桥,俩人一合计,五万多人马浩浩荡荡,愣是把战火从锅里溅到了陇西、汉阳那片儿,改名叫天水郡的地界也不得安宁。这西北啊,简直是乱成了一锅粥,糊里糊涂,没个消停!

这么一闹腾,汉章帝忽然拍脑袋想起了那位能人耿恭,立马封他做了个长水校尉(虽说俸禄跟二千石差不多,但比起西汉那会儿,可是矮了半截)。然后,皇上急吼吼地喊他进宫,说是得赶紧合计合计怎么对付那些难缠的羌人。
战事吃紧,耿恭火急火燎地赶回京城,一进门就写了封奏章,详细说了咋收拾羌人的法子。他说啊,西北那地界儿,山峦叠嶂的,弓箭手们在那儿可占了大便宜。咱得赶紧把各郡的精锐射手都招呼起来,一股脑儿地派到前线去。这么一来,羌人准得被咱们打得落花流水,逃都没地儿逃!
章帝猛地一拍桌子,乐呵呵地说:“得嘞,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建初二年那八月里,汉章帝发了话,说城门校尉马防啊,他虽是管着京城各大门兵马的头儿,跟那二千石的官儿差不多大,但这回得让他去干车骑将军的活儿,当平羌的大头头。长水校尉耿恭呢,就给他当副手。俩人一合计,带了北军五校里最厉害的卫士,还有各郡的弓箭手,拢共三万人,浩浩荡荡往西北前线奔去了。
马防这家伙,原本是跟耿恭一个级别的城门校尉,可他呢,从没摸过枪杆子上过战场,十足一个军事门外汉。要论真本事,要论那威风凛凛的名声,嘿,他得往耿恭后边排老远呢。可你猜怎么着?这家伙一眨眼,就成了“地位赛过九卿,跟三府平起平坐”的车骑将军,还当上了这场大战的主帅!这事儿,可真让人摸不着头脑,不是?

这事儿说起来简单得很,那位马防啊,可不是一般人,他是大名鼎鼎的伏波将军马援的二小子,当今马太后的亲二哥嘞!
瞧瞧那后台,硬得跟石头似的,耿恭啊,也只能往边上站站了。没法子,人家身后那是大树参天,自己呢,顶多就算是个影子,还模糊不清的。说起来,人家有的是靠山,自己嘛,也就剩个背影,还孤零零的。
耿恭闷声不响,可朝中总有那么些大臣爱凑热闹。东汉到了后半截儿,说白了就是那帮儒臣士大夫和皇亲国戚斗来斗去的故事。这不,那个老爱跟皇上拧着来的司空第五伦,第一个跳出来挥舞大旗,上书直愣愣地反对:“我说啊,那些皇亲国戚,赏个侯爵让他们富贵富贵就得了,别让他们插手朝政。为啥呢?按法律来办吧,伤了和气;徇私情吧,又违了规矩。听说马防这家伙要往西边去打仗,我琢磨着太后仁慈,皇上孝顺,万一出点小岔子,那可咋收场啊,心疼都来不及呢!”
可这事儿吧,白搭!奏章递上去,跟那泥牛掉海里似的,连个泡儿都没冒,章帝大爷压根儿不当回事儿。这简直就是政治场上的红灯啊,明摆着的事儿,光武帝刘秀和明帝刘庄那会儿,对外戚那是严加看管,生怕他们搞事儿。可到了汉章帝这儿,嘿,这觉悟没了!马防这家伙一开先例,外戚们那是越来越嚣张,东汉这摊子事儿,眼看就要乱套了!
另一边儿,东汉那帮大军早就上了路,他们顺着渭水一路往西溜达,眼瞅着就要到汉阳郡的老巢冀县了,就是那隗嚣当年让人围了的地界儿。眼瞅着敌人就在眼皮子底下,可汉军高层那儿却闹起了别扭。马防这家伙,满心满眼都是立功出风头,哪儿能让耿恭给抢了先呢?于是乎,他打发耿恭带着北军五校的三千号人,往北跑到陇西郡那疙瘩的枹罕(搁现在就是甘肃临夏东北那块儿),说是要切断陇西羌跟塞外羌的勾连。他自己呢,则带着大军主力,直愣愣地往西冲,奔着临洮就去了,打算好好收拾收拾那个“封养羌”的头头儿布桥。
耿恭心里头猛地一颤:让我跟着打打下手,跑个龙套啥的,那倒没啥大不了的。可问题是,马防这平叛的大当家,咋就这么心急火燎地往外冲呢,连点儿拐弯抹角的外交手腕都不带使的,这不是瞎忙活,费力不讨好嘛!
耿恭琢磨来琢磨去,决定给朝廷写封信,保举窦固来搭把手,他是这么说的:“想当年,咱们那位安丰侯窦融,在西边那块儿混得风生水起,羌人胡人都跟他铁了心似的。到如今,一提起窦家,大伙儿还乐呵着呢。再说说大鸿胪窦固,前阵子带兵攻打白山,羌人一听窦固来了,吓得三天之内就乖乖投降,白山一战大胜,全靠窦固的本事。依我看,得让他当个大使,去凉州那块儿镇镇场子。至于车骑将军嘛,让他带着兵在汉阳那儿守着,当个威风凛凛的大靠山,保管没问题!”
那当然白搭,奏章递上去,就好比石头扔进大海,连个泡都不冒,章帝老爷压根儿就不带瞅一眼的。
不理也罢,耿恭自知人小势微,说的话没人听也是常理,可他做梦也没想到,这回自个儿可真是捅了大娄子了。您瞧,马家跟窦家现在那是政坛上的死对头,章帝心尖上的人是窦家的贵人,宠得跟啥似的,正跟马家力挺的宋贵人较着劲儿,争那皇后宝座呢。这背后的权力较量,暗流涌动,凶险得很。耿恭偏偏在这个时候给窦固站台,这不是明摆着往老虎嘴里送肉嘛!
不提那祸根儿咋埋下的了。咱们聊聊马防在西北那场大战。他单枪匹马,哦不对,是独自率领了三万汉军的精锐,首先在临洮那儿,跟羌虏干了一仗,打得他们屁滚尿流,一下子就干掉四千多人。这还没完,他又追着敌人往南跑,跑到临洮西南一个叫望曲谷的地界儿(就是现在的甘肃岷县那块儿),又是一顿猛打,又干掉一千多。这回不光是人,还缴获了牛羊十几万头,布桥手底下的万把人也都投降了。汉军这第一仗,打得那叫一个漂亮!
得了,咱接着说。打从建初二年那热乎乎的八月起,一直到建初三年的秋天,马防在陇西那块地界上忙活得跟孙子似的,整整一年啊,好歹算是把羌军给摆弄老实了点。汉章帝一看,行嘞,大手一挥,写了道诏书,就把马防带的那帮汉军主力给撤回来了,就给耿恭撇下三千人,让他去拾掇那乱成一锅粥的西北。瞧这章帝,对打仗这事儿似乎不太上心,用兵那是能抠门就抠门,一万人能搞定的事儿,他愣是不想多花两万。再说那马防,一回京城,嘿,马氏三兄弟跟坐火箭似的,一个个封了侯,风光得不得了。章帝还非得让史官给马防那征西的事儿写赞歌,弄得人心里头直犯嘀咕,这也太过了点吧!
章帝心里头对西北那摊子事儿挺乐呵,可朝堂上的大臣们啊,一个个眉头紧锁,心里头七上八下的。虽说封养羌那头是投了降,可陇西那边儿,叛羌还跟韭菜似的,割了一茬又一茬,数万人马在那晃悠呢。再看耿恭,手头就那么三千号人,跟人家比起来,简直是蚂蚁撼大树,双拳打群架,他能不能撑得住场面,再把这羌乱的火给彻底扑灭,还真是让人捏把汗!
嘿,大臣们可真是瞎操心,你们瞧瞧耿恭这位爷,那可是逆风局里的高手,专治各种不服。马防一走,耿恭一来,对西羌来说,简直就是噩梦连连,雪上加霜啊!

建初那年的冬天,耿恭接了皇上的命令,带着队伍从枹罕一路往南冲。嘿,你猜怎么着?就那么一仗,直接把那些羌人打得落花流水,斩首加俘虏加起来上千号人,还顺手牵了四万多头牛羊回来。那些羌人的十三个部落头头脑脑聚一块儿开会,商量来商量去,最后一致举手:得了,咱们向耿恭投降吧!人家可是西域的战神,投降给他,不寒碜!
喜讯飞到洛阳城,朝廷民间乐融融,官吏百姓笑开怀,大臣们争着上书庆贺,琢磨着给耿恭补上那份早该来的奖赏。
嘿,你猜怎么着?就在这节骨眼儿上,陇西那边儿给章帝递来一封不那么顺耳的折子。耿军的监军大人,也就是那个李谭,他上书说道,耿恭这家伙,“带着兵却不管士兵的死活,整天就知道放鹰逐犬,满大街晃悠,敌人来了他倒好,躲在营里不敢露头,接到诏书还一脸不乐意”,得好好收拾收拾他才行!(这故事出自《东观汉记·耿恭传》)
瞧瞧耿恭这家伙,刚在西域大展拳脚,把那些羌人收拾得服服帖帖,眼看就要封侯拜相,风光无限了。咋一转眼,他就成了人们口中的“不管手下死活,整天就知道玩鹰遛狗,见到敌人比兔子跑得还快”的纨绔子弟了呢?要是他真这副德行,早在西域那会儿,早就举手投降匈奴了,哪还能硬撑到最后?再说了,那十三个铁了心跟他共进退的勇士,是眼瞎了才会跟他混?这诬告也太离谱了,简直就是胡说八道不打草稿。可让人纳闷的是,汉章帝居然也不好好查查,二话不说就给耿恭定了罪,直接扔进大牢,官职也给撸了个干净。
大伙儿心里明镜似的,这事儿准是小人马防捣的鬼。他为啥这么干?一来是想抢头功,二来嘛,当年马援将军那档子冤案,耿恭他二叔耿舒也没少煽风点火,马防这是要借着机会,跟耿家算算旧账。你说这伏波将军,一辈子英明神武,怎么他家里人一得势,就沾染上那股子歪风邪气,连名门之后也跟着学坏了,变成了龌龊小人。更气人的是,这些个外戚功臣的二世祖,堕落起来简直没法拦着。史书上都写了:“(马)防兄弟权势滔天,家里奴仆上千,财产多得数不清,全买了京城的好地。他们还大修宅院,楼阁一座连一座,占满了大街小巷,家里歌儿舞女成群,那曲子唱得比祭祀用的还高雅。”还有啊,“宾客络绎不绝,从四面八方赶来……刺史守令多半出自他们家门”(《后汉书·马援列传》)。汉章帝呢,对这些事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啥事儿都向着他舅父马防。这样一来,耿恭就是有天大的理儿,也没辙了。
您瞧,这事儿啊,压根儿就不是谁对谁错那么简单,说白了,全是靠山和影子的事儿。
范晔在《后汉书·章帝纪》里头琢磨道:“魏文帝曹丕说啊,‘明帝那小子太精明,章帝呢,是个厚道人’。章帝心里明镜似的,知道大伙儿烦明帝那套苛刻劲儿,他自己呢,办事宽宏大量……还讲什么忠恕之道,用礼乐来装点门面。说他是个厚道人,挺贴切的嘛!”可我说啊,范晔兄,曹丕这家伙看得可不咋准!他对手下人那是一点儿不透亮,光会护着自家人的短处,说什么厚道人,不就是个老好人,没啥真本事嘛!
嘿,您瞧,疏勒城那墙头还挂着红呢,耿恭这位硬汉就已然被关进了大牢,名声也跌到了谷底。您说这事儿逗不逗?耿恭啊,那可是东汉的战神,一辈子跟外敌较劲,骨头硬得跟铁似的,宁死不屈。可到了朝廷里头,嘿,他倒成了个糊涂虫,面对那冤枉,他愣是一点儿辙都没有,连去找老上司窦固帮衬一把的念头都没有——您知道吗,窦固他姐窦氏,三月份刚当上皇后,皇上对她那可是宠爱有加。要是耿恭找上门去,窦固不使使劲儿让他官复原职,好歹也得在皇后耳边嘀咕几句,让他戴罪立功不是?可惜啊,这位好汉只会跟外人斗狠,一到自个儿家里头的弯弯绕绕,他就成了糊涂蛋,轻易地就举了白旗。
嘿,你猜怎么着?后来啊,多亏了郑众、鲍昱这帮大臣在皇上面前磨破了嘴皮子,耿恭这才算是捡回了一条命。没让他去吃牢饭,倒是给打发回老家了,还附加了一条——这辈子都别想再出来做官咯。

没了战场上那股子威风劲儿,耿恭的日子就像褪色的画儿,最后只能窝在家里,闷闷不乐地走了。这位曾经的英雄豪杰,到头来落得个凄凉下场,真是让人心里头不是滋味,直想叹气——哎,世事无常啊!
要是说那打了败仗的李广老抱怨自个儿没捞着封侯的爵位,那耿恭岂不是比窦娥还冤?你想想,李广那小子败了军还嘟囔个不停,耿恭要是知道了,指定得说:“嘿,我这功劳大大的,咋就没个封侯的份儿呢?我这冤枉得,比那黄河水还深呐!”这不是明摆着嘛,耿恭要是真计较起来,那才叫一个大大的冤枉!
老李广走了,身后留下一大票文人墨客粉丝,那叫一个同情加慨叹啊!可咱说说耿恭呢?咋就没人提提他呢?
老舍先生要是搁这儿,八成也得挠挠头,您猜怎么着?我把那唐诗宋词翻了个底朝天,愣是没找着几句是专门夸咱耿恭的。您说这事儿逗不逗,耿恭这么一号人物,诗词里头愣是没咋露脸。看来啊,古时候的文人墨客,眼光也有跑偏的时候,愣是把这位英雄好汉给忽略了。
要是说关羽打了败仗那会儿,曹操再怎么诱惑,他愣是一点儿没动心,那简直就是忠肝义胆的武圣嘛!那耿恭咋样呢?
嘿,您听听这事儿,耿恭那小子,愣是在那缺水断粮、百死一生的鬼地方,硬扛了一年多。您说这事儿奇不奇?更绝的是,匈奴的王公贵族们拿好处诱惑他,他愣是没动心。您说,这得是多大的定力啊!这么一比,关羽那道德精神,虽然也挺高,但耿恭这不更胜一筹嘛!嘿,这事儿可真够逗的!
哎,说起来都是民族的大英雄,可岳飞那会儿的难处,跟耿恭一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您说是不?岳飞遇到的那些坎儿,跟耿恭的困境比起来,简直就是天堂到地狱的差别。
咋就想不通呢,耿恭这家伙,咋就默默无闻地来了,又憋屈地走了呢,最后还让人给忘到脑后勺去了?你说他吧,没留下啥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也没混出个名堂来,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走了。你说这世道,是不是有时候就爱跟老实人开玩笑?耿恭这家伙,说不定心里头还憋着好多故事呢,可到头来,连点儿浪花都没翻起来,就被大伙儿给忘了个干净。你说,这事儿怪谁呢?是耿恭自己太低调了,还是咱们这些后人眼光太高,把人家给忽略了?反正啊,耿恭就这么成了历史长河里的一个小透明,连点儿回响都没留下。真是让人琢磨不透啊!
要说耿家啊,耿恭那小子出了名,可家里头其他几位英雄好汉,那也是功不可没,一个个受了不少冤枉气。转眼十年过去,窦宪那小子北上把匈奴给灭了,还在燕然山刻石留念,风光得不得了。可您知道吗?窦宪这家伙之前压根儿没摸过枪杆子,就是个挂名的头儿。真正上战场拼刺刀的,全是耿家那些将领,实打实的硬汉!
耿恭那老哥们儿耿秉,可是个了不起的角色,早年当过征西将军、度辽将军,整天在边疆跟西羌、南匈奴打交道,还帮着窦固平定西域,那可是头一号功臣。后来,他又跟着窦宪去攻打北匈奴,功劳大得没法说。可你猜怎么着?窦宪封了俩万户侯,耿秉呢,才捞着三千户,连窦宪的零头儿都不到。这耿秉啊,一辈子在战场上摸爬滚打,最后累得一身病,就这么走了。他在边关那会儿,勇猛得很,每次打仗都冲在最前头,还特疼士兵,士兵们都愿意为他拼命。他在蛮夷之地威望也高,大伙儿都服他。他一去世,南匈奴全国都给他办丧事,哭得稀里哗啦的,有的还往脸上刺字流血,就为了祭奠耿秉的英灵。耿秉的儿子耿冲接了老爸的班,可没多久,就因为窦宪那档子事儿,爵位也给削了。这世道,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啊!

耿恭他那位堂哥耿夔,就是耿秉他二弟,也当过窦宪大将军手底下的假司马。跟着窦宪出征北匈奴,那叫一个勇猛。后来,他自个儿带着八百轻骑兵,嗖的一下子,奔出居延塞五千多里地,破了汉朝军队远征的最远纪录,那可是前所未有的事儿啊!一直打到金微山,把北匈奴那五千多残兵败将给一锅端了,北单于就差那么一点,也成刀下鬼了,北匈奴就这么给灭了。这耿夔啊,后来还当上了边郡太守、度辽将军,跟西羌、貊人、鲜卑这些个异族,那是没少干架,战功赫赫。他还带着兵攻进了高句丽,把朝鲜人打得那叫一个落花流水。可谁成想,他后来也让人给告了,下了大狱。不过,出狱没多久,他就老死在家里了,这事儿,哎,说来也是让人唏嘘不已。
耿夔这家伙,虽说晚年过得有点儿惨淡,历史上也没留下啥大名儿,可他这一辈子,嘿,那可是真够忙活的!干掉了匈奴,又骑着马去踩了鲜卑一脚,远征朝鲜,西边儿还把羌人给摆平了。你说这算不算得上是个满腔热血、拼劲儿十足的英雄好汉呢?
再说耿恭那小子,他儿子耿溥,后来做了京兆虎牙都尉。汉殇帝元初二年,也就是公元115年那会儿,耿溥跑到丁奚城跟叛羌干架,结果不幸捐躯了。耿溥的儿子耿晔也是个狠角色,顺帝在位时,他当上了乌桓校尉,带着手下把鲜卑十万大军打得屁滚尿流,一时间威名远扬塞北。到了汉献帝那会儿,耿秉的曾孙耿纪,虽然是曹操的心腹,但心里头还是向着大汉。他鼓起勇气起兵讨伐曹操,可惜啊,这简直就是现代版的“堂吉诃德大战风车”,耿纪兵败被杀,整个茂陵耿家也因此遭了殃,差点儿就被灭族了。说来也怪,耿弇那幼弟耿霸的七世孙耿宏,也不知道哪儿修来的福分,居然被曹操给放过了。耿家一门忠烈,代代都有英雄出,一直到最后,还在为大汉的荣耀而战,为大汉唱响了最后的悲歌。你说说,这样的家门,跟北宋的杨家将比起来咋样?跟西汉的李广一家比呢?

您知道吗,东汉那两百年里头,耿家可真够厉害的!不完全统计啊,大将军出了俩,将军九大员,还有那中郎将、护羌校尉、刺史啥的,加一块儿,数十上百号人物,都是二千石以上的大官儿。这耿家,简直就是名将界的老炮儿,说是中国头号名将家族,那是一点不含糊。范晔那小子说过,三代为将,道家可不乐意,说名将世家到后来准没好果子吃。可您瞧瞧耿家,名将辈出,好几代了呢,个个功勋赫赫,还都能善终。为啥?人家有原则啊,以暴制暴,该出手时就出手,但从不乱杀无辜。这才是真正的保卫家园,正义的铁血男儿!
哎,你说说,那么了不起的一个名将世家,咋就悄无声息了呢?你随便拉上一百个老百姓问问,能有几个晓得耿家将的?真是的,这耿家将啊,战绩赫赫,名头响亮得很,可咋就没在老百姓心里留下啥深刻印象呢?你说这事儿怪不怪?咱们平时聊天,提起来的是张三李四的传奇,耿家将的故事啊,好像就被风吹跑了一样,没几个人能拽回来。按说,这样的英雄世家,应该跟那夜空中最亮的星似的,让人一眼就能瞅见。结果呢,就像是藏在草丛里的金子,不发光,大家也就视而不见了。一百个人里头,能找出十个知道耿家将的,那就算不错了,你说这世道,是不是有点儿让人摸不清头脑?
嘿,我琢磨着,这数目啊,怕没那么夸张吧!
嘿,您知道吗,那些历史上的大人物啊,活着的时候就没少受冤枉气,没想到死了以后,这待遇还是不公平。学术界那帮子人,冷冷淡淡的,好像跟他们没关系似的;后头的人呢,也是不当回事儿。您说,这要是真有灵魂在天上看着,那些汉朝勇士的眼珠子,怕是要瞪得圆圆的,永远闭不上啦!咱们这个民族啊,怎么就非得让英雄们先流血,后流泪呢?这不是让人心里头不痛快嘛!
可又能咋样呢?瞧瞧历史那盏聚光灯,老爱照着窦宪那些个擅长自我推销的家伙;而那些沉默如铁、流血流汗的硬汉军人,嘿,到死也就是个无名小卒。

说起来,东汉那会儿啊,马家、窦家这些外戚大佬们,简直把封侯的路子给堵得严严实实的。你得承认,他们手里头还真有几把刷子,战功赫赫的。不过,要搁我这名将的小本本上看,他们可不够格青史留名。为啥呢?耿家将那些真刀真枪拼出来的铁血男儿,那才叫军魂!相比之下,他们这些人啊,全靠着别人起家,平平无奇,自私自利,还腐朽得不行,简直就是军人的败类,丢人都丢到姥姥家去了,万年都洗不白!
嘿,您知道吗?有那么一阵子,您可能觉得自己那是了不得,简直就像亲手刻下了历史的痕迹。可实际上呢,您不过是历史长河里头,命运随手捞起来的一粒小石子儿,凑巧被选中了罢了。您说,这事儿逗不逗?咱都不是那写历史的大手笔,不过是随着风,飘飘悠悠落在哪页书上的小尘埃。
您瞧瞧,西汉那会儿,城里头有北军八校尉,其中城里头还分着五校尉呢。到了东汉光武帝那会儿,人家可是动了真格的,搞了个精兵简政的大动作。胡骑跟长水合并了,虎贲和射声也成了一家,中垒校尉这职位还给撤了,换成了北军中侯来盯着。这么一来,北军就缩水成了五校尉,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就这么简简单单五兄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