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到了晚年,对张居正特别看不顺眼。虽然他们以前关系好得跟一个人似的,啥都能聊,政治理想也一模一样,但说实话,权力的游戏太狠了,能把人的本性都给带跑偏。张居正也没能例外,他也变了。
同样是朝廷里的大臣,可高拱不仅是阁臣还是皇上的老师,老压着我。而且他跟我年龄也就差个十二岁,我心想,我这内阁首辅的位置啥时候能坐上啊?我的政治抱负啥时候能实现呢?时间不等人啊,看来只有把高拱挤走,我才能坐上那首辅的交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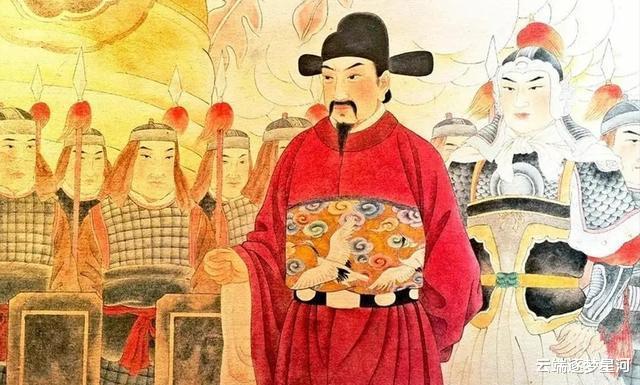
而且高拱对恩师徐阶下手太狠,我好不容易通过各种关系才让高拱手下留点情面。他还嘲笑我收了徐家的好处,这不是明摆着往我身上抹黑吗?无论从公还是从私的角度,我都得把高拱给拉下马。
不过高拱跟严嵩可不一样,早在隆庆帝还是裕王那会儿,高拱就陪在他身边了。他一直尽心尽力地帮衬着裕王,让裕王这心里头啊,总算是有了点暖和气儿。裕王对高拱这些年来的照顾,也是感激得不得了,两人早就处得跟师徒一样亲了。
隆庆时期,高拱权势滔天,他不仅坐上了内阁首辅的宝座,还拥有一大批门生和旧部,遍布朝廷内外。到了隆庆皇帝快不行的时候,他拉着高拱的手,深情地说:“朕把整个国家都托付给你了。”
隆庆帝一直到去世,都对高拱有着十足的信任。按这势头,到了后面的万历时期,高拱肯定是内阁里那个挑大梁的首辅大臣,没得说。

不过高拱有个大问题,那就是他自视甚高,脾气又急,除了张居正,谁他都看不上,这样一来,肯定得罪了不少人,万历小皇帝身边的红人冯保就是其中之一。
冯保起初对和高拱交朋友挺上心的,但高拱对他并不怎么感冒。特别是冯保一门心思要拿到司礼监秉笔太监那个位子,高拱还老拦着他,这一来二去的,两人算是彻底结下梁子了。
隆庆元年那会儿,冯保就已经是东厂的提督,还管着御马监,在宫里他算是老二,就排在司礼秉笔太监后面。要是没啥变故,等那个司礼秉笔太监的位置一空出来,他就能坐上宫里头把交椅了。
不过高拱先提议让陈洪来当那个秉笔太监,接着呢,他又把位置推荐给了排在他后面的尚膳太监孟冲。就这样,司礼秉笔太监的位置换了两次,偏偏就没冯保的份儿。这事儿让冯保对高拱心里头特别不满。
跟高拱不对盘,那就得找别的帮手,挑来挑去选中了张居正。在明朝,要想让内阁的提议生效,得靠司礼监的秉笔太监盖章批准。这种规矩下,内阁和司礼监自然而然地就走到一块儿了。一边想当内阁老大,另一边想当秉笔太监,俩人想法不谋而合。

隆庆皇帝病得厉害那会儿,张居正偷偷背着高拱,悄悄搞定了一些事儿,然后封得严严实实的,给冯保送了过去。这事儿吧,还让高拱给发现了,他急着想把东西要回来,可东西已经进了宫里头,没辙了。高拱只好直接找张居正开腔,问他为啥要和宫里的太监勾结。张居正心里头虚,没办法,只能红着脸给高拱赔了个不是,这事儿也就这么算了。
隆庆皇帝去世后,他留下的遗嘱里,除了让高拱、张居正、高仪帮忙照顾小皇帝,还提到了一个内监,但就是没写明是哪个内监。高拱心里琢磨着,这内监八成是孟冲。可隆庆皇帝刚咽气没多久,大概也就俩小时吧,宫里头就下了道命令,把孟冲那个管事儿太监的位子给撤了,换上了冯保。
这事儿让高拱他们心里很不爽,礼科给事中陆树德就直接上书说了,隆庆帝要是真想换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为啥不在快不行前几天提,非得等到快咽气了才说呢?那时候遗命一大堆,哪还有功夫管内宫的人事调动啊?就算管,咋就偏偏换上了冯保呢?
这件事说明,冯保能坐上司礼秉笔太监的位置,张居正暗中帮了大忙,还承担了不小的风险。但这份付出是值得的,没多久,冯保就给张居正回馈了一份厚礼。

隆庆六年五月二十五,隆庆皇上刚离世,高拱心里头特别难过。难受到不行的时候,他在内阁屋里头,就随口嘀咕了一句:“太子才十岁,这天下可咋管啊?”
高拱的想法是,一个才十岁的太子,哪能管得好整个天下呢?他挺为大明的未来发愁的。
不过,当冯保把这事儿跟两宫太后还有万历小皇上说的时候,他就换成了这样的说法:“拱把太子当成十岁的孩子来看待,这哪像个君主的样子。”
虽然用词相近,但含义差得远了,在她们听起来,那句话就是说,一个十岁的孩子哪能治得了国家,太后和万历听了这话,怎能不惊讶?话说回来,万历没资格,难道高拱就有资格了?高拱随口那么一说,结果把太后和万历都给得罪了。

高拱压根没意识到,他的话早被冯保偷偷改了。他还一门心思地琢磨着,要把司礼监代皇帝批红的权力给夺回来,全拢到内阁手里。他挺有把握这事能成,毕竟自己是内阁的老大,票拟意见都由他把关,万历小皇帝才十岁,哪分得清啥是对啥是错,最后还不是得听他的。
为了提高赢面,他又去找了张居正和高仪这两位内阁大臣,让他们一起签字。张居正接过奏折,眼尖的他一下子就瞅见了高拱的一个疏忽,不过他没吭声。不光签了字,他还特地派人把奏折的内容给冯保送了过去。
那这个问题的关键在哪儿呢?高拱的做法就是彻底惹毛了宫里的太监们。他本意是想赶走冯保,但这么一来,连带着孟冲他们掌权的机会也给整没了,直接就把宫里太监们的晋升道路给堵死了,算是跟内宫太监们彻底结下梁子了。
太监整天围着皇帝转,皇帝想了解宫外的事儿,都得靠他们传递。高拱这么一来,等于是自己动手,把宫里可能帮他的人全给断了。以后要是有人背后说高拱坏话,他连个帮手都没有,说不定连冯保已经告他状了都不知道。再说,那份奏折一递上去,内阁就算是大权在握了,这也证明了冯保之前说的,高拱觉得自己治理天下是独一无二的。
高端的争斗其实挺直接,张居正就搞了个小把戏,让高拱不知不觉就掉进他设的陷阱里,他这一手轻松应对,真是玩得太巧妙了。
六月十六那天,大臣们都在朝会上,司礼监的人突然宣读了皇上的旨意,说高拱不再担任内阁首辅,得回老家待着去。这话一出,高拱立马就软了,差点没倒在地上,还好张居正眼疾手快,扶了他一把。张居正还挺够意思,还帮他申请了个坐驿站马车回家的福利。
不过高拱并不买账,他脑子一转就猜出了谁在背后给他使绊子。可眼下自己已被革职,啥也做不了,只能干瞪眼。
隆庆皇帝去世到高拱离职,也就短短二十多天时间。想想以前,徐阶为了把严嵩拉下马,足足花了二十年功夫。这回,张居正和冯保联手,几下子就把高拱给解决了,张居正也顺利坐上了内阁首辅的位置,但他可没打算就此罢休。

万历元年一月十九号早上上朝时,万历皇帝瞧见旁边有个太监慌慌张张的,举动挺鬼祟,站位也不对劲,就让人把他逮起来,送到东厂去查问。这哥们儿一开始说自己叫王大臣,是从戚继光部队里溜出来的逃兵。但到了东厂的地牢里,他才吐露了真话。
他其实叫章龙,原本是浙东章百户手底下的一个小跟班。因为一时贪心,偷了东家二十两银子,就逃到了京城。他打算投奔戚继光的部队,当个南军士兵,可惜因为个子不够高,没被选上。没办法,他只好想着混进皇宫,看看能不能找到别的出路。
其实这案子挺直接的,但张居正一听,就跟冯保说,能借这机会把高拱给扳倒。冯保动手脚后,案子就变成了章龙受高拱指使,想进宫杀皇帝。为了让高拱栽个大跟头,冯保还跟章龙打包票,只要他认了这事,不光能保命,还能捞个小官当当。为了让这案子更像真的,冯保还特地找人教章龙怎么去冤枉高拱。
冯保不光在大牢里冤枉了高拱,还暗中让东厂的手下跑到高拱的老家,把他家里人给抓了起来。另一边,张居正可没闲着,他直接上书要求找出这案子的幕后黑手。
这事儿在朝廷里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但大家都觉得高拱是被冤枉的,纷纷为他打抱不平。就连被关在牢里的章龙,也不想再继续诬陷高拱了。结果,这案子最后就草草地以处决章龙收了场。
张居正和冯保之前合力,短短二十天内就让高拱下台了。可这才半年光景,他们弄出个莫名其妙的冤案,结果不但没杀掉高拱,自己还丢了脸,更是让高拱对他们恨得牙痒痒,真是亏大了。
这真的划算吗?其实张居正和冯保心里清楚,一个凭空捏造的指控哪能要了张居正的命。他们这么干,目的就是要借这事儿,把高拱的政治路给彻底堵死。
高拱虽然丢了官,但他才六十岁,不算老。你看以前那些被撤职的首辅,像翟銮、夏言、严嵩他们,哪个不是做过不止一次?而且高拱手底下有那么多的门生和老同事,他东山再起的机会大得很。要是他真的回来了,那张居正和冯保可就得倒霉了,他们肯定不想看到这个局面。
因此,这事儿的目的就是要拦住高拱重新得势的路子。其实,这案子并不是真要高拱的命,这么大动静主要是为了给太后和万历看,好让他们心里觉得高拱“可能”会干出刺杀皇帝的事儿。这样一来,就算他门生故吏满天下,政治名声再响亮,高拱也别想再回官场了。
这是一场教科书式的权力较量,张居正和冯保先是联手把高拱给拽了下来,然后又通过“王大臣案”彻底断送了他的仕途,这手法就像是剃刀削眉,一点皮都不带伤的,真的是既精准又毒辣。

这件事对高拱打击特别大,他一直到死都心里放不下。快不行的时候,高拱写了四卷《病榻遗言》,把心里的怨气都写了进去。说到以前的好朋友,高拱给他的评价是“又当媒婆又装神弄鬼,吹笛子、眨眼睛、敲鼓弹琵琶,啥都来点”。
在政治圈里头,没啥同盟是铁打不变的,说到底都是利益至上。明朝那会儿,讲的就是永恒的权力斗争。原先那些看似牢不可破的政治伙伴,到最后也都得散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