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驻藏大臣选任方式进行深度分析,发现清会典对驻藏大臣“皆为特简”的记述是不全面的,另外还有军机处开列以及军机大臣保举、大将军题补的情况存在。选任部门涉及军机处、吏部和内阁。
因此,对于驻藏大臣人物的评定决不能简单地阐述忠奸两分法,应要深刻认识到清朝选任制度高度的贵族性、权力集中性以及首崇满洲的特质,而且以原职衔赴任、高养廉银、戴罪大臣发配边疆、以及民族隔离政策的制度安排才是加速驻藏大臣腐化的重要制度缺陷。

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清军入藏平定准噶尔军间接催生出为稳定青海蒙藏部落控制的西宁办事大臣,以及初为善后事宜钦派的赴藏办事大臣。驻藏大臣的建立之始为先模仿西宁办事大臣制度,再借鉴新疆将军—参赞大臣—办事大臣体系固定化后政教兼管的回疆事务参赞大臣。
之所以驻藏大臣的发展历程如此曲折,既与西藏本土政教合一体制以及农奴制的根深蒂固有关,又与清朝的内外形势息息相关。驻藏大臣的选任要求与选任特点自然也随着驻藏大臣的发展历程,经历了由临时到常设、由以情报奏递与军事抚驭到稳定内部政教、由武职属性较重到文职属性为主的转变。

1725年清军平定青海罗布藏丹津叛乱后,西宁卫改为西宁府,同时设置青海办事大臣(即西宁办事大臣)管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受此影响,1727年卫藏战争后清廷也开始对西藏派遣办事大臣。至18世纪30-50年代,清朝主要军事重点在西北与外喀尔喀。因此这一时期大部分驻藏大臣曾有驻扎新疆或蒙古办事的经历。且从具有驻藏经历的边臣地区来看,驻藏大臣也是以青海、喀尔喀蒙古以及畿辅等地区为主。

准噶尔蒙古平定后,在喀尔喀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去世使得定边左副将军授权与制衡变得日益重要。此后为稳定清、俄、喀尔喀蒙古的关系,清廷借鉴在青海、西藏和新疆驻防大臣体系的设置,于1758年始设蒙古库伦办事大臣,1761年设科布多参赞大臣,1762年又设满洲库伦办事大臣,形成定边左副将军(1733)与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1736)、库伦办事大臣、科布多参赞大臣三方牵制喀尔喀蒙古的局面。
在平定策妄阿拉布坦侵藏的准噶尔军队以及罗布藏丹津叛乱后,清廷断绝了西藏同准噶尔蒙古和青海蒙古的联系。加之鉴于第司擅政的不良影响,因此在维持西藏政教合一体制的前提下,在藏内推行僧俗噶伦联合统治的制度。但后因俗官势力膨胀(如颇罗鼐等)压制了驻藏大臣以及系统,反而延缓了清朝在藏推行类似于西宁办事大臣的制度改革,最终引发了朱尔墨特那木扎勒事变。

1751年颁布《藏内善后章程十三条》虽规定了驻藏大臣监督政教、防准保藏的权力,但由于僧俗贵族势力再次灵活地渗入系统,导致驻藏大臣逐渐因为决策范围单一(中央批准事务以及驿站等事务的控制)、正副大臣制度缺失与横向机构短缺而陷入孤立。再者,对宗教事务的忽视,则导致地方教派势力的跨区域增长的潜在影响,如噶举派在巴勒布和金川土司地区势力扩展、主巴噶举在拉达克王室和不丹的传播、宁玛派在哲孟雄的传播。
还有宗教僧人参政前西藏地方事务的代理人制度缺乏的问题。七世宗教僧人去世后,西藏政教势力逐渐倾倒向摄政。朱尔墨特那木扎勒叛变让清廷意识到在西藏建立常备军队的重要性,以及以驻藏大臣体系限制僧俗权力的重要性。但驻藏大臣控制西藏政教势力结合的尝试(1751)也无疑为回疆伯克制政教分离的改革(1760)提供了反向经验。

这一时期的驻藏大臣制度因颇罗鼐家族主掌西藏政教事务而发展迟缓,因此主要集中于军事奏报、粮务转运与监督藏军方面,未能对藏内民生或政教事务有所干涉。该时期驻藏大臣的选任来源也受频繁军事活动影响,以都统副都统、部院侍郎和散秩大臣为主。
从选任程序上来看,由于涉及机密事务以及军事活动较多,因此该阶段驻藏大臣的选任主要以特简为主,选任部门也主要以军机处为主。从任职机制来看,驻藏大臣的权力尚未完善,自1740年开始,因封赐噶伦以及驻藏大臣原衔兼任的弊端,清廷始给予驻扎西藏办事大臣以副都统衔(正二品),来统驭藏内僧俗贵族。

1747年改称不分正副的“西藏办事大臣”,至1749年开始定员二人并注意关防职掌权力的区分。因此自钦差大臣派驻西藏一直沿用不固定的钦差大臣关防。1751年,钦差大臣关防的使用成为定制。至少从1754年8月开始使用驻藏大臣关防,实际上仍是固定化的钦差大臣关防。驻藏大臣官防采用文职属性的尚方大篆,表明乾隆帝对于驻藏大臣的设想,并不是简单地类比于以武力镇守的其他驻防办事大臣,而是将其作为文官系统中的地方驻扎大臣来主持西藏地方政教事务,并给予西藏地方一定的自主权。
驻藏大臣的议叙与荐举制度、以及监察制度尚未成形,处分与开复机制更是缺乏,加之驻藏大臣对藏内政教事务直接干涉不多,如此长期下去,若不区分正副大臣(1749年始区分职掌关防权力)以及同驻办事地点(1751年迁往撒木朱康撒尔后始分居)就很容易滋生舞弊与贪腐行为。因此在选任制度方面借鉴同样处于军事前沿的哈密汉城、满城的驻扎大臣,或军事缓冲区的西宁办事大臣反是正常。

18世纪60-90年代,乾隆皇帝对于回疆的设想本于准噶尔的经验。1在平定回部叛乱时,率先开始应用固定化将军—参赞大臣—办事大臣体系的军府制设置,并逐渐开始了对伯克制政教分离与土官改流官的改革。在西北和回疆相继平复后,清廷于1762年设置伊犁将军作为新疆最高的行政与军事长官总揽新疆事务,形成了伊犁将军镇守伊塔地区、乌鲁木齐镇守东路乌鲁木齐地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节制南路八城的格局。
1765年乌什回民不堪阿奇木伯克与驻扎大臣剥削,爆发人民起义。事后,乾隆帝在乌什增设了各回城事务参赞大臣,也注意对驻扎大臣和伯克勾结的管理。1789年后,乾隆帝对驻藏大臣和高级僧俗贵族的勾结也十分警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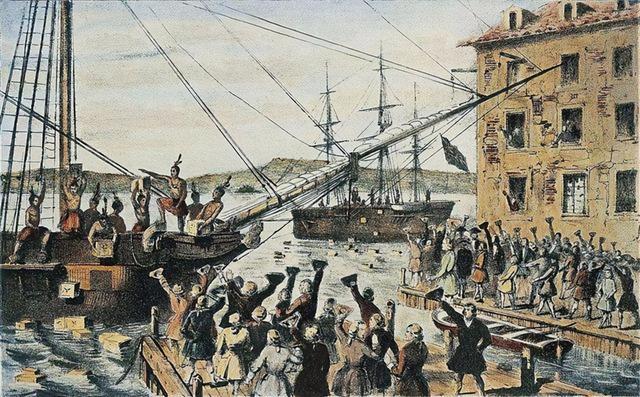
廓尔喀战役后,掌管地方政教权力的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便成为驻藏大臣权力改革的最佳参照对象。18世纪80-90年代,则多倾向选派具有任职伊犁经验的伊犁领队大臣、伊犁参赞大臣与伊犁将军赴藏。
18世纪60-90年代驻藏大臣的调转开始向中西部(如宁夏、陕甘、四川、云贵)和东南(如福州、台湾等)方向转移。一方面,这与八旗驻防重心转换有关。乾隆中后期在重点防守畿辅的同时,也经历了八旗驻防体系形成、八旗汉军编入绿营以及由重东南到重西北(西和北)的转移。另一方面,也与清缅战争(1765-1769)、第二次金川战役(1771-1776)、清越战争(1788-1789)、平定台湾叛乱(1787-1788)的战争需要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