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声明:本人所有行文提及的“中华文明”,特指“中华古代文明”,即从轩辕黄帝继位的上古时期开始计时,至封建王朝最后一任王朝清朝末代皇帝退位的1912年为止,时间跨度4600年,与当代中华文明没一点关系。
文明:一度被中华老祖宗解读为礼仪,用以区别于“禽兽”。老外因为说话很直,办事简单粗暴,常被认为是“蛮夷”
作为历史最为悠久的民族之一,同时也是最有思想的民族,中华民族4600年的历史长河中在不断与巍峨的世界打交道的同时,也在不断丰富自己独特的思想,提出了很多用于解决纷争和夯实“家天下”的治国思想。

儒家思想因其语言华丽、上纲上线,以及“天命所归”等观点,在满足了中华民族无限想象力的同时,也为统治者所青睐。自汉武帝之时异军突起,成为了治国致仕的不二思想,影响后世2000年。
在儒家思想主导之下,中华民族有了礼仪之邦的自豪感,据此我们有了傲视周边游牧民族的资本;在儒家思想的引领下,我们对文明的理解走向了一条“独孤求败”之道:物质生活被藐视,外表的仪态礼仪被奉为判别文明的唯一标志。
《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中的“野”指的是野人,通俗说来就是举止粗俗、说话直白;“史”指的是流于虚饰的矫揉造作之言行。

站在现代文明的角度: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要物质生活达到一定程度,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生活富足了,“腹中未消化的鱼肉”多了,人自然也就会注意自己的言行,言行举止也就文明了起来。
比方说对比我之前和现在住的小区。一个业主群里面天天有人在撕心裂肺地呐喊,不是怪楼上敲东西,就是辱骂物业吃肉不吐骨头,按照中华文明标准,显然属于粗鄙的野人行径;
反之,我现在住的这个小区,业主群里几乎没听到什么辱骂声音,反倒是客客气气的感谢声音此起彼伏,出现分歧也以“请”、“不好意思”化解。我们买的东西放在路边一夜,也无人拿。
之所以两个小区文明风尚相差如此之多,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物质生活有没有上一档次,绝非无视物质实际而盲目追求外表上的文明礼仪的“克制”。

但在孔子看来,文明的特质不在于物质生活层次的高低,而是如何维持文质平衡的君子模样。故而孔子无视物质生活实际,极端崇尚颜回的“安贫乐道”作风,对于如何不野蛮又不流于虚饰的微妙平衡,则投入了大量精力,显然是有违人性的做法。
也正是因为孔氏思维影响后世2000年,导致我们对西方充满了鄙夷之态:在我们物质生活领先于对方时,我们讥笑他们衣不遮体、食不裹腹;在他们通过科学利器实现了物质生活大爆发时,我们又嘲笑他们是说话直白、办事粗鲁的“野人”。
总之他们就是“不开化”的蛮夷,与孔子立定的文明标准相差太远。据此,甚至有人得到一个结论:全世界就咱们是文明之人,这也是儒家“平天下”引发的“唯我独尊”导致的后果。

被“绑架”的中华文明:最温柔的语言,干最狠的事,难道这就是我们引以为傲的文明?
圣人尚且如此,以礼仪之邦自居的中华民族自然不能落后,自此中华文明走上了一条“孔乙己”式的文明之路:即便生活再糟粕,却要穿长衫;
即使没钱喝酒,不惜背地里偷窃,也要跟着长衫们一道“文明喝酒”;当被讥笑为“偷”,文明人设崩塌时,却用“窃”不是“偷”来为自己的“文明”做法背书,这就是无视物质实际、盲目追求仪表上的“文明”导致的恶果。
故而,原本武力值爆表、重于开拓实际的中华文明被道德绑架了,“偃武修文”、“刑不上大夫”,对于“空谈误国”的读书人全方位保护了起来,沉湎于仪表和语言编制的“文明”世界中。

这也使得中华文明走上了另一条“双面之路”:用最温柔的语言,干最狠的事。
带头人依旧是被奉为圣贤的孔子。在教授的弟子当中,有一个不喜欢畅谈理想而追求实际的樊迟。他不问周礼问世俗,不问治国问种菜,“请学于稼,请学于圃”,这让孔子很是无语。
当着樊迟的面,孔子“强力克制”,表现出了超然的文明气质:我不如老农,我不如老圃。但当樊迟转身离去时,孔子终于爆发了,当着子路的面将樊迟好一输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随即斥责樊迟为“没有出息的小人”。

圣人尚且如此,其他以此为榜样或者为挡箭牌的野心家更是“有恃无恐”,于是当着受害者的面说着最温柔的语言,但在背地里却干着最狠最恶毒的事;表面上对人爱护有加,背地里却恶言相向的事比比皆是。
在此“文明”风向引导下,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明明两个人是死敌,但是在公众场合往往表现出了“你好我好”的和谐融洽场面,但在背地里都对对方下死手,一旦一方占据上风之后,得胜的一方终于露出獠牙,将对方“诛九族”、“斩草除根”。
难道这就是我们以引为傲的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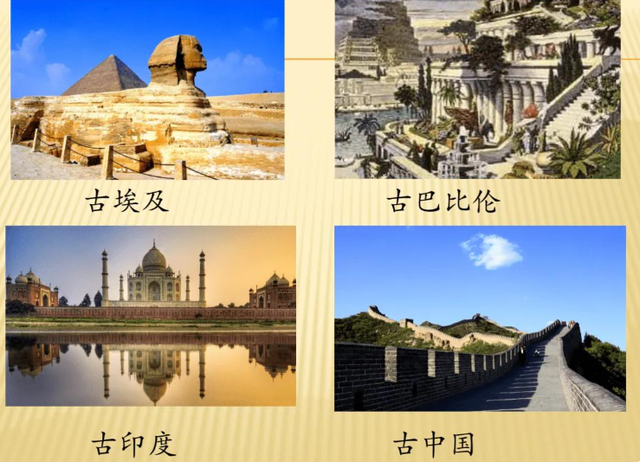

自霉体好蠢洁哦,收了倭円还是米刀?去了解一下犹太教基督教神棍们都干过啥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