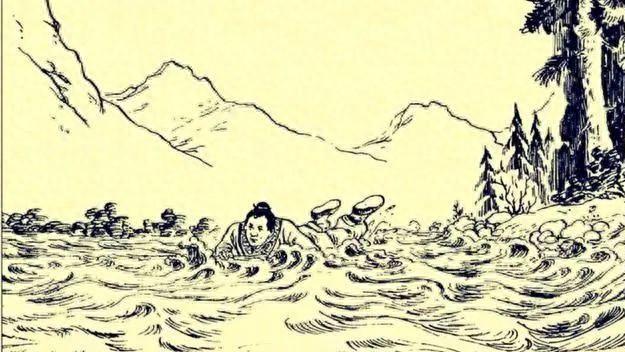清明时节的细雨像绣花针似的,密密地扎在青石板路上。崔文远收起油纸伞,在自家伙计诧异的目光中,悄悄从绸缎庄后门溜了出去。他今天特意换了身粗布衣裳,连平日里不离身的玉佩都摘了下来。
"东家,您这是..."账房先生老周欲言又止。
"我去趟码头验货,有人问起就说我染了风寒。"文远压低声音,眼角瞥向二楼账房——父亲崔老爷正在那里查账。
转过两条街,文远闪进一家茶楼,选了张临窗的桌子。从这个角度,正好能看见对面仁和药铺的全貌。他叫了壶龙井,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桌面。茶还没上来,药铺门口就出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他的妻子柳如嫣。
如嫣今天穿了件藕荷色衫子,鬓边只簪了支银钗,比平日朴素许多。她左右张望了一下,快步走进药铺。文远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了。他数到二十下,果然看见药铺伙计张三笑嘻嘻地迎出来,递给她一个油纸包。
"客官,您的茶..."小二话音未落,文远已经扔下几个铜钱冲了出去。他远远跟着妻子,看着她没有直接回家,而是绕到城西的破庙附近。更奇怪的是,父亲崔老爷竟从庙里走出来,接过那个油纸包,还拍了拍如嫣的肩膀!
文远站在巷子口,浑身发冷。三个月前,他还是崔柳两家联姻的受益者——崔家的绸缎庄配上柳家的绣坊,简直是天作之合。更何况新过门的妻子柳如嫣容貌秀丽,一手刺绣功夫名满苏州城。可自从上个月父亲染了风寒,家里就处处透着古怪。
先是如嫣突然开始频繁出入药铺,再是父亲总找借口支开他,现在竟发展到两人私下相会!文远想起昨夜如嫣梳妆台抽屉里那方绣着鸳鸯的帕子——角落里分明绣着个"张"字。
"崔少爷?"一个声音把他拉回现实。绸缎庄的老主顾李员外正疑惑地看着他,"您怎么这身打扮..."
文远勉强寒暄几句,匆匆回家。经过父亲书房时,他听见里面传来如嫣的声音:"...药性太烈,恐怕..."门缝中,他看见父亲竟握着如嫣的手!
当晚,文远在卧房里堵住了如嫣:"今日你去哪了?"如嫣正在卸簪环,闻言手一抖,珠钗掉在地上:"去...去绣坊取了新花样。"
"是吗?"文远从袖中掏出那个油纸包——他趁如嫣不备从她妆奁里偷出来的,"这是什么?"打开一看,是几味罕见的药材。
如嫣脸色煞白:"这是...给父亲调理用的..."

"哪个父亲?"文远冷笑,"你爹去年就过世了,难道是说...我爹?"
如嫣突然哭了,却仍不肯解释。文远甩门而去,彻夜未归。第二天一早,他带着两个家丁直奔仁和药铺,却被告知张三告假回乡了。更蹊跷的是,父亲崔老爷也不见踪影。
"少爷,老爷一早就出门了,说去杭州查账..."管家的话还没说完,文远就看见如嫣的贴身丫鬟小翠鬼鬼祟祟地往后院溜。他悄悄跟上,竟在小翠手里发现了张三写给如嫣的信笺!
"...三日后老地方见..."文远读着这行字,眼前发黑。他原想当场发作,却突然改了主意——他要人赃俱获,让这对奸夫淫妇无可抵赖!
接下来的三天,文远表面上恢复了平静,甚至对如嫣和颜悦色起来。暗地里,他买通了药铺的小学徒,得知张三根本没回乡,而是在城西租了间屋子。更令他心寒的是,父亲崔老爷这几天总在傍晚时分出门,说是去会友,马车却总往城西方向去。
第三天傍晚,文远带着四个膀大腰圆的家丁,直奔张三的租处。那是个僻静的小院,院门虚掩着。文远示意家丁埋伏在四周,自己蹑手蹑脚地靠近正屋。透过窗纸,他清楚地看见如嫣的背影,她对面坐着个男人,两人之间的小几上摆着——那个熟悉的油纸包!
文远一脚踹开门,眼前的景象却让他愣住了:屋里除了如嫣和张三,父亲崔老爷竟然也在!三人围坐的桌上摊着几味药材,还有本医书。如嫣惊叫一声,手中的茶盏摔得粉碎。
"好啊!"文远气得浑身发抖,"三个人...你们..."他突然注意到父亲异常红润的脸色和桌上那碗黑乎乎的汤药,一个可怕的念头闪过脑海,"难道这药是..."
崔老爷猛地站起来:"文远!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是怎样?"文远抓起医书砸在地上,"你们三个在这里做什么?"
张三突然跪了下来:"崔少爷明鉴,小的和少夫人清清白白..."
"闭嘴!"文远一脚踹翻小几,汤药泼洒在地,冒出诡异的气泡,"我要去县衙告你们通奸!"
如嫣闻言,直接晕了过去。崔老爷慌忙去扶,却被文远一把推开。场面一片混乱之际,谁也没注意到张三悄悄溜走了。
第二天,整个苏州城都在传崔家的丑事。文远一纸诉状递到县衙,告妻子柳如嫣与张三"私通苟合",连带父亲崔老爷也成了纵容包庇的帮凶。
升堂那天,县衙外围得水泄不通。如嫣脸色惨白地跪在堂下,崔老爷则不住地叹气。当县令问及通奸证据时,文远呈上了那方绣着"张"字的帕子、往来书信和家丁的证词。
"被告有何辩解?"县令惊堂木一拍。
如嫣只是垂泪不语,崔老爷却突然重重磕了个头:"大人明鉴,此事...此事都怪老朽!"
县衙大堂内,崔老爷重重叩首,额头抵在冰冷的青砖上,声音沙哑:"大人明鉴,此事全因老朽而起,与儿媳如嫣无关!"
县令眉头紧皱:"崔老爷,此话怎讲?"
崔老爷抬起头,老眼含泪:"老朽...患有隐疾,多年来靠一味特殊药材续命。"他颤抖着从怀中掏出一张泛黄的药方,"此药方乃二十年前一位游方郎中所留,需用'血灵芝'入药。这些年,血灵芝几乎绝迹,唯有仁和药铺的张圣手还存有一些..."
堂下一片哗然。文远愣在原地,他从未听父亲提起过什么隐疾。
"三个月前,老朽病情加重,张圣手年事已高,便让其孙张三暗中为我配药。"崔老爷看向如嫣,眼中满是愧疚,"如嫣心细,偶然发现此事,便主动帮忙取药..."
如嫣此时已醒转,泪流满面地补充:"儿媳见公公每次服药后痛苦不堪,便查阅医书,想找替代药材减轻药性。那日破庙相会,实则是张三带我去见一位懂药性的老和尚..."

文远脑中嗡嗡作响,突然想起那方绣帕上的"张"字,急忙从袖中取出细看——角落里绣的竟是"张大夫"三个小字!
"那...那些书信..."文远声音发颤。
张三此时从人群中走出,跪在堂前:"回大人,那些所谓'情书',实则是药方讨论。小人祖父曾受崔老爷大恩,这才冒险配药..."
县令命人取来信件细看,果然都是药材名称和用量记载。其中一页还画着血灵芝的图样,旁边批注"药性太烈,需配甘草调和"。
文远如遭雷击,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父亲...如嫣...我..."
崔老爷长叹一声:"都怪老朽!当年如嫣父亲救我一命,如今我本想让文远娶她过好日子,却害她蒙受不白之冤..."
原来二十年前,崔老爷经商途中遇劫,是柳如嫣的父亲拼死相救。后来柳家落魄,崔老爷便以联姻之名报恩。谁知婚后不久,他发现如嫣竟认得血灵芝——这正是她父亲当年为救崔老爷而中的奇毒所需解药!
如嫣哽咽道:"父亲临终前告诉我,崔伯伯体内余毒未清,终会发作...我嫁过来后见公公病症,便知是时候到了..."
堂外围观的人群中,一位白发老者突然高声道:"老夫可以作证!"众人让开一条路,正是隐居多年的张圣手。
"崔老弟当年中的是'七日断魂散',老朽穷尽毕生所学,也只能用药压制。"张圣手向县令拱手,"这丫头为减轻药性,翻遍医书,还亲自试药,手上全是针眼..."
如嫣慌忙将手缩回袖中,却被县令命人查看。只见那双绣花能手上,果然布满细小的针痕——那是她为测试药性,用银针自刺的痕迹。
文远见状,再也忍不住,重重磕了三个响头:"娘子,我..."
如嫣却扶住他,轻声道:"不怪夫君,是我太过谨慎,反惹猜疑。"
县令拍案判决:"本案已明,柳氏贞洁可鉴,崔文远诬告发妻,本应重责。念在事出有因,且夫妻情深,罚银百两修葺县学。退堂!"
回家的马车上,崔老爷终于道出全部真相。原来他当年中的毒已入骨髓,血灵芝虽能续命,却会带来剧痛。如嫣发现后,暗中寻访减轻痛苦之法,这才有了与张三的频繁接触。
"为父怕你担心,一直隐瞒病情。如嫣为保全我的颜面,宁可被你误会也不解释..."崔老爷老泪纵横。
文远羞愧难当,握住如嫣的手:"娘子,我..."
如嫣掩住他的口:"夫君不必自责。其实..."她脸一红,"我本打算等找到完善药方,给你个惊喜..."
原来如嫣在古医书中发现,血灵芝配合几味普通药材,不仅能解毒,还能助孕。她悄悄准备多时,想在崔老爷寿辰时宣布这个喜讯。
三个月后,崔家张灯结彩。崔老爷的六十大寿宴上,如嫣当众宣布有喜。更令人惊喜的是,张圣手带来好消息——他已找到彻底解毒的法子。
宴席散去,文远在院中追上正在收拾药材的张三,深深一揖:"张兄,先前多有得罪..."
张三连忙还礼:"崔兄言重了。其实..."他压低声音,"我接近如嫣姑娘,还有一事相求。"
原来张圣手年事已高,看中如嫣在医药上的天赋,想收她为关门弟子。张三此番频繁接触,实为考察她的品性。
文远大笑:"这是好事啊!"

从此,崔家绸缎庄的少夫人成了张圣手的弟子,不仅调理好了崔老爷的顽疾,还开创了"药绣"——将药材融入绣线,制成有安神功效的香囊绣品,名扬江南。
一年后的满月宴上,崔老爷抱着孙子笑得合不拢嘴。小娃娃手腕上系着条红绳,绳上穿着颗血灵芝雕的小葫芦——那是如嫣用边角料做的。
"老爷,药铺送来贺礼。"管家捧来个锦盒。
盒中是张圣手亲笔所书"医绣双绝"的匾额,落款处还附了张三的婚帖——他要娶的是如嫣的丫鬟小翠,那个当年帮忙传递"情书"的姑娘。
文远搂着如嫣笑道:"这下真是亲上加亲了。"
如嫣倚在丈夫肩头,望着满院宾客,忽然瞥见墙角闪过一道熟悉的身影——是那个曾给他们带来无数误会的老和尚,正笑眯眯地冲她点头。
原来这一切,早在那日破庙相遇时,就被老和尚算准了。他送给如嫣的签文上写着:"鸳鸯错配实非错,柳暗花明又一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