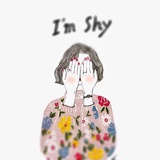1939年6月,老蒋在重庆第二次召见王耀武,提拔其为74军军长。两人足足谈了一个半小时,这在老蒋接见下属将领乃至黄埔嫡系的场合中,是不多见的。
期间,王耀武提到了自己的心腹爱将邱维达,夸他深沉果敢、作战有勇有谋,还曾荣获“云麾勋章”。
老蒋一听说是“云麾勋章”,来兴趣了,问道:“此人现任何职?”
王耀武说:“作战参谋。”
此外,王耀武还告诉老蒋,邱维达曾经建议加强下级军官平常训练工作,成立内部军官训练班。
老蒋觉得邱维达是一个好苗子,就对王耀武说:“这个人不错,不要当什么作战参谋了,你回去跟他讲,让他来陆大进修。至于他的职务嘛,由你来安排。”

邱维达这个人不简单,湖南平江人,黄埔四期毕业,自1928年春便开始在王耀武麾下任职,是74军所有高级将领中最早追随王耀武的人,其亲信程度可见一斑。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邱维达时任74军第51师第151旅第306团上校团长,率部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和兰封会战,期间升任第151旅副旅长。
1938年7月,第58师第172旅旅长一职出现空缺,王耀武有意让邱维达过去接任。
不过,直接将自己的嫡系副旅长空降到军长俞济时麾下的主力师去当旅长,这在军中是比较犯忌讳的做法。尤其是第58师,是俞济时亲手组建的嫡系部队,师长冯圣法更是俞济时的心腹爱将,为人也颇为强势。如果王耀武的人直接“骑”到冯圣法的头上,必然会引起冯圣法的强烈不满和抵触,不仅邱维达的日子不好过,甚至可能影响到王耀武与俞济时、冯圣法之间的关系。
王耀武显然考虑到了这一点。他深知,这件事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能由自己直接出面去向俞济时“强推”,那样目标太明显,也太容易让冯圣法将矛头指向自己。必须制造一个看似“顺理成章”的过渡,让邱维达的任命显得不那么突兀。

于是,王耀武不直接向俞济时推荐邱维达去当旅长,而是先运作一番,说动俞济时,将邱维达从自己的部队调到第七十四军的军部去任职。军部参谋、处长之类的职务,虽然未必有实权,但级别上去了,更重要的是,进入了军部的视野,成为了“军部的人”。这样一来,将来再由军部“下放”到下面的师旅担任主官,就显得名正言顺,不那么扎眼了。
为了实现这第一步,王耀武同样没有亲自出马,他派自己的心腹私下里找到了俞济时的副官,承诺若能促成此事,将来必有回报。
俞济时的副官被王耀武的“诚意”打动,不失时机地、旁敲侧击地为邱维达“美言”起来。最终,俞济时同意任命邱维达为第58师第172旅旅长。
对于这个结果,师长冯圣法心中自然是极为不爽。他觉得自己麾下的主力旅,竟然被一个“外人”,而且还是王耀武的亲信占据了。
但是,任命毕竟是顶头上司俞济时亲自下达的,冯圣法虽然心中憋着一股火,但碍于俞济时的面子,他不好公开发作,只能暂时捏着鼻子认了。
然而,冯圣法绝非善茬。他对这个“空降”来的旅长邱维达,必然是处处提防,暗中观察,甚至可能在寻找机会,想要将这颗“眼中钉”拔掉。因此,邱维达的日子,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好过。

1938年7月下旬,南浔路战役打响。
当时,侵华日军在华中地区发动猛烈攻势,继占领安庆之后,又于7月下旬从长江南岸的姑塘等地强行登陆,迅速攻占了九江。随后,日军主力沿南浔铁路(南昌至九江)向南大举进犯,兵锋直指华中重镇南昌和武汉。中国军队紧急调集重兵,依托庐山有利地形和南浔铁路沿线据点,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武汉会战(南浔路作战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俞济时指挥的第74军(特别是其麾下的第58师),正是防守南浔线中段德安地区的主力部队之一。面对日军的汹汹攻势,军委会下令增强当面之敌的防御力量,要求第58师火速开赴德安东北方向的黄老门一线,增援负责该地段防御的粤军名将李汉魂指挥的第64军。
师长冯圣法接到命令后,立刻向麾下的两个旅——邱维达的第172旅和劳冠英的第174旅下达了作战指令:“第172旅迅速占领黄老门以西高地,构筑工事,阻击敌人;第174旅迅速占领黄老门以东高地,与172旅形成掎角之势,坚守阵地。”
这个命令本身,从军事地图上看,似乎并无不妥。黄老门东西两侧的高地,确实是控制该区域的关键要点。然而,冯圣法在下达这个命令时,却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战场实际情况——部队的初始位置和行军路线。

其时,邱维达的第172旅主力正驻防在德安县城的东面地区,而第174旅则驻防在德安县城的西面,黄老门位于德安东北方向。由于南浔铁路此时已被日军炮火破坏或为阻止日军南下已被我军自行破坏,部队只能沿铁路两侧的简易道路或乡村小径徒步行军。更为关键的是,德安以东地区紧邻庐山山脉南麓,地形复杂,道路稀少,几乎无路可走。
这意味着,要想到达指定的黄老门以西阵地,驻扎在德安东面的172旅,实际上需要向西穿过德安县城或绕一个大圈子;而驻扎在德安西面的174旅,要想到达黄老门以东阵地,也需要向东行军。这两支部队的行军路线,不可避免地要在德安附近或通往黄老门的某条主要道路上发生交叉。
对于两支急于奔赴前线、抢占阵地的部队来说,行军路线交叉,极易引发混乱、拥堵甚至冲突。这是一个非常低级但却致命的指挥失误,冯圣法作为师长,在地图上“想当然”地划分了防区,却完全没有考虑到部队的实际出发位置和战场交通状况,为接下来的混乱埋下了伏笔。
接到命令后,邱维达和劳冠英两位旅长不敢怠慢,立刻率领各自的部队,星夜兼程,向黄老门方向急行军。
果然,正如冯圣法的“疏忽”所预示的那样,麻烦很快就出现了。两支部队在行军途中,不可避免地在某条狭窄的道路上“狭路相逢”。由于任务紧急,谁也不愿让路,加上夜色昏暗,指挥不畅,场面顿时变得混乱不堪。

更糟糕的是,走在前面的174旅的后卫部队,竟然将紧随其后的172旅旅部以及所属的第343团(主力团)给死死地堵在了后面。道路被辎重、人员挤得水泄不通,172旅的主力一时间寸步难行。
就在这混乱拥堵、进退两难的当口,前方突然传来了枪声,一股前出侦察或迂回穿插的日军小部队,竟然已经出现在了距离他们不远的山沟里。
情况万分危急,如果不能迅速抢占前方有利地形,一旦被日军抢先控制了制高点,后果不堪设想!
邱维达心急如焚,他的主力团被堵在后面无法前进,身边只有旅部的少量人员和特务排。他当机立断,命令特务排排长立刻率领全排士兵,不惜一切代价抢占前方那个关键的山头高地,控制局面,掩护后续部队展开。同时,他派人火速催促被堵在后面的第343团,排除万难,尽快赶上来增援。
特务排虽然奋勇冲锋,但在日军优势火力的攻击下,寡不敌众。还没等343团赶到,特务排排长便已中弹牺牲,旅部的参谋主任也身负重伤,高地眼看就要失守。
情急之下,邱维达将目光投向了堵在他前面的、隶属于174旅的后卫部队——第348团的第3营。他立刻派人前去联系该营营长,请求他们看在同属一个师、共同抗敌的份上,立刻出兵援助,先将面前这股日军打退,解救危局。

但那位营长,竟然以“邱维达并非我的直属长官,无权指挥我部”为由,当场拒绝了邱维达的紧急求援。
邱维达非常生气,却又无可奈何。他派去的参谋苦苦哀求,晓以大义,或许还搬出了师长冯圣法和军长俞济时的名头。最终,那位营长才心不甘情不愿地、象征性地派出少量兵力进行骚扰性射击,但根本不肯全力投入战斗。
就在这宝贵的救援时间被内部扯皮和消极应对所浪费的时候,后续的日军部队已经沿着铁路线快速南下增援。
等到172旅的第343团好不容易疏通道路,气喘吁吁地赶到战场时,为时已晚。他们还未来得及展开战斗队形,就被士气正盛、占据有利地形的日军一顿猛冲猛打。仓促应战之下,343团阵脚大乱,几乎是一触即溃,部队被冲散,伤亡极为惨重。
黄老门一线的防御,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遭遇战和内部协调的巨大失误,从一开始便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局面。虽然最终中国军队依靠顽强的抵抗,守住了德安一线,但172旅在初战中所蒙受的损失和挫折,却是不争的事实。

黄老门初战失利,伤亡惨重,总得有人为此负责,第74军军部下令彻查此事。
此时,师长冯圣法面临着一个微妙的局面。部队行军路线交叉引发混乱,这是他这个师长在下达命令时考虑不周、指挥失误造成的。但如果承认是自己的责任,必然会受到上峰的斥责甚至处分。而将责任推给一个自己本就不待见、又是“外来户”的旅长邱维达,似乎是一个既能“甩锅”又能“清除异己”的“一石二鸟”之计。
于是,在向军部汇报战况和调查结果时,冯圣法将所有的责任都归咎到了邱维达的头上。他指责邱维达指挥不力,未能及时抢占阵地;指责他擅自行动,拦截友军,导致部队混乱;甚至将343团被冲散、伤亡惨重也归结为邱维达未能有效掌握部队、临阵处置失当。总之,在他的描述下,邱维达成了导致黄老门初战失利、损兵折将的“罪魁祸首”。
至于他自己命令上的疏漏,以及那位174旅3营营长见死不救的行为,冯圣法却轻描淡写,完全隐瞒了过去。
军长俞济时收到的,自然是经过冯圣法“加工”和“包装”过的报告。他对邱维达本就谈不上什么深厚的感情,这次又确实吃了败仗,损兵折将。再加上冯圣法是自己的心腹爱将,俞济时自然更倾向于相信冯圣法的说法。
盛怒之下,俞济时下令撤销邱维达第172旅旅长一职务,另委派自己的另一位亲信将领廖龄奇接任172旅旅长。

邱维达,就这样成了这场指挥失误和内部倾轧的“替罪羊”。他不仅丢掉了好不容易得来的旅长职务,更背上了一个“指挥不力”、“贻误战机”的黑锅。在第58师,他自然是再也待不下去了,最后还是回到了老部队第51师。
当然,王耀武也不可能立刻就给一个刚刚受过军部处分的人安排重要的实职,那不符合规矩,也会引人非议,只好暂时委任邱维达担任了第51师司令部的一名作战参谋。
因此,王耀武在与老蒋会面时,才会极力推荐邱维达,邱维达得以进入陆大深造,毕业后重新回到第51师,担任旅长一职。
1944年1月,王耀武升任第24集团军总司令。关于参谋长一职,王耀武不放心别人,而是交给了邱维达。
次年三月,第四方面军成立,王耀武再进一步,升任第四方面军司令官,邱维达继续担任王耀武的参谋长。

不久, 湘西会战(也称雪峰山会战)打响。
战役前夕,最高统帅部对作战方案的制定慎之又重。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亲自偕同来华协助抗战的美军作战司令麦克鲁将军和参谋长巴特鲁少将,风尘仆仆地赶赴设在湖南安江的前线指挥部,与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及其幕僚们,共同研究制定最终的作战计划。
指挥部内,气氛严肃而紧张。中美双方的高级将领围坐在一起,面前摆放着各种情报分析和兵力部署图。
作为第四方面军的参谋长,邱维达负责首先汇报方面军司令部初步拟定的作战构想。邱维达在深入分析了敌我态势和雪峰山的地形特点后,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借鉴了三国时期魏国名将邓艾偷渡阴平、奇袭成都的作战方案。
邱维达说:“目前日军进攻态势已明,其主力正沿湘黔公路两侧,试图突破我雪峰山东麓防线,直扑芷江。我军若仅凭现有防线层层阻击,虽能消耗敌人,但恐难全歼其主力。属下认为,应效仿邓艾将军奇袭涪城之策,在正面坚守的同时,抽调一支精锐奇兵,行险而出,直捣敌后。”
他具体阐述道:“我建议,以一个加强军的兵力(至少三个师以上),从我军左翼的辰溪、溆浦山区隐蔽出发,克服险阻,向南迂回穿插,插入敌军的侧后方,直击其腰膂。而后挥师南下,截断敌军赖以生存的生命线——湘黔公路。如此,正面之敌顿失补给,军心必乱。我正面主力兵团再适时发起反攻,配合迂回部队,便可形成前后夹击、四面包围之势,将这股深入雪峰山的日军主力彻底围歼于此。”

邱维达汇报完毕,指挥部内响起了一片低低的议论声。陆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肖毅肃、副参谋长冷欣,以及第四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罗明理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他们认为,邱维达的方案过于冒险,迂回穿插的难度太大,变数太多,一旦失败,后果不堪设想。他们更倾向于采取一种更为稳健、也更符合常规战法的策略——中央突破,将日军压缩于雪峰山脉以西、资水以东的狭窄区域内,逐步分割围歼。
双方争执不下,都无法说服对方。作为最高决策者的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也感到有些为难。他知道,两种方案各有优劣,也各有风险。选择哪一个,不仅关系到战役的胜负,更关系到他个人以及整个国民政府的声誉。尤其是美方将领在场,若选择的方案未能充分发挥美械装备的优势,或者最终导致战役失利,这个责任可不小。
眼看会议陷入僵局,何应钦一时难以决断。心思缜密的邱维达看出了总司令的为难,也明白自己作为方面军参谋长,不宜在总司令部的高级参谋面前过于坚持己见。他找了个机会,以“需要核对一些情报数据”为借口,暂时离开了会议室,将最终的抉择权,留给了司令官王耀武和总司令何应钦。
邱维达离开后,会议室里的气氛略显尴尬。何应钦将目光投向了自始至终未明确表态的王耀武。

“佐民,”何应钦缓缓开口,语气中带着询问,“刚才两种方案,你都听了。依你之见,哪一个更切合当前战场的实际情况?更能克敌制胜?”
王耀武沉吟片刻,站起身,走到地图前,略作思索后,给出了自己的判断:“回禀总座,以学生愚见,邱维达参谋长提出的左翼迂回方案,虽然看似冒险,但更具主动性和决定性,也更能发挥我军兵力上的优势和对地形的熟悉。若能克服困难,出奇制胜,则可毕其功于一役。中央突破方案虽稳妥,但恐难彻底围歼日寇主力,战事或将迁延,于我消耗亦大。”
王耀武明确表达了对邱维达方案的支持。这并不奇怪,邱维达是他的心腹参谋长,方案很可能是在他的授意或认可下制定的。
但何应钦却有他的顾虑,他说:“邱青白(邱维达字青白)这个方案,要效仿邓艾偷渡阴平,那可是要钻山沟、爬险路的,我们刚刚装备的那些美式重炮、卡车,恐怕都派不上用场,甚至连部分轻型美械都可能因道路难行而受限。这次盟军的将领都在这里看着呢,我们若是选择了一个不能充分发挥美械装备优势的方案,万一战事再有个什么疏漏,这个责任可不轻啊!将来在盟军面前,我们也不好交代。”
何应钦的这番话,点出了问题的关键——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考量,还有政治上、尤其是对美关系上的考量。当时国民政府急需美国的援助,在作战方案的选择上,自然也要顾及美方的意见和装备效能。

紧接着,何应钦话锋一转,说:“佐民,你我不是外人,有些话我也不跟你绕弯子,讲那些官场上的虚文了。我这次是怎么坐上这个陆军总司令的位置,你应该比谁都清楚。(何应钦之前因史迪威事件等原因一度失势,后因滇西缅北反攻胜利,尤其是龙陵、松山等战役的胜利,才重新被启用,出任权力极大的陆总司令)好在我来的时候,头上还顶着一顶‘松山大捷’的光环帽子。现在到了你王佐民的地盘上打这一仗,结果如何,可是直接关系到我这顶帽子能不能戴得更稳,甚至能不能再添上一顶更亮眼的‘冠冕’啊。你总不能让我打了败仗,把这好不容易得来的帽子都给丢了吧?”
说到这里,何应钦还特意干笑了两声。
王耀武何等聪明,他立刻听懂了何应钦的潜台词:这场仗,你王耀武是前线总指挥,方案你来定,仗你来打,但打赢了,功劳有我何应钦一份,我这个总司令的位子才能坐稳;打输了,主要责任也得你担着,你得给我保证打赢。
王耀武立刻挺直身体,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斩钉截铁地回答:“总座放心,卑职明白,绝不辜负总座厚望!”
“好!我就要你这句话!”何应钦似乎松了一口气,将手中的决策权完全下放给了王耀武,“具体怎么打,你来下决心,需要什么支持,人、枪、粮、弹,只要我何某人能办到的,绝不含糊!我给你当后盾,豁出去了,反正我也是走下坡路的人了(指之前失势),还怕什么?”

王耀武知道,何应钦说的明显是气话。他立刻拿起电话,接通了在外面等候的邱维达:“青白,你马上回来,我们商议具体的操作办法!”
邱维达回到指挥部,得知总司令和司令官已经采纳了自己的迂回作战方案,精神大振。接下来,便是具体落实的关键环节——由谁来担当这支深入敌后的奇兵?
邱维达最初的建议是“一个加强军”。王耀武略作思索,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名字:“那就用第18军。”
第十八军,是陈诚“土木系”的核心主力,以能征善战、作风顽强著称。军长胡琏(字伯玉),更是黄埔四期毕业生中的佼佼者,精明强干,狡黠善战,但也以“会捞钱”、“贪财”而闻名。
听到王耀武点了胡琏的名,何应钦下意识地皱了皱眉头,问道:“胡琏?可是那个特别喜欢捞钱的胡伯玉?” 语气中明显带着一丝不以为然。何应钦与陈诚素来不和,派系倾轧由来已久,他对陈诚系统的部队和将领,自然也抱有成见。
王耀武当然知道何应钦的心思,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选择,替胡琏说了句公道话:“总座,胡伯玉虽然有些其他的毛病,但论带兵打仗,确实是一把好手。18军的战斗力,也是有口皆碑的。此次迂回穿插任务艰巨,非硬部队不能担此重任!”

何应钦沉吟了一下,最终还是同意了王耀武的意见,但仍不忘敲打一句:“那可是人家(指陈诚)的起家本钱,你王佐民要用可以,可得小心点用,别到时候把人家的宝贝疙瘩给折腾光了,不好交代!”
王耀武立刻立正回答:“有总座在此坐镇指挥,学生还有什么好怕的?豁出去了。”
何应钦听了,这才满意地笑了笑。
方案既定,将领选定。第二天清晨,邱维达便代表第四方面军司令部,与第18军军长胡琏进行了对接。
邱维达开门见山,将方面军的战略意图和迂回穿插的任务,言简意赅地向胡琏作了介绍,并特别强调了一句:“伯玉兄,这次方面军的重任,可是王司令官亲自点了你的将!”
胡琏也是个聪明人,一听便明白了其中的分量和风险。他摸了摸自己的头,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呵呵,司令官动动嘴,我们下面的人可就得跑断腿咯!这雪峰山里钻来钻去,可不是好差事啊!”
邱维达眉毛一挑:“怎么?伯玉兄不愿意?”
胡琏立刻收起玩笑的神色,正色道:“青白兄说哪里话,若是换了旁人下这个命令,我还真敢说个‘不’字,但在王司令官这里,没有二话。我胡琏和18军上下,绝不讲价钱。请司令官和参谋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他知道王耀武如今圣眷正隆,又深得何应钦信任,此时若不卖力表现,将来恐无好果子吃。

“好,有伯玉兄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邱维达赞许道,“我就知道伯玉兄是条明事理、顾大局的汉子!”
随后,两人就具体的行军路线、时间节点、协同信号、后勤补给等细节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磋商,并最终敲定了具体的执行方案。邱维达将与胡琏商定的方案,向王耀武和何应钦做了汇报,得到了批准。
事实证明,胡琏确实是一员能将,18军也确实是一支劲旅。接到命令后,胡琏说到做到,率领18军仅用三天便成功地插入了日军的纵深腹地,并与友邻部队协同作战,一举截断了日军赖以生存的咽喉要道——湘黔公路。
湘黔公路被截断,如同扼住了日军的脖颈。深入雪峰山区的近二十万日军顿时陷入了前有坚固阵地难以突破、后有奇兵断绝补给、侧翼又不断遭受打击的四面楚歌之境,军心大乱,攻势顿挫。
湘西会战,最终以中国军队的完胜而告终。此役,不仅彻底粉碎了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企图,保卫了芷江空军基地,更歼灭了大量日军有生力量,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它成为了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的最后一场大捷,也为王耀武辉煌的军旅生涯,画上了一个浓墨重彩、近乎完美的句号。

作为方面军参谋长、迂回作战计划的主要制定者,邱维达自然也功不可没。他的名字,因此在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正式“挂上了号”,成为了军界冉冉升起的一颗将星。战后,鉴于他在制定作战计划中的杰出贡献,他还荣获了美国总统杜鲁门特意颁发的一枚“自由勋章”,这在当时的中国军界,也是一份极高的荣誉。
抗战胜利后,王耀武指挥的第四方面军即将奉命北调,改编为第二绥靖区,这意味着他将离开自己长期经营的湘西根据地,前往一个全新的、局势也更为复杂的战区。同时,原方面军下辖的各部队也将被打散重组,进行调整。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王耀武起家的“老部队”——战功赫赫的第74军的调动。根据南京的命令,74军将调往首都南京,担负卫戍京畿的重任。这意味着,王耀武将失去对这支自己最熟悉、也最能掌控的王牌部队的直接指挥权。
这让王耀武心中充满了忧虑。74军,尤其是其中的核心——他亲手带出来的第51师,一直被他视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屁股”。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了这个‘屁股’,我就坐不稳了!”无论他将来身在何处,担任何种高位,只要能通过心腹牢牢掌控住74军(特别是51师)这支基本力量,他就有了安身立命的本钱和在军界博弈的底气。

因此,在74军即将脱离自己直接指挥的前夕,为这支部队选择一个既有能力、又对自己绝对忠诚可靠的接班人,成为了王耀武心中最为重要、也最为紧迫的任务。尤其是作为核心骨干的第51师师长人选,更是重中之重。
在王耀武看来,能够胜任这个关键位置、并让他完全放心的,只有一个人——邱维达.
邱维达不仅能力出众(雪峰山大捷已证明),更重要的是,他是王耀武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干将,对自己感恩戴德,忠诚度毋庸置疑。而且,邱维达虽然勇谋兼备,但在运用权术、搞小团体方面似乎并不擅长,甚至有些“简单”。这种“缺点”,在王耀武看来,恰恰是最大的“优点”,因为这意味着邱维达不会像某些将领那样难以掌控,将51师交给他,等于还是将这支部队牢牢握在自己手中。
于是,王耀武决定,在自己北上赴任之前,运作安排邱维达接任第51师师长。
对于王耀武的这个安排,邱维达自然没有任何异议。他本来就更喜欢带兵打仗,而不是做机关里的参谋长。他对王耀武说:“司令官的安排很好。我交卸了参谋长这副担子,正好可以让给明理(副参谋长罗明理)他们去挑。我还是愿意下去带部队,简单,痛快!”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非完全如王耀武所愿。围绕着74军未来军长的人选,一场复杂的人事博弈已经在南京悄然展开。
当时,74军内部有资格竞争军长宝座的将领,主要有四位:张灵甫、周志道、邱维达、李天霞。
论资历(跟随王耀武的时间),邱维达和周志道(王耀武的老部下,时任100军副军长)无疑最深。
论与各派系的关系和手腕,李天霞(时任100军军长)似乎更胜一筹。
论战场上的剽悍敢战和名气,则非张灵甫(时任74军副军长兼第58师师长,勇猛善战,但也桀骜不驯)莫属。
在王耀武内心深处,他真正属意的、认为有能力也有资格接掌74军帅印的,其实只有两个人:张灵甫和邱维达。
张灵甫作战勇猛,但其人性格过于刚愎自用,桀骜不驯,王耀武担心一旦他坐上军长的高位,可能会尾大不掉,难以完全掌控。

而邱维达,能力足够,忠诚可靠,是掌控部队的最佳人选。但他的缺点在于性格不够强势圆滑,在复杂的派系斗争中未必能站稳脚跟。
权衡再三,王耀武做出了一个看似矛盾、实则深谋远虑的决定:他表面上似乎更倾向于推荐张灵甫接任74军军长,而坚持让邱维达去接任更为关键的第51师师长。
王耀武的如意算盘是:即使未来74军的最高指挥权落不到最理想的邱维达手中(比如落到张灵甫手中),但只要自己最核心的“老营”——第51师掌握在绝对忠诚的邱维达手里,那么整个74军的“军魂”和骨干力量,就依然牢牢掌控在他王耀武的“遥控”之下。这是一种退而求其次,但却能确保自己核心利益不受损的万全之策。
1945年10月初,74军空运到南京,担任卫戍任务并兼管日伪军武装解除、遣返日俘、日侨。
邱维达随军到达南京,被国民政府授予忠勤勋章。授勋结束后,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特意找邱维达进行了一次单独谈话。这次谈话,表面上是嘉奖和勉励,实则充满了暗示和点拨。

何应钦先是肯定了邱维达在湘西会战中的功劳:“王佐民司经常在我面前提起你。老实说,以前在黄埔的时候,我对你的印象确实不深。这或许是我这个当教官的官僚主义了。不过,上一次在湘西雪峰山,我可是亲眼见识了你的本事!”
邱维达连忙谦逊道:“学生才疏学浅,愧不敢当总座谬赞。”
何应钦摆摆手,话锋一转,切入了正题:“青白啊,有些话我也就跟你直说了。最近为了74军未来军长的人选问题,已经有不少人托关系托到了我这里来。想必你也听到了一些风声。以你的战功和资历,想要谋求这个位置,也是理所应当的。但是,这么多人都在活动,或请托王佐民,或请托于我,唯独你邱青白,既没有来找我,也没有听说你去找王佐民活动。这一点,倒是难能可贵。说句心里话,像74军这样的精锐王牌部队,它的指挥权,只有放在像你这样淡泊名利、不搞钻营的人手中,或许才是最稳妥、最让人放心的。”
不过,尽管有了何应钦这番看似“肯定”的谈话,邱维达最终也未能如愿(或者说如王耀武所愿)成为74军军长。这个万众瞩目的位置,最终落到了作战勇猛、但也更具争议性的张灵甫头上。邱维达,则按照王耀武最初的安排,接任了第51师师长。

这个结果,表面上看似乎是张灵甫的胜利,但背后却隐藏着更高层次的权力逻辑。这一点,在不久之后何应钦与王耀武的一次谈话中,被点破了。
1946年1月,王耀武到南京面见蒋介石,汇报工作,并为即将前往济南出任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做准备。会面结束后,在他准备返回湘西处理交接事宜时,何应钦却突然邀请他一同乘飞机前往徐州视察(这本身就有些不同寻常)。
在飞往徐州的专机上,两人闲谈之际,何应钦貌似随意地、突然冒出了一句话:“佐民啊,你这次推荐张灵甫接任74军军长,而不是力保你的心腹邱维达或者李天霞,这一点,做得很高明,也很让上边(指蒋介石)满意啊。”
王耀武闻言一愣,心中有些不明所以。他确实在最终的推荐人选中选择了张灵甫,但这更多是基于对现实情况(张灵甫呼声高)和自身利益(保住51师)的权衡,怎么就成了“让上边满意”了呢?他连忙谦虚道:“学生愚钝,未能体会其中深意,还请敬公明示。”
何应钦笑了笑,带着几分老谋深算的意味说道:“呵呵,佐民啊,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在这里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呢?罢了,我就点醒你吧。”

他凑近王耀武,低声解释道:“你想想看,邱维达也好,李天霞也罢,他们跟你王佐民的渊源太深了,可以说是你一手提拔起来的嫡系心腹。如果你力保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接掌74军,虽然名正言顺,但在上边看来,这支王牌部队就等于是换汤不换药,仍然是你王耀武的‘私家军’,只不过是换了个‘管家’而已。这对于力求军令统一、最忌讳将领拥兵自重的上边来说,能完全放心吗?”
“而张灵甫则不同!”何应钦继续分析道,“他虽然也是你提拔重用的将领,但毕竟算是‘半路出家’投到你门下的(张灵甫原属胡宗南系统,后因故入狱,出狱后才到王耀武麾下)。而且,张灵甫本人性格桀骜,在上边那里也是挂过号的(指其杀妻案等争议事件)。你现在不避嫌疑,极力保举这样一个‘有争议’、且并非你最核心嫡系的人来执掌74军,这在上边看来,恰恰是你王佐民‘顾全大局’、‘毫无私心’、不愿继续插手74军人事的一种姿态!上边自然龙心大悦,觉得你懂分寸,识大体!”
何应钦的这番话,如同醍醐灌顶,让王耀武瞬间明白了其中的奥妙。原来自己为了保住核心利益(五十一师)而做出的妥协之举(推荐张灵甫),在更高层看来,竟然被解读为了一种“政治正确”的表态,这真是歪打正着,无心插柳柳成荫。

这也解释了为何能力、忠诚度都堪称上选的邱维达,最终未能成为74军的掌舵人。并非他不够优秀,而是因为他与王耀武的关系“太近”了,当然邱维达处事不够圆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王耀武心知肚明。
王耀武不禁暗自庆幸自己的谨慎,同时也对高层政治的复杂和微妙,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他成功地保住了自己的“屁股”(第51师),又意外地赢得了上边的“满意”,可谓是一举两得。
参考资料:
《蒋介石的亲信爱将王耀武传奇》《我对湘西“雪峰山会战”的回忆》
邱维达回忆录——《沧桑集》、《何应钦在黔阳安阳召开中美联合军事会部署雪峰山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