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罗伯特·凯恩(Robert Kane)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哲学教授
在现代社会,没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了。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呼喊着要自由;世界的整个趋势(尽管经常遭到暴力抵抗)都是朝着更自由的社会发展。但是,我们为什么想要自由呢?简单但并不完全适当的回答是,我们拥有越多的自由,就越能满足自己更多的欲望。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我们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们可以选择看什么电影,读什么书,投票给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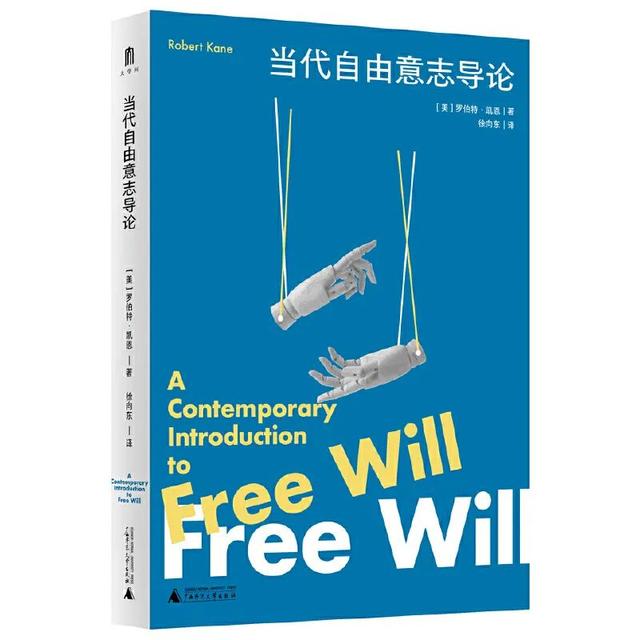
《当代自由意志导论》
[美] 罗伯特·凯恩 著
徐向东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年2月
但是,你可以称这些自由为“表层自由”。我们所说的自由意志比这些平淡无奇的自由更为深刻。为了明白何以如此,假设我们为了满足我们的欲望而有最大的自由做出刚才提到的那些选择,但我们做出的选择实际上是被他人操纵的,是被当权者操纵的。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将有大量的日常自由去做我们想做的事,然而我们的意志自由会受到严重限制。我们可以自由地行动或选择我们想要什么,但我们对自己想要的东西没有最终控制权。其他人会在幕后操纵,不是强迫或胁迫我们去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而是操纵我们去具有他们希望我们具有的愿望。
现在你可能会想到,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确实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在那里我们可以自由地做出选择,但也可能被广告、电视、舆论操纵者、销售人员、市场营销人员,有时甚至被朋友、父母、亲戚、竞争对手或敌人操纵而做出许多选择。表明自由意志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的一个迹象是,人们对这种操纵感到厌恶,当他们发现自己受到操纵时,他们会觉得自己被贬低了。他们意识到,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是独立自主的人,因为他们是在按照自己的欲望和目的来进行选择,但他们的欲望和目的一直以来都被其他人操纵,这些人希望他们做出与自己完全一样的选择。这种操纵有辱人格,因为当我们受到这种操纵时,我们意识到我们不是独立自主的;拥有自由意志大致就是要做自己的主人。
这个问题在20世纪的乌托邦小说中得到了很好的阐释,比如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的《瓦尔登湖第二》。(你可能很熟悉类似主题的新近电影或科幻作品。)在这些经典作品所描述的未来主义社会中,人们可以拥有他们想要的东西和做他们选择的事情,但他们从出生起就受到了行为工程师或神经化学家的训练,因此他们只想要自己能够拥有的东西和选择他们能够做的事情。在《美丽新世界》中,下层工人受到强效药物的影响,因此他们不会去想自己不能拥有的东西。整个周末他们都全然满足于打迷你高尔夫球。他们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但他们的欲望受到了药物的限制和控制。
斯金纳《瓦尔登湖第二》中的居民比《美丽新世界》中的工人过得好。然而,生活在瓦尔登湖第二中的那些人的欲望和目的也受到了行为工程师的暗中控制。瓦尔登湖第二的居民集体生活在一个可以被称为“乡村公社”的地方;因为他们共同承担农业劳动和抚养孩子的责任,他们有很多闲暇时间。他们追求艺术、科学和手工艺,从事音乐表演,享受着看似愉快的生活。事实上,小说的主角,一个叫弗雷泽的家伙,创立了瓦尔登湖第二,他直言不讳地说,他们的快乐生活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在他的社区里,人们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或选择的事情,因为他们从小就受到行为训练,只想要他们能够拥有的东西和选择他们能够做的事情。
弗雷泽接着挑衅性地补充说,在他看来,瓦尔登湖第二“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因为那里的人们能够选择和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对的。瓦尔登湖第二中不需要强迫或惩罚(没有监狱)。没有谁会被迫去做违背自己意志的事情。没有谁骚扰居民,也没有谁必须骚扰他们。然而,我们可能想知道,瓦尔登湖第二究竟是不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瓦尔登湖第二中所有这些表层自由难道不是以牺牲更深层次的意志自由为代价的吗?瓦尔登湖第二的居民确实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或愿意做的事情,但他们对自己想做或愿意做的事情没有最终的决定权。他们的意志是由他们无法控制的因素决定的。这种异议实际上是这部小说中一位弗雷泽的批评者提出的,他是一位拜访瓦尔登湖第二的哲学家,名叫卡斯尔(Castle)。
但是,弗雷泽对卡斯尔的批评并不在意。他承认,在瓦尔登湖第二中,确实没有这种被认为层次更深的意志自由,但他论证说这并不是真正的损失。与小说作者斯金纳(心理学中行为主义的主要捍卫者)相呼应,弗雷泽认为所谓意志自由,即卡斯尔和其他哲学家数个世纪以来一直鼓吹的那种自由,是一种幻觉。他说,无论是在瓦尔登湖第二内部,还是在其外面,我们都没有这种自由,也不可能拥有这种自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就像瓦尔登湖第二的居民那样,都只是教养和社会训练的产物,尽管我们可能会欺骗自己,让自己有不同想法。我们之所以会认为我们是自己意志的创造者或原创者,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对我们产生影响的大多数遗传、心理和社会因素。此外,在弗雷泽看来,如下想法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我们可以成为自己意志的终极的或“原始的”创造者——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我们自己的原因”。如果我们追溯行动的心理根源,比如追溯到童年,我们就会发现,那时我们的自由不是更多,而是更少。
因此,当弗雷泽呼应斯金纳等许多其他现代思想家时,他就下了战书:那种所谓更加深层的意志自由,是哲学家和神学家在我们对行为的隐藏原因有更多的理解之前想象出来的幻觉。这是一种过时的想法,在现代科学的世界图景或人类图景中没有立足之地。(请注意,在《瓦尔登湖第二》中,为这种“过时”观念辩护的哲学家被赋予了一个听起来像中世纪的名字,即“城堡”。)为什么要牺牲对我们来说真正重要的日常自由,即不受强迫、惩罚、约束、压迫等的自由,来换取一种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拥有的虚幻的意志自由呢?
以这种方式反思自由的观念是通往自由意志问题的一条途径。另一条途径是反思责任的概念。自由意志也与行动的归责(accountability)、应受责备和值得赞扬的概念密切相关。
假设一个年轻人因袭击和抢劫他人而受审,其中受害者被殴打致死。假设我们参加了对他的审判并在法庭上听取了证据。起初,我们对被告的态度是愤怒和怨恨。那个年轻人的所作所为太可怕了。但是,当我们每天都听到他是如何养成他确实具有的低劣品格和堕落动机——一个关于父母疏于照顾、虐待儿童、性虐待和不良榜样的悲惨故事时,我们对被告的一些怨恨就转移到了对他进行伤害和虐待的父母和其他人身上。我们开始对他们和他都感到愤怒。(请注意这种反应是多么自然。)然而,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把所有的责备都从这个年轻人身上转移开。我们想知道是否有一点剩余的责任属于他。我们的问题变成:他在多大程度上要对成为现在这样的人负责?他的行为都是由父母教养不当、社会照顾不周、社会训练失败等因素造成的吗?还是说他在选择其行为时起到了一些作用?
这些都是关于自由意志的关键问题,也是关于那个年轻人的所谓“终极责任”的问题。我们知道,父母教育和社会、天性和教养,会对我们成为什么人和是什么人产生影响。但这些影响是发挥了完全决定性的作用,还是为我们“留下了”我们要负责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想了解的关于那个年轻人的事情。他究竟只是恶劣环境的受害者,还是要对他成为现在的样子负有一些剩余责任。也就是说,他到底是不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成为现在的样子,这个问题似乎取决于这些其他因素是否完全是决定性的。
当人们通过这样的反思而开始怀疑,他们的行动可能是由他们不知道和无法控制的因素来决定的,或者因为这些因素而变得必然时,自由意志问题就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决定论或必然性学说在关于自由意志的争论的历史中如此重要。每当决定论学说出现时,它们的出现就表明人类已经达到了一个更高的自我意识阶段,在这个阶段,他们开始对其行为的来源、对自己在宇宙中作为行动者的地位感到疑惑。古代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哲学始于好奇,而没有任何好奇比对自由意志的好奇更深刻地影响我们的自我形象。我们不想成为某个未知棋局中的棋子。
决定论学说在历史上有许多种形式。在不同时期,人们想知道他们的选择和行动究竟是不是由命运或上帝来决定的,是不是由物理定律或逻辑定律来决定的,是不是由遗传和环境来决定的,是不是由无意识的动机、心理条件或社会训练来决定的,等等。但是,在历史上,所有决定论学说都有一个核心观念,它揭示了为什么决定论学说构成了对自由意志的威胁——无论这些学说是宿命论的、神学的、逻辑的、物理的、心理的还是社会的。按照这个核心观念:
当早期的条件存在(例如命运的判决或者上帝的预定行为,又或者先行原因加上自然法则),而且这些条件的出现是一个事件(比如一个选择或一个行动)发生的充分条件时,该事件就被决定了。换句话说,情况必定是这样:如果这些早期的决定性条件存在,那么那个被决定的事件就会发生。
用更熟悉的术语来说,我们可以说,在决定性条件已经出现的情况下,一个被决定的事件是不可避免的或必然的(它不可能不发生)。如果命运裁定或者上帝预先决定(又或者自然法则和先前的原因决定)约翰将会选择在某个时间去萨马拉,那么约翰就会选择在那个时间去萨马拉。因此,决定论是一种必然性,但它是一种有条件的必然性。不管其他什么事情发生了,一个被决定的事件不一定要发生(它不一定是绝对必然的)。但是,当决定性条件已经出现时,它必定会发生。如果命运的判决有所不同,或者过去在某个方面有所不同,约翰可能就会决定去大马士革而不是去萨马拉了。历史上的决定论学说指称不同的决定性条件。但是,所有决定论学说都意味着,每一个事件,或者至少人们做出的每一个选择和行动,在这个意义上都是由某些决定性条件决定的。
—End—
本文选编自《当代自由意志导论》,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加,特别推荐阅读。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