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上,青少年心理健康仍然是备受关注的热门议题之一。《2023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显示,学生群体心理问题日益严重,且呈现低龄化趋势。在全面人工智能时代,面对青少年成长困境,AI能否成为心理咨询的新助力?

近日,清华大学教授彭凯平在“四川天府新区青少年青春期大讲堂”上提出,AI可为心理健康赋能,但情感陪伴无法替代现实真实拥抱。
在接受红星教育·成都儿童团专访时,他进一步剖析了青少年心理问题根源,探讨了家庭亲子关系的改善之道等,并指出:AI时代,人类的终极竞争力恰恰是机器无法复制的感性能力。


目前有一种现象,一些医院的心理门诊挤进了不少中小学生,您觉得当下青少年心理问题高发的原因是什么?

最常见的是学业问题,很多孩子学习困难,学校不断地加码,要求不断提高,还经常排名,搞得家长也很难受。
二是互动时间很少,大部分时间都是被动地学习。很多孩子回家把门一关,跟任何人没有接触,就在屋子待着,导致社会互动的时间减少。
三是现在孩子的行动太少,大部分时间动脑筋,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人动得太少,大脑很难产生积极的生理化学机制,比如多巴胺、催产素、类非肽等,就会造成很大的心理的问题。
四是我们现在的社会攀比太大,老是跟那些优秀的、极端的人比,父母压力大,就反馈到孩子身上,给孩子们形成压力。


现实中还有哪些隐秘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群体关系,孩子读书期间正好是他社会关系形成的一个关键时刻,包括如何待人接物,如何沟通交流,如何不被欺负,如何不去欺负别人,这些社会技能往往是家长容易忽视的。
很多孩子,其实就是在和同学的交往过程中产生了心理问题。霸凌怎么出现的?就是因为有些人他不懂,他就开始欺负别人,把自己家里的一些做法搬到学校,对付同学,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线上的心理行为。现在很多孩子在线上交流,他们有哪些朋友?有哪些伤害、欺骗他们的人?很多父母是一无所知的,这也是一个应该被关注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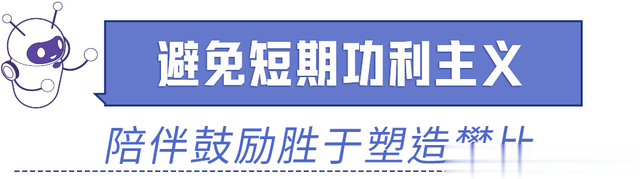

在这些过程中,家长有哪些需要反思的吗?

很多心理问题其实是可以自我痊愈的,但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个时候父母就要多陪伴孩子,挖掘对孩子的爱,跟孩子共同成长。
因为没有时间陪,我们的所有标准来自老师的反馈,老师说他考试不好,学习不认真,你得下功夫,家长又内疚,又没有时间,就把所有的怨气迁怒在孩子身上,这也是很多关系产生问题的地方——因为孩子的心理需求没有被真正地理解,孩子成长的一些痛苦,父母亲没有真正地去解决,这些都是要用爱心、用时间陪伴来完成的。
我们的孩子是一个自由的心灵,我们的目的其实是引导他的成长,陪伴他、关注他,而不是去塑造他。但陪伴时注意不要有太多开导,这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是没有意义的。父母也不要老拿自己小时候的经历拿出来对比,这是两码事。
很多时候家长着急,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讲,他把孩子当作自己没有完成的梦想的工具,在意老师的评价、社会的夸奖,一定要把这些都放到一边,真心实意地爱孩子,可以多带孩子做一些事情,走出家门,去看花花草草,去听音乐、去跳舞、去读书,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去做他想做但一直没做成的事情。


所以一个家庭应该如何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

我曾经提出三个C原则。第一是接触(contact),父母一定要多跟孩子在一起,拥抱、握手、鼓掌、亲吻,这些看起来特别小的事情,其实对人有一种温暖的作用,所以孩子痛苦的时候抱一抱他,做得好的时候给他鼓掌,这些肢体的接触其实很重要,陪伴的时间也很重要。
第二一定要有沟通(communication)。现在都是功利性的沟通,有目标、有任务、有具体要求,考多少分等等,这样是不行的,要多聊一些社会性的、情感的一些话题,哪怕是闲聊也可以。
第三个C是文化(culture)事业,多做一些公益事业、艺术文化类的事业,多去欣赏美好的文化生活,这些都能让孩子特别开心,能够弥补学校的学科教育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让孩子健康成长。


今年全国两会上,还有代表建议应尽早实施十二年义务制教育,以化解内卷消除焦虑,促进孩子们身心健康发展,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我认为要合理削减学制,每个阶段都要削减一年,最好二十四五岁念完博士。学制要缩短,内容要减少,看能不能做出东西。而且将来一定要采取混班模式,因为男孩、女孩的成熟时间不一样,发育不同,要根据孩子的成长发育规律来办学,而不是统一模式、统一标准、统一进度和统一要求。


您从事积极心理学研究,从专业角度来看,学校和老师可以采取哪些具体措施来帮助学生更好地应对心理问题?

首先一定要有成长性的思维,要关注孩子的成长,而不是关注结果。现在有个突出问题是短期功利主义,拿一次的考试、一次的表现来判断、评价孩子,这是很危险的。因此要培养一种成长性的思维,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把话说得更委婉一些。比如孩子考试不好,不要说他怎么这么笨,给他定性,而是说我们努力一下是不是可以变得更好。

第二个相信“成功才是成功之母”,每个孩子的起点不一样,走到什么地步才算是成功,要因人而异。只要他达到了父母确定的成长指标,一定要给他鼓励、欣赏、支持、爱护,也不是乱夸奖“天才、了不得”,而是表扬他的努力,不要老是拿高标准来要求孩子。成就感不是跟别人比,是跟自己比。
第三个就是一定要在行动中学习,老是死记硬背不行。孩子看起来很安静,其实他没有学,他在走神,他在干别的事情。孩子在那安安静静学了半个小时,就鼓励他走一走、说说话,放松一下,通过行动来不断激发他的学习兴趣。

由于长期面对学生、家长、社会期望,教师需要投入大量的情感劳动,这种高强度的情绪投入使得教师职业的幸福感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积极教育如何引导教师?

我们现在有太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你要比别人强,比别人厉害,这样才能出人头地。整个社会就是被这样的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驱使着,大家都在比拼,都在竞争,都在攀比。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生存的权利和价值,关键是让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我们的教育一定要改变这种现象,就是不要有太多的攀比竞争排名。
在教学工作中,也要让每一个老师都活出体面的尊严,不要因为自己的学生考不好,就觉得没面子,这个思想观念是不对的。老师也要做一些自我成长的事情,自我关怀,一个幸福的老师才能培养出成功的孩子。


现在AI已经走进了社会的方方面面,AI工具对心理干预有没有什么帮助?

ChatGPT出来,我们就深挖比较细致的心理咨询功能。一是做AI测评,以前的心理测评都是用问卷,但很多孩子不说真话,现在用AI辅助的方法进行动态的追踪,通过面部表情、生活习惯等,能够推测出来孩子的心情状况如何,这种动态的监测是一个特别好的AI辅助。
二是AI情感陪伴。比如今天被老师骂了,很难受,半夜睡不着觉,孩子可以跟AI倾诉一下,它会给一些安慰和劝告。还有就是AI咨询,通过咨询虚拟彭凯平老师,给自己找到一些行动的方法,虽然不是我,但是借着我的形象增加它的说服力。但AI只是辅助,离不开面对面的真人的帮助,这是不可替代的。


您刚刚也提到AI的情感陪伴,它会不会削弱青少年的真实社交能力?应该如何去平衡?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也是我经常讲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的情感交流,诚实的情感体验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
小朋友需要真情实意的关爱,需要父母亲的拥抱,需要我们身体的接触,这些都是人工智能提供不了的,所以我不建议小孩长期接受AI的情感陪伴。起码在没有上高中之前,那种语言的情感陪伴都是苍白的,孩子感受不到的。
但是那些孤独的人,年纪大的人,卧床不起的人,人工智能的陪伴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因人而异。


您从事积极心理学研究多年,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人类本质上是感性的生物,不是理性的生物,从进化的角度来讲,我们先有感性,后有理性。积极心理学,恰恰就是提倡挖掘人类的感性的美德,包括我们的善良、幸福,而现在发现感性的事情,恰恰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因为人工智能就代表人类理性的典范,人类跟它拼理性是拼不过的,我们应该拼感性的能力,这些是机器没有的。所以说把人类的高感性价值活出来,挖掘出来,那一定是我们人类未来的竞争优势。

从积极心理学角度来看,它强调个人的感知,注重人文素养。但现在有一个客观的情况是“全球文科倒闭潮”来了,这是否矛盾?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大的矛盾,就是判断错误。大多数人是要创造社会价值、服务他人,而这样的能力文科是提供了的,包括言谈举止、待人接物、道德伦理,这都是文科教育要做的。
现在很多大学培养不出顶尖人才,顶尖人才要靠他未来的自我发展,大学就培养基本的素质,而素质教育很多是跟人文有关系的。比如丘成桐先生是数学家,但是人家的诗写得特别好,出了四本诗集,参加香港中学语文竞赛拿了第一名。所以说文理兼容、古今贯通,才是人才成长的秘诀。当然我们文科有些地方也要改革,但不表示这个学科不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