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国庆,今年五六十岁了,大半辈子都和铁路打交道。老朋友老张有时会打趣我:“老周,对着这些铁疙瘩几十年,值吗?”我总是笑笑,望着远方延伸的铁轨,思绪也跟着飘向远方。
1985年,我高中毕业,一心想报考农学院。从小在农村长大,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就像种子渴望阳光雨露一样。家里那十几亩地,养育了一家人,也承载着我的梦想。我梦想着用学到的知识,让家乡的土地焕发生机,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好。村里人也对我寄予厚望,觉得我是周家的希望,也是全村的希望。那时,电视里播放着外面的世界,村里人围着那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对未来充满憧憬。老支书曾问我:“国庆,你学成回来,能不能让咱们村也种出电视里那种又大又红的西红柿?”我拍着胸脯保证:“一定能!”高考那天,我信心满满地走进考场,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穿着白大褂在田间地头忙碌的身影。

命运却开了个玩笑。录取通知书寄到那天,全家人都愣住了——我被调剂到了铁路学校。铁路,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是个遥远而陌生的领域。父亲拿着通知书,眉头紧锁,手里的烟袋敲得门框咚咚作响:“铁路学校是干啥的?”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不是我想要的。那天晚上,我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望着月光下的田野,默默流泪。收割后的麦田,留下金黄的麦茬,在月光下泛着柔和的光,像是在嘲笑我的失落。发小大庆拿着酒壶过来安慰我,劝我别想太多,可我知道,放弃农学梦,我心里有多难受。爹娘省吃俭用供我读书,为了我的学费,连家里的猪都卖了。我还有什么资格任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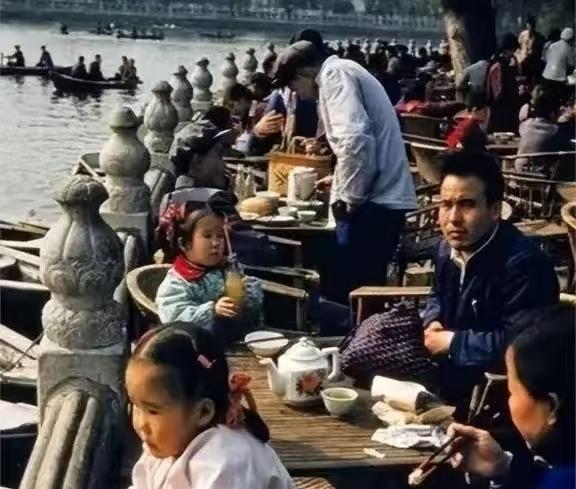
就这样,我带着复杂的心情,踏上了开往铁路学校的火车。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车厢里拥挤嘈杂,各种气味混杂在一起,让我感到有些不适。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风景,我的心也像断了线的风筝,飘忽不定。

铁路学校的生活比我想象中要好一些。校园不大,却很干净整洁。班主任杨老师是一位老铁路工人,他身上那种坚毅和执着深深地感染了我。杨老师看出了我的心不在焉,把我叫到办公室,语重心长地开导我。他给我讲了他在铁路上的故事,讲了铁路的责任和使命。他说:“铁路就像国家的血管,连接着四面八方,输送着希望和未来。”杨老师的话,就像一颗种子,在我的心里生根发芽。我开始慢慢接受了这个专业,并逐渐对铁路产生了兴趣。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家乡附近的一个小站当信号员。小站很小,工作也很辛苦,但我却干得兢兢业业。我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认真检查每一根铁轨,确保每一列火车都能安全通行。冬天寒风刺骨,夏天烈日炎炎,但我从不抱怨。

起初,村里人不理解我的工作,觉得我一个大学生,去“看铁轨”太可惜了。发小老张赚了钱,也劝我跟他一起做生意,说铁路那点工资不够干啥的。我心里五味杂陈,也曾动摇过。

直到有一次,暴雨冲毁了附近的路基,我和同事们冒着风雨抢修,连续奋战了三十多个小时,终于保证了铁路畅通。看着载着救灾物资的火车驶向灾区,我突然明白了铁路的意义。它不仅连接着城市和乡村,更连接着人心和希望。那一刻,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满足。

后来,我在小站认识了我的妻子小梅,一位温柔而坚强的乡村教师。我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都想为家乡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婚后,我们的小日子过得简单而幸福。

九十年代末,家乡要建一个加工厂,需要铁路运输。发小王大年找到我,希望我能给予“特殊照顾”。我拒绝了他,并坚持按照规定办事。为此,我得罪了一些人,甚至连儿子在学校都受到了欺负。但我没有后悔,因为我知道,有些原则不能妥协,有些底线不能触碰。

进入新世纪,铁路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我们的小站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我积极学习新技术,推动小站的现代化改造。这个过程充满了挑战,但我始终坚信,只有不断进步,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随着高铁时代的到来,我们的小站面临着被撤销的命运。我多方奔走,最终争取到将小站改造成物流中心的机会,为家乡的农产品销售开辟了新的渠道。

退休前,我的儿子小年也成了一名铁路人。他穿着铁路制服,站在我面前,眼神中充满了自豪和坚定。那一刻,我知道,我的铁路情怀得到了传承。

退休后,我常常坐在家门口,看着远处的铁轨,听着火车鸣笛的声音,心中充满了感慨。如果当年我去了农学院,人生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也许我会成为一名农业专家,也许会像老张一样经历商海沉浮。但我从不后悔我的选择。在铁路上的这些年,我见证了国家的发展,也感受到了人间的冷暖。我的青春和汗水,都洒在了这片土地上。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条路都有它独特的风景。就像火车,即使偶尔会偏离预定的轨道,最终也会到达目的地。而我的目的地,就是这片我深爱的土地,这条我守护了一辈子的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