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不光在把握大局上高人一等,就连处理细节也是相当出色。下面,咱们就聊聊主席是怎么调解陈毅和饶漱石之间矛盾的几个小事儿,简单分析分析。
一、谁去延安,谁就得留下来负责工作。
陈和饶之间有了矛盾,俩人现在谁也不让谁,主席想了个好办法,就是先放一放,冷处理。
由于两边都在死磕,单靠远在西北的外界力量,很难真正平息这场冲突。既然这样,那不如把两边先分开,这也不失为一个实用的解决办法。
接下来,得挑个人留下来负责工作,再选个人去延安,这事儿又得好好琢磨琢磨了。
我们之前提到过,主席和陈毅同志早就认识了。在井冈山会师那会儿,陈毅同志能算是除了朱德和毛泽东之外的第三号人物。再加上经历了“九月来信”那档子事后,他们俩对彼此都了如指掌。
主席和饶之前并不熟。饶一开始是在白区干活,跟少奇同志关系挺好。后来他长期在国外负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咱们争取国际上的理解和帮忙。皖南事变那会儿,饶漱石通过收买一个敌军连长逃了出来,结果被查了。但因为证据难找,事情就一直拖着。最后是主席和少奇同志站出来给他做了担保。
这主要有两个缘由:一方面,少奇同志对饶颇为赞赏;另一方面,饶在皖南事变中表现出的那种敢于负责的勇气,给主席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好印象。
所以,不管是谁留下来,还是谁离开,其实都行得通,两边应该都能同意这个安排。

从干活的匹配度上讲,饶留守显然是更合适的人选。你看,赖传珠刚当上政治部主任,他能不能扛起新四军全部的政治工作,这还真不好说。但陈老总一走,军事上有张云逸、粟裕在呢,还有叶飞、张爱萍这些大佬,他们那个时候军事能力已经显现得明明白白了!
主席并没有下死命令,他在电报里是用商量的方式说的:“……我们挺希望陈能来延安,参加‘七大’。之前你们来电说只想派一个人来,那时候我们还不清楚你们内部有矛盾。现在知道了,这矛盾主要就是因为党内好多事儿没说清楚。要是陈能来延安参加‘七大’,并且在这儿待上半年左右……”
接到中央的通知后,两边都没有啥不同意见:陈要前往延安,饶就留在原地。
二、为啥主席当时没直接听陈毅当面说呢
陈毅心里憋屈得很,一回到延安,头一件事就是琢磨着得赶紧找主席当面把事儿说清楚。
但是,主席并没急着见陈毅,更别说聊起黄花塘那事儿了。原因嘛,挺直接的:一方面,主席心里明白,陈毅刚到家,还带着黄花塘那事儿的气呢,连凳子都还没捂热乎,这时候去跟他说事儿,能不能客观公正,真不好说。另一方面,要是主席立马就找陈毅谈,那不就先入为主了嘛,对远在华中的饶漱石来说,也不公平啊。
所以,主席跟陈毅讲:老陈啊,要是你想聊聊在南方打三年游击战的经验,或者新四军抗日那会儿的事儿,我可以组织个会,让你痛痛快快讲上三天三夜。但要是想说跟小饶的那些纠葛,那就别提了,一句都别多讲。
在延安待的那几个月,陈毅的心情其实一直忽上忽下的。说起来,这心情的变动,一部分是因为主席,另一部分嘛,跟远在华中的饶漱石也有关系。

经过好几个月的冷静期,陈毅的看法一点点地在转变,他对待和饶之间的不同意见也越来越能沉得住气了。说真的,多亏了主席给他做思想工作,再加上他自己也好好想了想,到最后,陈毅是彻底想通了,也不再纠结那些事儿了。
三、找挂铃的人把铃铛摘了遇到问题时,咱们得找个办法解决,就像是谁挂的铃铛,那就得找谁来把它摘掉。这事儿挺简单的,谁惹出的事儿,谁就得负责收尾。别找别人,也别拖着,直接找那个系铃的人,让他自己动手把铃铛解开,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嘛。这样处理,既公平又高效,大家都能省心。
主席觉得两边都冷静下来了,现在处理问题的时机也挺合适了。
1944年3月15号,主席给华中局和新四军军分委发了封电报,里面说了这么些事:“陈、饶两位同志之间的那点小分歧啊,其实就是工作上有不同看法,没什么大不了的。说到内战时候他们在闽西那点争论,也就是个别事情上有出入,根本扯不到总路线上。再说到抗战时候,陈毅同志在皖南、苏南那可是坚决执行中央的命令,跟项英同志的情况不能混为一谈。不管内战还是抗战,陈毅同志都是立了功的,没有走过歪路。要是有人对这两点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就让漱石同志去给他们讲讲清楚。”
说到陈毅同志早期的革命经历,主席是很有发言权的。因此,在这份电报中,主席对陈毅同志给出了评价。不过,让人意外的是,最后一句竟然是让“漱石同志来解释说明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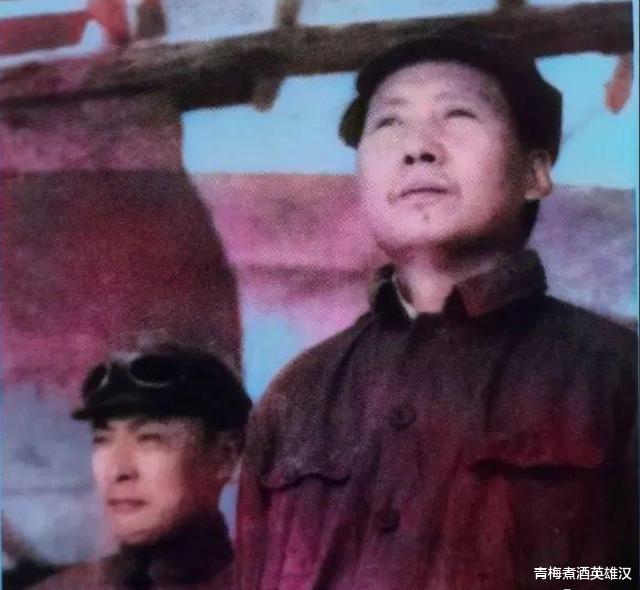
这事儿挺有意思,饶和陈一起工作的时间其实很短,对陈的了解并不多。那为啥主席还要让漱石同志来解释这事儿呢?
说白了,新四军里头传的那些话,比如陈毅老跟主席唱反调,陈毅不瞧政委顺眼,还有陈毅跟政治工作制度过不去,这些全都是饶那家伙搞出来的。所以,主席说“让漱石同志来解释清楚”,这挺对的。谣言啊,光靠明白人不理它可不行,得让造谣的人自己去摆平,这才是最有效的招数。
饶漱石发了封电报,里头说了:“陈同志啊,他在思想上、组织上还有些小问题。对于统一战线、文化干部还有一些偏右的看法,对某些组织原则也是。他对过去的一些事情,心里还有疙瘩,有时候还会用那套老掉牙、不好的做法。这些呢,他在电报里头稍微提了一下,我也回了电表示欢迎他提出来。不过感觉他还是没说明白,所以我再详细跟你说说,好让你帮他一把。”
主席这时候显得特别能忍,既然是为了能帮他一把,那我就再去劝劝陈毅同志。主席还是没选择直接找陈毅当面谈,而是继续写信:“……遇到事情得忍着点,多找找自己的不足,努力提升自己,得顾全大局。只要不是原则性问题,就多担待点别人……”
写信表达心意还不够,第二天,主席硬是从繁忙的日程中挤出时间,亲自去看望生病的陈毅。陈毅心里头那个暖啊,当下就说:“我本来心里头挺不满的,现在啊,我啥怨言都没了。”
到现在这地步,两边都把自己的想法说透了,也聊得很详细。主席呢,他在中间起到了大作用,把两边的要求都给考虑进去了,让大家都满意。
1945年8月25号,主席给华中局和饶发了电报:说陈毅同志昨天已经飞到太行山,接着又要赶去华中。陈毅表现得很不错,所有事情都沟通顺畅了。他们这样分工:饶担任书记和政委,陈毅当军长和副书记,其他职位保持不变。
到现在为止,两边儿的争执其实早该有个结果了,也确实是时候做个了断了。
真心感谢大家花时间阅读!也非常感激那些给予打赏支持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