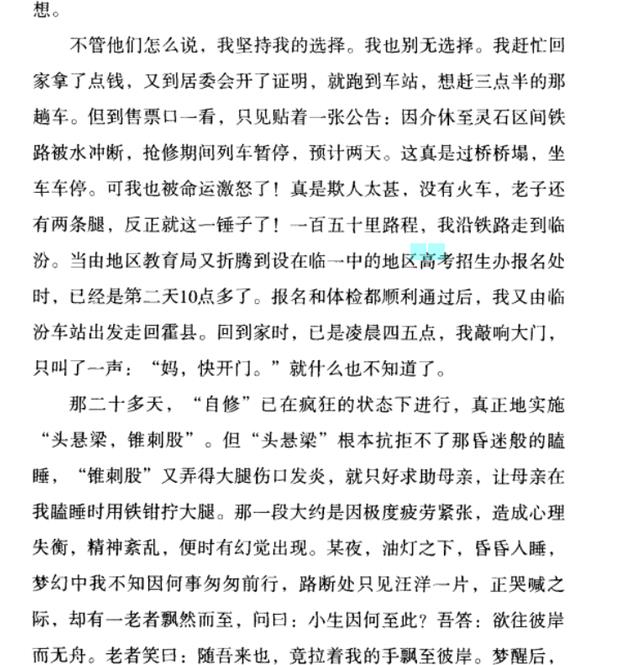高考,几乎是每个学子的印记。
紧张、忐忑、挣扎,那是一场与命运的较量。
安永全或许比大多数人经历了更多的波折。
他曾在煤矿里挑过担、运过货,直到二十几岁才第一次走进考场。

他埋头苦读,终在两次高考后,拿到了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入场券。
安永全在之后的岁月里,依旧没有忘记那段曾令他泪流满面的时光。
每年高考时,安永全的散文《我的高考》都如期而至,在无数学子中流传。
山西运城原市委副书记安永全的高考,看哭了无数人……
贫困与渴望
故事主人翁正是山西省运城市委原副书记安永全。

1958年,山西霍县,安永全在霍县中学度过了他的初中时代。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
霍县的初中分为两类班级,其中一类班是二年制的速成班,安永全正是被分配到了这个班级。
速成班的课程紧凑,教学内容匆忙,来不及品味。
在这里,安永全的学业生涯也不过是短短一年多。
当时安永全的真正课堂,在田间地头和社会的奔波中度过。

为了生计,他早早地下地翻土;有时,他又得前往钢铁厂,背着沉重的矿石,在寂静的夜色中一步步跋涉。
这样零星的“学习”,使得安永全对于课堂的渴望更加强烈。
安永全未曾上过高中。
1960年,霍县,安永全从初中毕业,成绩名列前茅,大约在前五名之内。
那年的升学由当地政府分配。
而安永全,按理说该进入高中继续求学。

可他心中明白,这条路,自己走不通。
家境,始终是他无法摆脱的枷锁。
那一年,他家住在霍县的破旧县城小屋里,家中共有八口人,其中有六个弟兄,他是长子。
父亲做的是售货员,月薪不过三十四元。

屋里狭小,十平米不到的空间里,兄弟们像是被挤进罐头盒的沙丁鱼,每晚,土炕上的空隙寥寥无几,兄弟们的头和脚交错叠成一团。
母亲早就对他说:上完初中就够了,别再上了。底下的孩子,连小学都上不了了,能认得钱就行。
那时候,安永全从不敢反驳,只是默默点头,心中却空洞无物。
在霍县中学的最后一天,安永全将自己的脸紧紧贴在那块匾牌上,泪水模糊了视线。
匾牌上那几个字,重若千斤,将他从曾经渴望的知识殿堂拖回那片贫瘠的土地。

他的心,像被某种无形的力量紧紧握住,无法挣脱。
毕业后,安永全没有选择继续求学,而是投身社会,做过小商贩,做过小工,也做过装卸工,什么能赚钱,便做什么。
无法反抗,难以逃避
十五岁那年,安永全放下了书包。
当他看到父亲一天天愁眉苦脸、步履蹒跚,看到母亲带着一盆辣椒面在街头叫卖时,他的心里便清楚了一个道理。
人生第一要紧的事,不是理想,不是未来,而是能不能吃得饱肚子。

他随母亲走上了街头,站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个“社会位置”,开始了贩卖瓜果蔬菜的生意。
安永全并未从父母那里学到过什么经商之道,只听得最多的便是些空洞的“和气生财”“买卖公道”之类的话。
事实上,生意的“道理”不止这些。
每逢中午,总有一些初中的同学经过,看到他的小摊,便是眼冒光、手不由自主地伸向了筐子里的甜瓜与西红柿,抓得也毫不客气。

安永全站在一旁,心里充满了羞耻,却又无力制止。
他的秤盘总是空荡荡的,他甚至不敢要求他们付钱。
在他眼里,这些人成了远离他生活的“另一个世界”的人。
他只能默默地看着他们白拿白吃,自己则眼睁睁地承受着这一份不敢言明的屈辱。
不久之后,安永全找到了一份较为固定的工作——拉人力车。
他每日拉着货物,穿行在街头巷尾。
东大街,那条绵延的长坡,是他每天的战场。

地面上,砖石与碎石交织成一种奇怪的纹理,坑洼不平。
坡顶上,副食店是他的目的地,每日都要用力拉着沉重的货物,爬坡而上。
他低下头,弓起腰,像是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了车辕上,两手死死抓住辕杆,拼命前进。
汗水浸湿了眼睛,模糊了视线,前方的路变得一片迷茫。

到了最陡的地方,安永全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还拥有双腿。
每天,他都要在这条街上,展现自己最狼狈的一面。
1961年端午节,安永全一时贪心,额外拉了100斤货物。
那一天,他拼尽全力攀爬着东大街最陡的坡段。
肩上的拉绳突然裂开,失去控制的车子猛烈冲撞地面,安永全的脸猛地撞上了坚硬的土路,鲜血瞬间涌出。
车子横冲直撞,翻滚着撞过路旁的人群与摊子,酱油和醋洒了一地,街头瞬间乱成一团。
周围的惊叫声、责骂声如潮水般涌来。
安永全猛地清醒,意识到自己正被撞倒的行人愤怒地打骂着。
那时,他才终于察觉到围观的人群里,竟有几张熟悉的面孔——那是他初中的同学。
自尊心在这一刻被撕得粉碎,安永全躺在地上,眼泪与血水混杂,号啕大哭。

他低下头,心底的羞耻感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贫穷,真是可怕。
你的一切努力,别人看不到,别人忽略;甚至连最基本的尊重,都在无形中被践踏。
因为穷,你只能忍受所有的屈辱与辛酸;因为穷,别人可以在阳光下读书,而你却只能在阴暗的角落里推车、搬运,汗水与疲惫成了你唯一的标志。
你不敢反抗,也无法逃避。
然而就在那一瞬,安永全心中闪过一个念头——要杀出一条血路,打破这层无法跨越的贫困藩篱。
名为希望的花
1961年秋天,安永全偶然得知,社会青年只要具有同等学力,也能报名参加高考。
即便没上过高中,照样可以考大学。
文科考试,竟然没有数学与理化,只有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和俄语。
这一发现让他忽然看见了不远处的希望。

安永全立刻奔赴县城的旧书店,翻箱倒柜,找来高中三个年级的文科课本。
那些发黄的书页,见证了他渴望知识的焦虑与决心。
他把所有能找到的复习资料都搜罗回来,抓住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1963年夏天,安永全已深知自己自学的时间短,内容不够扎实,知识体系混乱,漏洞百出,常常读得头晕眼花。
按计划,他本该再学一年,理清思路,但他心里也清楚,时间不允许他再拖延。
他只能匆忙上阵,怀抱一丝微弱的希望——也许,或许,命运会眷顾他一次。

然而,考试那天,意外还是来了。
安永全自认为最拿手的语文,竟然把作文题目看错了。
对于自己费尽心力攻克的俄语,他对完答案后才发现,最多也不过五分。
第一次高考,就这样草草结束,带着失败的阴影和深深的懊悔。
安永全并未因此气馁,反而愈发坚定。

他重新制订了学习计划,几乎不留一丝空隙。
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只学初中的外语,放弃高中外语。
他定下40分为目标,集中攻克其他四门课程,力争每科均分达到85分以上,在强项上做足文章,补足自己的弱点。
光有记忆是不够的,必须要用方法来加深记忆,才能使学习变得更加扎实。
历史,六本教材放在一旁,他用两本稿纸,分朝代、分世纪,逐一写出每个重大事件、人物和时间。
古文,他要求自己做到标点无一差错,若一时写不下去,便查书再写。

每次写完,都会重新默记,做到能脱口而出。
为了锻炼应变能力,安永全又另辟蹊径。
他将每科的试题分别写在纸条上,卷成捻子,放入五个小盆中。
大题是长捻子,小题则是短捻子,每次定好闹钟,抽取五道大题,十二道小题,限定两个小时内完成,做完后再对照课本阅卷评分。
他甚至为作文定下了严格的时间限制,自己设计了50道各类作文题,随时抽出一道,要求在50分钟内完成。
这一切的反复训练,几乎成了他每日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命运总是难以预测。
1964年,距离高考仅剩二十七天,安永全接到了通知,九月将上山下乡。
此时,怎能再等?高考的钟声近在眼前。
他急忙拿起报名通知单,心急如焚。
一番折腾后,他急奔县教育局,却被告知霍中的集体报名早已提交,体检也已结束。个人报名?只得赶去临汾的招生办。

明日即是最后一天,错过便无望。
安永全回家,拿出所有积蓄,跑去居委会开证明。随即,飞奔至车站,争取赶上三点半的车。
然而,售票口贴出了公告:铁路因水灾被冲断,预计恢复需两日。
安永全怒火中烧。
无铁路?那便走!
一百五十里,步行开始。
从介休到临汾,他的步伐越来越沉重,疲惫已透入骨髓。到达临汾时,天已亮,已是第二天上午十点。
办理完报名和体检,又匆匆折返。
一天一夜的奔波,终于回到霍县,天色已明。
他敲响家门,虚弱至极,只低声道:“妈,快开门。”
说完,便再无力言语。
一觉沉沉,醒来时,双腿肿胀如桶,脚底疼痛难忍。

但他没有喘息片刻。书本和试卷已占据了他的全部,他脑中只有一个个密密麻麻的题目。
自那时起,安永全便以一种近乎拼命的姿态开始了逐梦的征程。
头悬梁,锥刺股,他甚至恳求母亲用大钳子夹着他,用力拧醒那片顽固的瞌睡。
他如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活在那无尽的课本与试卷之间。
终于,高考落下了帷幕,漫长的等待将人的意志一寸寸剥离。
有一日中午,太阳无情地烤着大地,安永全依旧在家门口的小店里,忙着卸货。
汗水浸透了他的背脊,汗珠在脸上沿着脖子滑下,瞬间被灰尘吞没。
忽然,视线一转,邮递员手捧一封信,正朝他走来。
那一刻,安永全几乎是飞奔过去的。
手接过信封时,指尖微微颤抖。
那一纸薄薄的信封,沉重得让人几乎无法喘息。
他撕开信封,看到的是——一张录取通知书——来自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
站在门口,他久久未曾动弹。

眼前的世界变得模糊,空气也似乎停滞了。
站在炽烈的阳光下,他终于明白,那段被生活狠狠折磨的岁月,终将开出一朵名为“希望”的花。
曾有多少人批判高考,批评它过于功利,批评它给大学生带来了无尽的困惑。
可一个有知识、有能力、有素养的人,终究会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收获属于自己的阳光。
参考资料:
安永全著.《我的高考》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