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卿心君悦
1925年,鲁迅沉重地写下了小说《弟兄》。
对这篇小说的解读,多基于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兄弟失和”的背景。
据现有的多方资料(鲁迅两兄弟及亲人、好友的文字材料)表明——
在1923年到1924年间,鲁迅与周作人两兄弟,在周作人媳妇羽太信子的挑唆下,其乐融融的两兄弟分崩离析,也由此鲁迅从八道湾大宅被迫搬到了西三条胡同。
当年的事,羽太信子对鲁迅的构陷,以“性”为重点;而在鲁迅的眼中,问题的根源却在于“金钱”。
用这个创作背景介入去阐释《弟兄》,有一定合理性;但将《弟兄》这篇小说完全看作是鲁迅对当年“失和”之事的“泄愤”、“映射”与“解释”,却又有失公允。
毕竟,批判“国民性”,揭露人性的愚昧与卑劣,以期唤醒“沉睡的人”,才是鲁迅的第一要务,而作者自身的经历不过是创作的素材而已。

这篇文章对《弟兄》的阐释,则基于小说情节,分享鲁迅借小说意欲道出的人性真相——
在金钱面前,亲情有多可笑?!
“不将钱放在心上”的模范兄弟小说《弟兄》的主要人物有四个:张沛君和张靖甫两兄弟,公益局办事员秦益堂和汪月生。
故事开始于公益局里的日常——
公益局平时没有什么公务,几个办事员成天闲在办公室里聊家常。
说话间,老烟枪秦益堂猛然被水烟筒呛得剧烈咳嗽,办公室里聊天的声音立马停了,直等秦益堂咳嗽完,长叹了口气,气恼地抱怨道:
“到昨天,他们又打起来架来了,从堂屋一直打到门口。我怎么喝也喝不住。”
秦益堂口中的“他们”,是他的两个儿子——老三和老五,而二人打架的原因则是:老五所购买的“公债票”赔了钱,老五要求所赔的钱算家里的开销,由家庭公账出,而老三反对,认为老五赔的钱就应该由老五自己承担。
听了秦益堂的抱怨,躺在坡腿躺椅上的张沛君站了起来,眼中露着慈祥的光,不理解地说道:
“我真不解自家的弟兄何必这样斤斤计较,岂不是横竖都一样?……”
秦益堂看了张沛君一眼,眼神移动,感叹道:
“像你们的弟兄,那里(哪里)有呢。”
张沛君笑着继续说道:
“我们就是不计较,彼此都一样。我们就将钱财两字不放在心上。这么一来,什么事也没有了。
“有谁家闹着要分的,我总是将我们的情形告诉他,劝他们不要计较。益翁也只要对令郎开导开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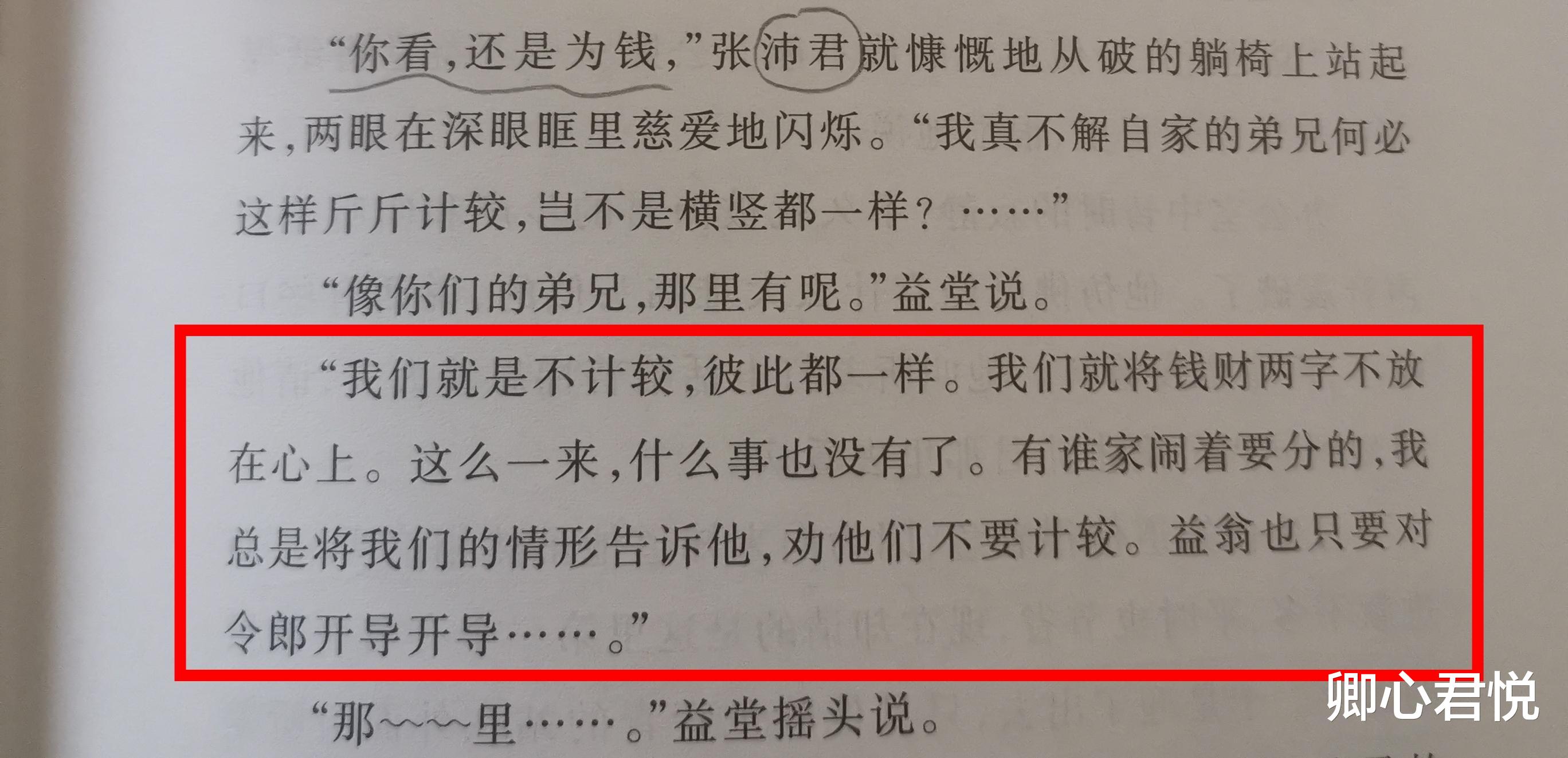
秦益堂摇了摇头,旁听着的汪月生觉得张沛君把事情想简单,其理由是:
“像你们的弟兄,实在是少有的;我没有遇见过。你们简直是谁也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心思,这就不容易……。”
说罢,汪月生问张沛君,他的弟弟仍旧在忙?
张沛君应道:弟弟靖甫还是忙,一星期18点钟功课,外加93本作文,但这几天弟弟请假了,说是浑身热,应该是受了风寒。

汪月生听完叮嘱道,这可得小心点,从早上的报纸看到最近在流行“时症”。
张沛君急问,什么时症。他见汪月生答不上来,只说是“什么热”的病,便连忙到阅报室去找那张报纸。
张沛君走后,汪月生又向秦益堂称赞起张沛君和张靖甫两兄弟的感情:
“他们两个人就像一个人。要是所有的弟兄都这样,家里那里(哪里)还会闹乱子。我就学不来……。”
秦益堂听后,更是恼怒家里两个孩子为“钱”大打出手。
而就在这个时候,张沛君的声音在走廊响起,话语带着颤抖,仿佛大难临头,只听他连连呼喊听差,要其立刻打电话给普悌思普大夫,让大夫去同兴公寓张沛君那里去看病。
普悌思普大夫是当地最有名也最贵的西医,汪月生一听便知道问题很严重,否则收入一般的张沛君决不会请这位大夫。

于是,汪月生迎了出去,见张沛君脸色铁青,连问发生了什么事。
张沛君一边向汪月生解释,报上说的“时症”是“猩红热”,跟靖甫的症状很像;一边听到听差在电话里告知医院,等普悌思普大夫回来立马让其去同兴公寓。
随后,张沛君匆忙走进办公室取了帽子,对跟进来的汪月生说:
“局长来时,请给我请假,说家里有病人,看医生……”
病中的守望与煎熬从公益局出来,张沛君没顾价钱,看到一个强壮能跑的车夫,就一步跨上了车,让其快些赶路。
等张沛君走进弟弟靖甫的房间,见弟弟脸色更红并有些发喘,心倏地剧烈跳动起来,他伸出手摸了摸弟弟的头,直感烫手。
靖甫从哥哥的神情之中,隐约察觉到了点异常,问他的病是不是很重?
张沛君躲着弟弟眼神,支吾地安慰弟弟没事,然而在心里,一向不相信什么封建迷信的他,却从弟弟的身上感到了某种不详,这种发现令其更为不安,退出弟弟的房间,轻声招来寓所的伙计,要其打电话给医院,问找没找到普大夫。
听到否定的答案,张沛君坐立不安。
焦急慌乱中,张沛君想到了同寓所的一位中医,他对其是极为不信的,还曾言语冷嘲热讽过这位中医,然而,束手无策中还是硬着头皮地找了这位中医白问山。
白问山一听缘由,倒并没有难为张沛君,戴上玳瑁边的墨晶眼镜来到靖甫的房间,一通诊疗过后,白问山从容且高深莫测地离开,张沛君忐忑地跟随其后。
回到白问山的住处,张沛君问他弟弟究竟是什么病。
白问山肯定地回复道:红斑痧。
听到这,张沛君松了一口气,又确认地问道:
“那么,不是猩红热?”
却没想到,白问山接下来的一句话,让张沛君的心从高空直接坠了下来:
“他们西医叫猩红热,我们中医叫红斑痧。”

张沛君失神地从白问山的住处出来,路过电话机他再次想到普大夫,连忙打电话给医院,问找没找到普大夫。
医院回复说,找到普大夫了,但正在忙,很可能要明天早上才能去。张沛君听后,再三叮嘱医院,不论多晚,都让普大夫过来一趟。
再次进屋去看弟弟靖甫,张沛君发现弟弟的脸似乎更红,还出了一些红色的点,眼睛也跟着肿了。他坐在房间的椅子上,如坐针毡。
在房间与夜的寂静里,他仿佛能听到寂静的声音,也因此每一辆车的汽笛声,都听得更加分明。几次听到汽笛声,张沛君都以为是普大夫来了,然而他还没有走到门口,车却早已驶过,就这样次次失望地返回弟弟的房间。
期间靖甫醒来一次,听到哥哥进屋,以为是有他的信,知道不是来信,又闭上了眼睛。(请记住这一情节,有特殊的含义。)

坐在房间中的张沛君,听着一辆辆从寓所开过来又驶离开的车的声音,多次失望变得绝望,绝望中紧张的情绪却慢慢地舒缓了——
慢慢的,张沛君对弟弟靖甫的病已下了定论,必是“猩红热”无疑,也不再去关注寓所外经过的汽车,所有的心思逐渐集中于之前一再逃避的问题:
“那么,家计怎么支持呢,靠自己一个?
“虽然住在小城里,可是百物也昂贵起来了……。自己的三个孩子,他的两个,养活尚且难,还能进学校去读书么?只给一两个读书呢,那自然是自己的康儿最聪明,——然而大家一定要批评,说是薄待了兄弟的孩子……。”

就这样,在外人看起来“极重兄弟情义”的张沛君,在弟弟靖甫重病之后,自利的心思终于真实地呈现了出来。
脱下一直以来披着的“兄弟怡怡”的外衣,可能引来的外界评议,非张沛君所愿;而为了维护一直以来所塑造的对外形象,而让自己吃亏,也非张沛君所想。
就在这挣扎与彷徨之中,远远传来了一阵脚步声,等待已久的普大夫终于来了……
隐藏在梦中的“真相”经普大夫一番诊疗,最终确定张靖甫所得的并非什么“红斑痧”“猩红热”之类的“时症”,而只是起了疹子而已。
张沛君激动地再三向普大夫确定,得到的答案都是起了疹子,这让张沛君彻底放下心。
普大夫开了药方,叮嘱了一番注意事项便离开了。
张沛君将药方交给寓所的伙计,让其一早就去指定的地方买药,随后便将这一好消息告知弟弟,然而弟弟却没有任何的反应。
带着喜悦的心情,张沛君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醒来时,阳光已透过窗户照了进来,朦胧中,张沛君只见自己床前站着一个满脸流血的女孩,而他似乎正要去打这个孩子。

定神看了看,刚才呈现在眼前的一切又都消失了,张沛君仍在他自己的房间,身上满是汗。他若有所思的换好衣服,到弟弟靖甫的房间看望了一下,见弟弟状态没有恶化,伙计尚未将药送来,便在屋内的椅子上坐下。
昨晚的梦境片段陆陆续续在脑中的呈现出来——
在梦中,弟弟靖甫就躺在眼前这张床上,死了。他忙着收殓,期间,独自一人背着棺材从大门外背进里屋,外面见到这种情形的人,纷纷给予了他赞颂。
弟弟死后,他让自己的三个孩子去上学了,弟弟遗留下的两个孩子哭嚷着也要去。他被哭闹声吵得心烦,用力抽了其中一个孩子荷生一个嘴巴,将其打得满脸是血。
荷生满脸是血的来找张沛君,张沛君跳到了供奉祖宗排位的堂桌上,他看到荷生的后面跟随了一群人,这些人都是荷生找来指责他的。
张沛君激动地向跟荷生进来的那些人辩解道:
“我决不至于昧了良心。你们不要受孩子的诳话的骗……。”
说完这些话,张沛君看到满脸是血的荷生站在面前,(这一幕正是张沛君醒来时呈现在眼前的那一幕)张沛君伸出手,再次狠狠地打了过去……

就在这个时候,伙计进来了,手里拿着药,还有一包书。
躺在床上的靖甫,瞥了一眼,问张沛君拿来的是什么?
张沛君说是“药”,靖甫追问另一包是什么?
张沛君喂靖甫吃完药后,告诉靖甫另一包是“书”。(这是靖甫找人去借的书,也是在上一段中,重病的靖甫最在意的东西。)
张沛君把书递给了靖甫,靖甫摸着书露出了微笑:
“等我好起来,译一点寄到文化书馆去卖几个钱,不知道他们可要……。”

对于张沛君听完这句话后的态度,鲁迅在小说中没有描述。
但结合张沛君的梦境、一直努力塑造的形象,也不难猜出鲁迅在这一处埋下的“留白”——必是张沛君的惭愧与羞赧,而在这种情绪的背后所隐藏着的,则是人性的自私与卑劣。

回看上述的情节,一些事已经不言自明了——
张沛君与张靖甫两兄弟是群居的,两兄弟一同维持着整个家庭的生计。在这里,张沛君的工作,不过是每日到公益局“点卯”,喝喝茶水、聊聊天、看看报,适时地塑造他那对外“兄弟怡怡”的形象,而他的弟弟靖甫,每周都有忙不完的工作,连生病都不忘“翻译新书”来增加整个家庭的收入。
由此则可看出,在为家庭的付出中,张靖甫的付出大于张沛君的付出。
而在家庭财产的索取中,不谈张沛君在外应酬所需的花销,但讲孩子的数量,张沛君有三个孩子需要养,而张靖甫却只有两个孩子要养,所以,在家庭整体的财产的使用与索取上,张沛君却是大于张靖甫的。
在这种情况下,对内占了极大便宜的张沛君,对外言称,兄弟不应分你我,更不应该在钱上斤斤计较,是多么可笑、虚伪,又多么卑劣的一件事;尤其是当联系张沛君的梦境,这种无耻的程度更会加深。
同时,张沛君这种虚伪的思想与态度,对张靖甫来说也是一层道德的绑架,迫使着张靖甫只能忍受被压榨的命运,而在这一点,也正是鲁迅所要批判的封建家庭伦理制度对人的压迫以及其特有的“吃人”特性。

张沛君在弟弟靖甫生病之前,已被自我塑造的光辉形象进行了自我催眠;然而,在弟弟靖甫心中,对张沛君的内心却是有所了解的。
于是,张靖甫才会在重病中仍念念不忘“译书挣钱”的事,他清楚一旦他死了,或是失去了挣钱的能力,那个看起来极为重视“兄弟情”的哥哥,首先就会一脚踹开他及其两个孩子。
在私利面前,在金钱面前,兄弟之情的可笑,由此可见一番!
结语小说《弟兄》的结尾,鲁迅安排张沛君回到了公益局。
当经历了这些事后,尤其是做过那个“不敢示人”的梦以后,再次听到秦益堂对自家孩子争斗的抱怨,张沛君已不敢发声。
在秦益堂的叙述下,他的两个孩子,老三与老五之所以大打出手——“老五要把他公债票的赔款由家庭公账支付,而老三又极为反对”——的背后真相却是:
老三比老五多两个孩子上学,由此老三一家的日常花销远超于老五,因而引起了老五的积怨与不满,所以才非要把他赔在公债票上的钱由公账支付,以此来讨个心理平衡。

在金钱面前,人与人的感情不堪一击,这似乎是一个现实,然而导致这个现实的根源是什么,却很值得我们深思,这也是鲁迅批判国民性的缘由所在——
是在生存面前,金钱的重量不断增加,唯有“仓廪足而知礼节”,还是人所处的环境影响,亦或者是人性所具有的某种“卑劣”特质在暗中作祟?
这需要每个人深思、反省,而非将既定的现实当作人生的经验与准则来抚慰自己,教育后人。
毕竟,“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和“人与人之间隔着厚障壁”的世界,并非你我所愿,但却会因你我而坚固,亦或破碎!

卿心君悦,读别人的故事,过自己的日子。用文字温暖你,我。

亲兄弟,也要明算账
不要拿金钱考验亲情!
自利至互利,自惠到互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在钱面前考验各种情,一切都会向钱看,所以看破不说破。经不起考验
我过了40岁悟得:任何关系都是利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