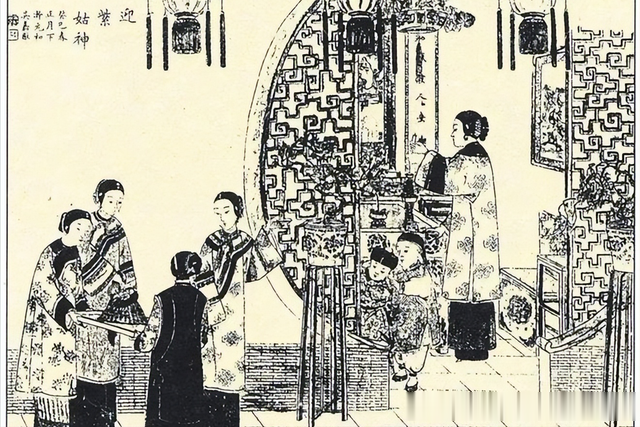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初三,汴京城南的赵家宅院内,蛙鸣声穿透了潮湿的夜幕。丝绸商赵德贵踉跄着踏入后院,满身酒气中夹杂着脂粉香。他伸手拨开垂柳枝条,脚下却踩中一团滑腻之物,仰面摔在荷花池边的青石板上。未等呼救,他的四肢已如抽筋般扭曲,喉头发出“咯咯”声响,待家仆举灯赶来,只见主人面目青黑,七窍渗出血丝。

尸身旁六只怪蛙蹲踞如石雕。这些蛙类通体墨色,背部红斑似凝血,眼珠泛着琥珀色幽光。更骇人的是,每当有人靠近,蛙群便齐声发出锯木般的嘶鸣,惊得护院犬夹尾逃窜。消息传入开封府时,知府李宪正与转运使饮茶,手中越窑青瓷盏“咔”地裂开细纹:“速传周文远!此案涉及蜀锦贡品,万不可草率!”
蛛丝马迹,推官断案推官周文远策马疾驰时,左眉刀疤在晨光中泛红。这位因侦破“郑州盐枭案”名震京畿的判官,此刻蹲在荷花池畔,指尖捻起一撮猩红粉末。仵作张九以银刀划开蛙腹,绿色毒液滴入陶碗竟腾起白烟:“此毒遇热则沸,赵德贵酒气催发血气,恰成致命引子。”
池边青砖缝里嵌着半枚脚印。周文远命人拓印比对,发现鞋底纹路特殊——前掌密布菱形凹痕,后跟却有月牙状缺口。这种制式的麻鞋,唯岭南脚夫常穿。捕头陈武忽然想起:“赵家庶子赵文礼,昨日焚烧的旧衣里就有这等鞋履!”

验尸牍报更添疑云。赵德贵指甲缝中残留着金丝线,与正室王氏衣襟的盘扣材质相同;而胃囊深处藏有半片未化药丸,经查竟是解毒圣药“紫金丹”。周文远冷笑:“服毒者随身带解药,倒是稀奇。”
南疆秘毒,往事如烟汴京东市“回春堂”的樟木药柜前,周文远轻叩台面。老掌柜盯着火斑蟾草图,浑浊眼中闪过惊惧:“此物只生岭南瘴疠之地,其唾可蚀铁,二十年前韶州军械库失窃案……”话到此处戛然而止,转而取出本泛黄账册:“四月廿九,有人购硫磺二十斤、艾草五十束。”
硫磺气味刺入鼻腔时,周文远猛然醒悟。赵家祠堂香炉灰中,正混着这等刺鼻粉末。他连夜提审赵家马夫,得知赵德贵每月初七必往城西土地庙上香。庙祝颤巍巍呈上签文:“去岁冬月,赵老爷抽得下下签,签诗写着‘蟾宫折桂反遭噬’。”
更深露重时,周文远翻开了《岭南异物志》。泛黄书页记载:火斑蟾需以人血喂养三年,方可成剧毒之蛊。某页夹着的宣纸上,赫然是赵德贵年轻时的笔迹:“广南西路,韶州府,天圣九年……”

五月廿一夜,雷声碾过汴梁城。赵家祠堂的百年柏木梁忽然断裂,香案倾覆露出地砖暗格。周文远抹去青铜匣上积灰,匣内密信让他瞳孔骤缩——工部侍郎陈广生的私印,竟盖在二十年前的韶州军饷调度文书上!
账册残页记载着惊天命案。天圣九年秋,韶州押送三十万两税银赴京,途中遭遇“毒蟾袭营”。幸存者仅赵德贵与时任韶州司仓的陈广生,而军帐废墟中,税银箱内填满河卵石。周文远抚过信纸上的褐斑:“这不是霉迹,是血渍。”
暗格底层躺着半块玉珏。玉身刻着“陈”字,断口处却与赵文礼颈间挂坠严丝合缝。青年被捕时惨笑:“我娘被赵德贵掳作毒蟾饲主,这块玉,是她与陈广生的定情信物!”

六月初一,开封府地牢弥漫着血腥气。赵文礼撕开囚衣,后背鞭痕交织如蛛网:“这些是赵德贵逼我娘驯蟾时留下的!他怕事情败露,连我都要灭口。”青年从鞋底抽出张药方:“火斑蟾毒混入曼陀罗花粉,可令人产生幻象,那晚他跌入池中不是意外!”
周文远在赵德贵书房有了新发现。镇纸下压着未寄出的密信:“陈兄钧鉴,琼州船队已备,然毒蟾恐成隐患……”信纸边缘沾着墨绿色黏液,与荷花池畔的蛙毒如出一辙。更蹊跷的是,账房先生刘茂突然暴毙,尸身怀中掉出陈广生府邸的通行铜牌。
拼图逐渐完整。陈广生欲借毒蟾灭口,赵文礼趁机加重剂量;赵德贵察觉危机,本欲携证据潜逃,却终遭双重毒杀。祠堂那场“意外”火灾,实为赵文礼销毁生母驯蟾手札所为。
替身谜云六月十五大朝会,紫宸殿上风云突变。当周文远呈上玉珏时,工部侍郎陈广生抚掌大笑:“本官耳后何时有过黑痣?”御史中丞却抖出秘档:真陈广生左耳缺失,乃当年毒蟾所噬!
天牢刑架上,替身吐露惊天阴谋。原陈广生五年前病亡于扬州别院,其庶子买通仵作李代桃僵。这个秘密被赵德贵在岭南旧部识破,勒索信却误送至赵文礼手中。周文远把玩着从替身发髻搜出的毒囊:“你们在赵德贵酒中下的慢性毒,本打算七日后发作?”
赵家暗室另有玄机。夹墙内藏着的鎏金蟾蜍像,双眼镶嵌的夜明珠上,密布着驯养毒蟾的刻度。转动蟾首,底座暗格弹出半卷《百毒谱》,其中朱笔批注:“血亲之血,可御蟾毒。”

七月初三,刑部公堂剑拔弩张。李宪将惊堂木拍得震响:“弑父者当千刀万剐!”旁听的陈广生党羽却高喊:“假冒朝廷命官罪加三等!”周文远默然展开血书——那是赵文礼生母用眉笔写在亵衣上的陈罪状。
三司会审当夜,御史台送来密函。火漆印着宰相私章,信中只八字:“民不可欺,法不可违。”周文远将密信投入灯烛,在案卷添注:“赵文礼弑父为母仇,陈党乱政为国患,然私刑若开,则律法崩矣。”
秋决前夜,狱卒发现赵文礼面壁而泣。他蘸血在墙上画了幅驯蟾图,角落小楷写着:“硫磺二两、砒霜半钱、人发灰三钱,可绝蟾患。”
余烬未冷熙宁六年春,赵家宅院爬满野藤。某个雨夜,更夫看见荷花池泛起幽蓝荧光,第二日便暴毙家中。周文远奉命彻查,在池底淤泥掘出铁箱,内藏百只毒蟾尸骸与陈广生亲笔账册。
新任工部侍郎赴任途中,座船遭毒蟾围攻。幸存船工回忆:“那蛙群似有人指引,专攻门窗缝隙。”民间流言四起,说赵文礼化作了蟾神。而琼州传来的噩耗称,流人营中根本无赵文礼的入籍记录。
周文远调任荆湖南路那日,收到匿名药囊。艾叶中裹着张字条:“岭南湿热,望君珍重。”笔迹与赵文礼血书驯蟾图如出一辙。

元丰八年,秘阁失火焚毁陈年卷宗。看守老吏醉后吐真言:“那夜有人影闪动,带着股硫磺味。”同年,岭南进献的瑞兽图中,赫然绘着只背生人面的巨型蟾蜍。
周文远致仕后隐居嵩山,某日晨起见窗台摆着青铜蟾蜍像。像底刻着蝇头小楷:“法理昭昭,毒蛊荡荡。”当夜山雨倾盆,他仿佛听见熟悉的蛙鸣,推窗却只见闪电撕破夜幕。
后世《汴京异闻录》载:每逢夏夜暴雨,赵家废宅便传出金铁交鸣声,似有人在池畔撒药粉。更夫曾见青衫书生蹲踞残垣,转眼化作黑斑蟾跃入荷塘,而水面浮起的,是半片写着《宋刑统》的残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