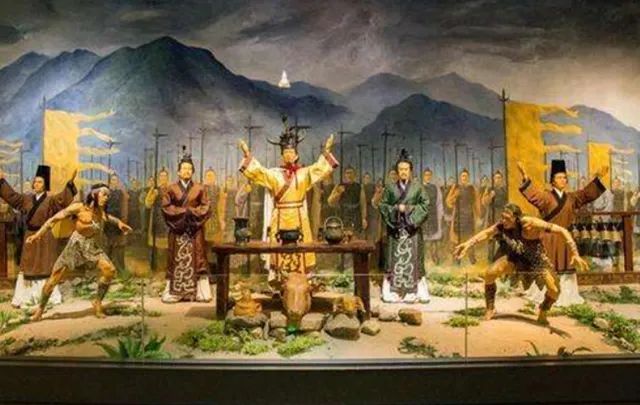

01野蛮战胜文明
北宋遭遇“靖康之变”被金人所灭。南宋则偏安南方,经历了与金元两朝漫长的抗争过程,最终为蒙元所亡。
因为辽、金、元、清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原王朝”,而是由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所以有一种说法叫“崖山之后无中国”,意思是崖山海战,宋代亡国之后,中原正统也就消亡了,文明被野蛮战胜了。
这种观点影响力很大,也很有迷惑力。我们即使知道它是错误的,但可能也并不清楚究竟错在哪里。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是我们理解过去一千年中国历史,理解我们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身份认同的关键。
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个问题开始说。

【北方民族王朝对“文明”内涵的丰富】
首先,思考一个话题是:什么是野蛮?什么是文明?
大家现在普遍接受一种观点:华夏文明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建构过程,但是在多元一体当中,还是会有这样一种认知,觉得中原相对是比较文明的,而周边地区,北方民族相对是比较野蛮的。
他们的文明水平相对比较低级,比较落后,在征服过程中,会使用一些残暴的手段。
这种看法不能说全是错的,中原王朝确实在政治、思想、文化、技术层面要更加发达,但是我们不能反过来,就简单的把北方民族王朝的征服和统治,看作是野蛮对文明的胜利。
准确地说,北方民族王朝是从其它几个角度,在不断丰富“文明”这个概念的内涵。
首先是军事文明。在讲一个王朝的“文明”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更多关注文化的维度,但容易忽视了军事这个层面。
可是“兵强马壮”本身就是是文明的重要形式。能不能构建起一个高水平、高质量、低成本、可持续的军事体系,这是文明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标准。
没有了军事能力、力量体系,所谓的“文明”“繁华”是很难长期维持的。
鲁迅先生比喻是:狮子肥壮是件好事,但是猪养肥了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所以,北方民族的军事能力是一个不能忽视的文明尺度。在前现代战争中,马匹是重要的战争工具,而马匹主要产自西北地区。
游牧民族生活在马背上,它的军事能力和生产生活方式是融为一体的,所以天然具备强大的骑兵作战素质,不像农耕民族需要高成本的投入和长期的脱产训练。
与此同时,游牧经济不如农耕稳定,所以抢掠本身就是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也就意味着发动战争是生存的必要条件。
因此中国历史上北方民族王朝的战争能力、战争韧性都很强。从前期的匈奴、鲜卑、突厥,到后半段的辽金元清,北族王朝以强大而高效的军事能力,加入中国历史的建构过程中,给中华文明注入了刚健俊爽的气质,也从另一个角度充实了“文明”这个概念。
除了军事文明之外,在政治文明方面,北方民族王朝有没有可取之处呢?当然有。
举个典型的例子:在南北朝的长期乱局中,为什么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能够统一北方,进而奠定隋唐帝国的基础呢?
这当然和他的军事征服密不可分,但更重要的是在政治和文化上,北魏统治者积极主动与北方汉族士大夫合作,将北方士族传承的儒家经典、秦汉制度和南北朝时期的社会需求相结合,建立起一套简明质朴的治理模式。
这种方式舍弃掉很多繁文缛节,有时会更接近治理的本质。为什么呢?因为政治是一个超级复杂的游戏,它固然需要一套发达的官僚制度,然而制度一旦太过复杂,又会走向它的反面,也就是“官僚主义”。
叠床架屋、人浮于事,变得低效、臃肿、繁复,不但失去了治理的意义,反而带来的更深层的破坏性。
另一方面,好的政治恰恰需要简单、明快,面向问题本身,这样不仅更加灵活高效,也更契合政治的深层规律。
从辽代以后,北方民族王朝实际上不仅是游牧帝国,同时也具有鲜明的二元属性。
辽朝既有长城以北的草原游牧之地,同时也有长城以南幽云十六州的农耕区域,实行南北面官制度:北面官治理塞外,南面官管辖汉地,以这种方式既保存游牧的勇武之风,同时也把农耕经济纳入统治秩序 当中。
后来的金、元、清几代都具有这种二元结构,因为不吸纳中原文明没有办法建立稳定的天下秩序,但过度“文明”又会疲软文弱,两者之间如何平衡,是非常考验政治智慧的。
政治智慧的体现,这种政治智慧体现在几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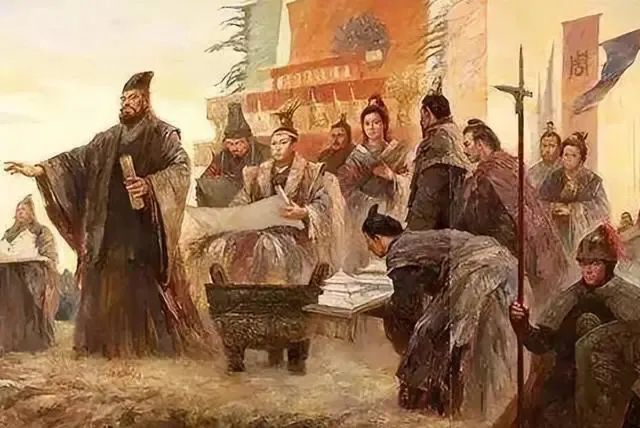
首先是决策过程的紧凑和高效。南宋思想家朱熹在和他的学生讨论宋金政治的时候,就指出:宋代虽然官僚制度很发达,但是也因此决策过程很繁冗,而且皇帝和大臣之间缺少一个小圈子议事、快速做决定的机制,很多事情在朝堂上争来争去拿不定主意。
最要命的是吵架也不当面吵,而是背后文书互相攻击来攻击去。朱熹就说,你看人家金人为什么打仗那么厉害,几个领头的大家往炕上一坐,吃个火锅,一边聊一边就把这个事决定了。
后来到清代的时候,军机处也是这样一个模式:皇帝居住的养心殿外,一个小房间、一张小桌子,重大军机问题,集中讨论,迅速拍板,这样就不会被官僚主义的因素牵绊太多。
除了决策高效之外,北方民族王朝的政治传统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重视私人情感在治理中的纽带作用。
比如元代有一种制度叫做“怯薛”,就是贵族子弟小时候到大汗身边当差或者当卫兵,从小在皇帝身边长大,长大之后,有才能的人被派出去担任官职。
元代虽然名义上有科举,但实行的次数很少,主要的官员选任通道就是怯薛。这个 制度是典型的用来维护蒙古贵族统治的,很明显有重大弊端,但是它也有一个好处:这些官员就像皇帝的兄弟或者子侄一样,有一个官方身份之外的私人情感联系。而这种私人感情对于维系广土众民的统治非常重要。
我们通常会说,治理一个大国要有完善的法制,这是必须的。但是在制度之外,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纽带、情感纽带也不能忽视。
中原王朝政治传统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皇帝和大臣之间的隔膜很深。大臣们都是通过文官体系成长起来的职业官僚,他们是“外朝”,而皇帝却生长于深宫,日常围绕着他的是由后妃宫女和宦官组成的“内庭”。
这种内外之别,非常容易带来隔阂,皇帝和臣僚可能互相尊重,但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信任。皇帝只能信任他身边的人,也就是宦官。要依靠宦官获取信息,甚至掌控军队。但宦官只能在内庭升迁,没办法进入真正的官僚体系,更不可能出任方面大员。
而一旦要掌控广大的疆域时,就需要统治者和地方官之间更深层的信任关系。想想看,如果没有一个私人的、情感层面的联系,一个统治者会放心地把自己手下的精兵良将交给另一个人去掌控吗?
这种私人关系,很多时候甚至会以“主奴关系”的形式呈现出来。
比如清代的制度中,大臣就是皇帝的家奴。只有特别亲厚的臣僚才有资格在写奏折的时候自称奴才,低级的或者疏远的官员还没这个资格。
这的确是一种陋习,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又对清代的版图拓展、疆域控制非常重要。
地方大员比如两江总督、两淮总督、湖广总督,这么重要的权位,他必须跟皇帝之间有一个比官方身份更深一层的亲缘关系。
而主奴关系是一种比亲缘关系还要更深一层的关系。在亲缘关系中彼此还是人格平等的,而主奴关系则意味着后者放弃了自我,以人格依附的方式表达忠诚。
这样反而在皇帝和大臣之间,建立起 一个更深层的精神联系。所以我们在清代的奏折批复中,能够看到“朕就是这样的汉子”这种掏心窝子的大白话,这个在中原王朝公事公办的文书中是见不到的。
所以为什么明代会受到宦官干政的困扰,而清代则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那不仅仅是皇帝下一道旨意,说宦官不许出京城,就完事了。
宦官代表着皇帝的私人意志,宦官不出 京,意味着皇帝有了其它的延展私人意志的渠道。宦官当家仆就可以了,政治上的奴仆有其他人担任,这样等于是把主奴关系、私人情感和文官体系兼容起来,从而建立起一 种更加复杂的君臣信任机制。
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是落后的、野蛮的,但它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清王朝能够打下这么大的疆域,并形成实质掌控,奠定现代中国的版图格局,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
“崖山之后无中国”讲法的错误,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北族王朝的军事、政治文化中包含的严重弊病。
一方面,军事征服是血腥残暴的,会在历史记忆里留下永远无法消除的伤痛;另一方面,主奴式的君臣关系也容易形成一种整体的奴性氛围,用对待奴仆的态度对待臣民百姓,反过来碰到更强大的对手时候也容易跪,容易卑躬屈膝、奴颜媚骨。
晚清政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就是如此。
我们来总结一下,北方民族王朝从军事能力和政治文化两个方面,为中华文明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整个中国大历史来看,我们会发现中华文明从根源上就是“多 元一体”的融合和建构。
孟子有一句话叫做“舜,东夷也;文王,西夷也。”这些圣王都是夷狄出身的。
西周王朝不就是以边缘小邦的身份翦伐大商而成为天下共主的吗?后来的秦汉隋唐,乃至辽金元明清等王朝,也都是这样一个碰撞融合、多元一体的过程。
只有宋代的情况比较特殊,有鉴于前唐五代的弊病,边界意识、华夷观念特别强。
从大历史角度看,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不是地缘整合,而是在治理深度、细密度,以及治理背后的哲学思想方面进行探索和挖掘。
这就是我们说中华文明的建构过程,既需要广度,也需要深度,两者缺一不可。
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讲法是完全错误的。还不是因为这种观点不符合民族融合的政治正确,而是因为它对“中国”的理解有严重偏差。
“中国”不是简单的文明繁华,更不仅仅是瓷器书画代表的“美学”。而是兼有广度和深度的文明主体性建构。
既有吞吐六合、兼容并包的雄浑气魄,也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价值情 怀,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之为“中国”的本质。
我们现在倡导多民族融合,强调多元一 体,但其实融合、多元、一体都不是目的,多元一体,最终是要建立起来一个高质量的文明共同体,“高质量”本身才是关键,不然弄个大杂烩有什么意义呢?
不同的族群融 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提升了我们文明的质量,让我们文明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才是民族融合真正的价值所在。
最后提出一个问题:你是如何看待私人感情在各个层级的治理体系当中的作用?一个好的制度,是应该警惕并防范私情呢?还是要做一定程度的兼容?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自己的看法!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