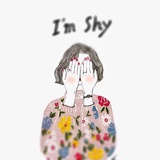洪学智晚年的时候回忆说,他最怕的人是彭总。因为在朝鲜的时候,洪学智作为彭总的副手(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及志愿军后勤司令,他挨彭总的批评是最多的,当然同时受到的表扬也多。
对此,洪学智表示说:“彭总这个人,批评人那是真厉害。那是不分场合地点,张嘴就骂。不过,彭总骂人那是亲,给你的感觉特别亲近,他并不会无缘无故地批评你,完全是从工作角度出发。因此,即使有的批评错了,我也毫无怨气。”
洪学智和彭德怀最早相识于长征路上。1935年7月,红三军团到了瞻化草地和四方面军会合。红4军政治部主任洪学智奉命接应中央红军,并为中央红军筹措了大批军需物资。
起初,军需物资直接送到红三军团。这段时期,洪学智结识了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

不过,抗战时期,两人接触较少,彭总长期在华北前线指挥抗战,而洪学智较长一段时间在苏北,隶属新四军。
至于解放战争时期,两个人更谈不上接触,一个在一野,另一个在四野。
直到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入朝参战,两人才有了并肩作战的机会,彼此之间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当时,彭德怀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任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洪学智任第二副副司令员,韩先楚任第三副司令员,解方任参谋长,杜平任政治部主任。
最初,入朝部队的吃穿用度,主要依赖鸭绿江对岸的东北军区后勤部来支撑。但随着战线的拉长,再加上东北军区后勤部的人手本就捉襟见肘,机构设置也难以完全适应一场现代化战争的需求。建立一个统一指挥、高效运转的志愿军专属后勤司令部,已经成了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任务。

那么,这个责任重于泰山、工作繁杂琐碎的“大管家”,该由谁来当呢?中央军委的指示很明确:就在志愿军现有的几位副司令员里选一位兼任。
当时,志愿军司令部里有四位副司令员: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还有一位是朝鲜方面的代表朴一禹。朴一禹同志自然不管理人选范围。剩下的三位,邓华和韩先楚都是久经沙场的战将,以指挥作战见长,几乎没有主管后勤的经历。数来数去,只有洪学智是最合适的人选。
早在红军长征时期,洪学智就曾临危受命,负责过部队的收容和后勤工作,展现了出色的组织能力。更难得的是,他具备成为优秀后勤指挥者的两大特质:一是记忆力好,对繁杂的数字、物资种类、部队番号和位置等信息能做到心中有数;二是心思缜密,考虑问题周全细致,善于从细微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在需要精确计算、统筹调配的后勤领域,简直是不二人选。

按理说,洪学智是众望所归的最佳人选。然而,当彭总找他谈话,准备把这副担子交给他时,却碰了个软钉子。
“老总,搞后勤?这不行吧?”洪学智一听,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他心里一百个不情愿。后勤工作太繁琐了,整天跟柴米油盐、枪炮弹药、车辆运输打交道,哪里有在前线指挥千军万马冲锋陷阵来得痛快?而且压力山大,责任重大,还容易挨批。
彭总一看洪学智这态度,那火爆脾气立马就上来了,眼睛一瞪,声调也高了八度:“洪大个子,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了?组织分配任务,你还挑肥拣瘦,这像话吗?”
洪学智还是有点犹豫,试图解释:“老总,不是我挑拣,只是我觉得在前线可能更能发挥作用……”

没等洪学智说完,彭总把手一挥,使出了“杀手锏”,干脆撂下一句狠话:“行,你不干是吧?那好,后勤这摊子我来管。你洪学智,替我到前面去指挥部队,怎么样?”
这话一出口,洪学智彻底没辙了,只好苦笑着,立正敬礼:“老总,我服从命令,这个后勤司令,我干!”
但洪学智也提了两个条件,他说:“如果我干不好就尽早撤我的职,换个比我能干的同志;等仗打完了,回国后不要再让我搞后勤了,我还继续搞军事。”
彭总一听就乐了,当即说道:“行,答应你。”
就这样,洪学智当上了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的第一任司令员。事实证明,彭总的选人非常正确。

洪学智虽然心里不情愿,但一旦接受了任务,就全身心投入,把他那过人的组织才能和细致作风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他的主持下,志愿军的后勤系统逐步建立健全,面对美军疯狂的“绞杀战”,硬是打造出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为前线几十万将士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彭总对他的工作,虽然批评依旧严厉,但内心的满意和倚重也是毋庸置疑的。
在第五次战役前夕,志愿军内部就打法产生了不同的意见。
彭总的意见是:主动出击,不能满足于在三八线拉锯,必须趁敌人立足未稳,集中优势兵力,在三八线南北地区,大胆穿插,坚决分割围歼敌人几个师(至少几万人),打出威风,然后再视情况向汉江以南发展,给敌人以更大的打击,甚至争取把美国人彻底赶下海去。这个想法,与远在北京的毛主席希望尽快解决战争、扩大战果的意图,是不谋而合的。

彭总之所以如此坚持,除了军事上的考虑,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当时战场上盛传美军可能效仿仁川登陆,在志愿军后方实施大规模登陆作战。一旦敌人成功在侧后开辟第二战场,几十万聚集在三八线附近的志愿军主力,将面临腹背受敌的灭顶之灾。彭总希望通过一次大规模的主动进攻,打乱敌人的部署,粉碎其可能的登陆计划,掌握战场主动权。
然而,出乎彭总意料的是,他的这个打法在他主持召开的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上,几乎是一片反对之声。
第一个站出来明确提出不同意见的,正是洪学智,他说:
“老总,您的决心很大,但恕我直言,目前主动全线出击的风险太大。我建议,还是采取咱们之前证明行之有效的战法,把敌人适当放进来一些,诱至铁原、金化这个‘腰部’地区再打。在这里,地形对我们有利,也便于我军后续部队展开,实施拦腰截断,更容易达成成建制消灭敌人的目的。如果我们主动打出去,敌人一受挫就可能利用其机械化优势迅速后撤,我们很难追上,容易打成击溃战,达不到歼敌数万的目标。而且,我们刚入朝的几个兵团(指三兵团和十九兵团)需要时间适应和准备,诱敌深入可以为他们争取宝贵的时间,做到以逸待劳。”

洪学智的发言,立刻得到了其他几位副司令员和高级将领的赞同。邓华、韩先楚,以及参谋长解方等人,都纷纷表示,洪学智诱敌深入的方案更为稳妥,风险更小,成功的把握更大。他们担心主动出击会过早暴露我军意图,且在敌人掌握制空权和地面火力优势的情况下,强行突击可能导致我军付出巨大伤亡,后勤补给也难以支撑过于深入的进攻。
会议室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凝重起来。彭总没想到,自己的作战计划会遭到几乎所有核心将领的一致反对。他本来就因为担心敌人登陆而心急如焚,现在看到大家“畏首畏尾”,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便猛地一拍桌子,说:“你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个仗到底还打不打了?”
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大家都被彭总这突如其来的雷霆之怒震住了,谁也不敢再开口。

沉默片刻,还是洪学智首先打破了僵局。他站起来,语气依旧是尊重的,但立场并未动摇:“老总,仗肯定是要打的,而且要坚决打!我们这些人,都是您的参谋。参谋的职责,就是把各种可能的情况和我们的建议摆出来,供统帅决策参考。至于最后采纳哪个方案,决心还得您来下。”
紧接着,邓华也赶紧补充道:“是啊,老总。您不是让我们畅所欲言吗?我们的看法就是这样,供您参考。最后您定了调子,我们保证坚决执行,绝不打折扣!”
两人这番话,既坚持了自己的意见,也给足了彭总台阶,表明了坚决服从命令的态度。彭总听了他们这番“软中带硬”的话,脸色稍缓,但也陷入了沉默。邓华和洪学智又趁机再次陈述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理由和好处。
彭德怀在会议室里来回踱步,紧锁眉头,反复权衡。最终,他对敌人可能登陆的担忧,以及尽快打破僵局的决心,还是占据了上风。他深吸一口气,最后还是决定:“就按原计划打,立即准备!”

会议不欢而散。大家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只有洪学智,似乎还不“死心”。他留了下来,陪着彭总一起吃晚饭。饭桌上,气氛依然有些沉闷。
洪学智看着彭总似乎还在思考着什么,瞅准一个间隙,鼓起勇气,再次开口:“老总,我知道您已经下了决心。但按照规矩,当参谋的有三次建议权。刚才会上算一次,会后我找您汇报算一次。现在,我想再跟您提最后一次我的想法,说完这次,我就坚决执行您的命令。”
彭总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没有作声,算是默许了。
洪学智便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详细地阐述了他的顾虑:“老总,主动打出去,看着痛快,但很可能抓不住敌人主力。敌人有汽车轮子,我们靠两条腿,一旦打成追击战,我们的人员疲劳,地形不熟,追不上不说,关键是补给线会迅速拉长,大大超出我们后勤的保障能力。那时候,前线部队缺粮少弹,反而可能陷入被动。而把他们放进来打,虽然要暂时放弃一些地方,但可以集中兵力,选择有利地形,扎紧口袋,全歼敌人的把握更大,后勤压力也相对小一些。”

这一次,彭总没有发火,也没有打断他。他只是默默地听着,拿着筷子的手悬在半空,对着饭碗若有所思。良久,他才缓缓说道:“洪大个子,你的意见,有道理,我不是不明白。但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战场太狭窄了,把那么多美国坦克放进我们控制的区域,一旦处理不好,也是个大麻烦啊!” 他说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另一个顾虑。
洪学智立刻回应:“老总,坦克进来固然难对付,但总比我们冲出去,面对敌人海陆空一体的火网要好一些吧?我们在自己的地盘上,总还能利用地形,组织反坦克火力。要是我们冲远了,后援跟不上,那才是真的危险!”
彭总听完,没有再说话,只是低头继续扒拉着碗里的饭。洪学智见状,也适时地闭上了嘴。

最终,第五次战役还是按照彭总的原定计划发起了。战争的进程和结果,不幸被洪学智等人的担忧所言中。志愿军虽然初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未能达成大规模歼灭敌人的目标,反而因为战线推进过远,后勤补给严重困难,在敌人随后的反扑下遭受了不小的损失,部分部队甚至一度陷入险境。
战役结束后进行总结时,彭总的内心无疑是沉重和自责的,他丝毫没有回避自己的失误。不久后,他特意把洪学智叫到自己的住处,诚恳地道歉:“五次战役的事,是我指挥失误了。战前,你给我提了三次建议,都是好意见,很有道理,可我没听进去,一意孤行了。事实证明,你是对的,我错了。我这个做统帅的,决策失误,要向你检讨,郑重地向你道歉!”

这番话,从彭总这样一位战功赫赫、性格强硬的元帅口中说出,其分量之重,可想而知。这不仅仅是对洪学智个人意见的肯定,更是彭总光明磊落、勇于承担责任、实事求是的高尚品格的体现。他错了就是错了,敢于在下级面前承认错误,这在任何军队、任何时代,都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品质。
正是这种“对事不对人”、以革命事业为重的胸怀,使得彭总虽然脾气火爆,批评严厉,却依然能赢得大家的衷心敬佩和拥护,怪不得洪学智说:“彭总骂人那是亲,给你的感觉特别亲近,他并不会无缘无故地批评你,完全是从工作角度出发。因此,即使有的批评错了,我也毫无怨气。”
在朝鲜这段时期,洪学智和彭德怀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以至于后面彭总身陷囹圄时,洪学智还出来仗义执言,这一点尤为难能可贵。

1960年,洪学智从总后勤部调到吉林省工作,任省农机厅厅长。在吉林,洪学智一呆就是17年。
1965年秋天,毛主席南下巡视,在与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闲谈时,曾提到洪学智。
伟人问道:“好久没有见到洪学智了,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吗?”
韩先楚回答说:“我也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听说他被调到吉林工作了。”
随后,毛主席又接着说:“下次你见到洪学智时,帮我转告他,他之前的事没有什么大不了,让他不要担心。”
后来,韩先楚将毛主席的这番话转告给了洪学智,洪学智心里非常感动,并示意自己现在的工作很好,学了很多东西,请主席不要挂念。

1977年9月,洪学智调回北京,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之后再次出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为我军的后勤事业的现代化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88年冬天,为了纪念抗美援朝胜利30周年,洪学智受邀撰写回忆录《抗美援朝战争回忆》。
在谈及彭总时,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将军不禁潸然泪下,说:“老总,真想你啊!”
2006年11月20日,洪学智将军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