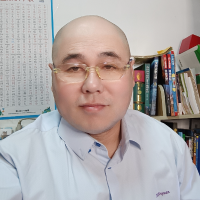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频繁抛出“吞并加拿大”的言论,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从经济施压到主权争议,从历史纠葛到地缘博弈,这场看似荒诞的“吞并”风波背后,折射出美加关系的深层裂痕与国际秩序的复杂挑战。 自2025年2月起,特朗普多次公开表示“加拿大应成为美国第51个州”,并将此定位为“严肃的政治目标”。3月21日接受采访时,他再次强调这一主张的“严肃性”,声称美国每年为加拿大承担2000亿美元经济补贴,并批评加拿大作为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过低却依赖美国军事保护。

他甚至质疑1908年美加边界条约的合法性,认为两国笔直的边境线是“用尺子人为割裂”,暗示要重新划定边界。这种言论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伴随具体经济胁迫同步推进:3月12日,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钢铝产品加征50%关税;4月2日将启动的汽车关税威胁,更被特朗普称为“足以使加拿大汽车制造业永久停业”。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直言,这些措施实为“经济吞并的前奏”,目的是通过摧毁加拿大经济实现政治兼并。 面对美方攻势,加拿大展开全方位反制。经济层面,联邦政府宣布对1350亿加元美国商品加征25%报复性关税,安大略省则对输美电力征收25%附加费,并威胁切断电力供应——该省每年为美国三州150万户家庭供电。政治层面,特鲁多3月初紧急面见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强调“维护主权是最高优先事项”,试图通过英联邦机制寻求国际支持。

此举触及英国王室“统而不治”的宪制传统,白金汉宫虽未公开表态,但舆论压力持续升温:加拿大前公务员公开质疑“若国王不能捍卫主权,其存在意义何在”。与此同时,加拿大加速推进国防自主化,暂停价值190亿加元的F-35战机采购计划,转而与欧盟洽谈防务合作,外长乔利明确表示要“构建摆脱美国依赖的防御体系”。 这场风波暴露出多重结构性矛盾。经济层面,美加日均20亿美元贸易额中,加拿大90%出口依赖美国市场,能源管道与产业链深度交织,这种不对称依赖使特朗普得以挥舞关税大棒。政治文化层面,特朗普将加拿大视为“天然延伸”的地缘认知,与美国历史上多次北进企图一脉相承——从1812年战争到19世纪“天定命运”论,扩张主义思维始终潜伏。

现实政治层面,特朗普将加拿大预设为“民主党蓝州”的担忧,折射出美国内政对外交的扭曲:即便吞并纯属臆想,相关言论也能转移国内矛盾、巩固保守派选民支持。 国际社会反应凸显当代治理困境。英国在“英美特殊关系”与英联邦义务间进退维谷,首相斯塔默屡次回避评论,王室则陷入“象征性支持”的微妙平衡。欧盟虽与加拿大加强防务合作,但实质性行动有限。加拿大民间的抵制浪潮——从取消赴美旅行到体育赛事政治化——展现小国面对强权时的身份焦虑,28万人联署取消特朗普幕僚加拿大国籍的请愿,更是情绪化抵抗的缩影。 历史经验表明,经济胁迫难以消解主权意识。1812年美军北侵失败,印证了加拿大民众的抵抗传统;如今特鲁多号召国民“购买国货、抵制美货”,安大略省以能源为筹码反制,都延续了这种抗争基因。

但全球化时代的对抗更具复杂性:加拿大若彻底转向欧盟,可能触发更大范围贸易重组;美国单边主义持续升级,或将动摇北美自贸体系根基。正如渥太华大学学者所言,这场危机像“打开的潘多拉魔盒”,既考验英联邦体系的现代适应性,也迫使各国重新审视经济主权与安全自主的边界。 当特朗普戏称特鲁多为“加拿大州长”,当查尔斯三世的沉默引发宪制危机,当2800公里边境线成为政治筹码,这场“吞并”闹剧已超越常规外交摩擦,成为观察国际秩序演变的特殊棱镜。其最终走向,不仅关乎美加关系,更将揭示21世纪主权国家如何在霸权阴影下寻找生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