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维文学创作最有成就的是杂剧,其杂剧集《凌霞阁内外编》包含杂剧十五个[1],惜已不存。现存杂剧八个[2],即《苏园翁》《秦廷筑》《金门戟》《闹门神》《醉新丰》《双合欢》《春明祖帐》《云壑寻盟》,前六个收入清顺治十八年(1661)刊《杂剧三集》,后两个被笔者发现于明刊本《茅洁溪集》中[3]。

《杂剧新编》
茅维自己曾言:“山民隐居放言,感近事而益激烈,拟献《丹扆六箴》。未已也,而撰《辕下商歌》三卷;犹未已也,而演《凌霞阁内外编》十五剧。”[4]可知其杂剧是有感于时事而作,重在表达自己思想,特别是《醉新丰》《双合欢》《春明祖帐》《云壑寻盟》四个杂剧,带有明显的自传性和时事性。因此要准确解读茅维的这些剧作,把握其精神实质,必须对其生平思想有深入研究。
目前学界专门研究茅维杂剧的四篇论文中,力作当数孙书磊的《茅维及其凌霞阁杂剧考述》。该文不仅指出茅维杂剧在体制上对元明北曲杂剧的明显突破,而且精辟地揭示出茅维杂剧独特的思想内涵是由其独特的经历决定,并认为《双合欢》“剧中的勾曲外史实则影射现实中的作者”,而《醉新丰》中马周入仕前遭遇,“恰恰就是作者的现实生活缩影”[5]。
然而,由于孙先生并未阅读到茅维《北闱蕡言》《十赉堂甲乙集》《十赉堂丙集》《茅洁溪集》等最能揭示其独特经历的别集[6],以及《春明祖帐》《云壑寻盟》这两个很有自传性和时事性的杂剧,故该文对茅维生平及杂剧研究不够到位[7],对其杂剧的自传性与时事性还未进行具体深入地探讨。

《春明祖帐》与《云壑寻盟》的自传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勾曲外史原型即茅维自己,洁溪是其隐居之地;二是剧中张更生、万炜、郭振明、刘曲周均是茅维友人,与张更生偕隐洁溪、同礼普陀是实有之约,且刘曲周治河冤死与朝廷但责列侯供办铠马是当时政治事件。

《茅维研究》
1、勾曲外史原型即茅维
《春明祖帐》中,万炜、郭振明问及张更生归隐后打算,张氏说:“小弟原与吾友勾曲外史有投老结邻之盟。此归住家旬月,即当尽室南行。”
《云壑寻盟》循此而来,写他归田不久,即携妻渡江,访旧洁溪。故该剧中率全家接待宴请张更生夫妇的洁溪主人——“正生外史道服上”的“外史”,即勾曲外史。
笔者以为勾曲外史原型即茅维,理由主要有三:
一是勾曲外史在《双合欢》中也出现,自称“坚隐洁溪”,而茅维隐居洁溪。洁溪在现湖州市吴兴区埭溪境内,茅氏祖先即从湖州埭溪迁湖州花林。
茅维移居洁溪在万历己未(1619),其《闲适诗引》曰:“洁溪一曲,经营十年。丙辰甫及开山,己未竟已移室。”此后除了时而出山,赴京应试,或谋求进用,茅维基本隐居于此。
洁溪别墅中有凌霞阁[8]、林光楼[9],别墅左边有离垢园[10]。茅维晚年著作合为《茅洁溪集》,中有《洁溪花史》《凌霞阁赋》《凌霞阁小品》等。其《凌霞阁赋》曰:“山民之徙洁溪也,倏十五祀于斯矣。”黄晦之曾为茅维画《洁溪图》,茅维有自题诗[11]。

茅维《洁溪花史》
茅维还自称洁溪山民,其诗歌对洁溪风光与隐居生活有细腻描写,如《洁溪二十咏》《洁溪山园十二咏》等[12]。茅维还曾发布招友偕隐洁溪启示,即《山栖九友招隐赞引》。据其诗文集可知,张圣标、刘荣嗣、夏登之、嵇湛侯、邵餐之等人与他皆有偕隐洁溪之盟。
临川章光岳与茅维说,“愿借洁溪一曲退老”[13];家住太湖滨的万载县令韦叔万,也极爱洁溪风土,“屡移书卜结邻”[14]。当时主动往洁溪拜访茅维的更是有括苍黄叔象、山阴赵佩之等十余人。
据此可知,茅维不仅坚隐洁溪,而且其洁溪在当时有一定知名度。
二是茅氏自称三茅后裔。
世俗将“句”字写作“勾”,故“勾曲”即“句曲”,而“句曲”即句曲山,在今江苏句容县东南,其形曲折似“句”字。东汉时有茅氏三兄弟来此修道,终成正果,后人因称他们为三茅真君,称此山为三茅山。
茅氏家族好道,茅坤结交道人无数,董九华、雷道士、沈炼师、醒神翁等十余位道士频现其诗文集中。在给亡弟茅艮写的墓志铭中,茅坤说到自己兄弟三人被当地人称为“三茅君”[15]。
茅元仪《亡姬陶楚生传》写及他曾在句曲梦到一道士,道士问他:“客从句曲来耶?句曲见尔祖否?”茅元仪答曰:“仆不佞,幸托神明之胄,然相距二千载,翁何相诳耶?”[16]此对话明确把湖州茅氏视为句曲山三茅真君后裔,而茅氏自称三茅后裔这个信息,也为其友人所熟知。

《石民四十集》
守节抚孤的姐姐去世后,茅元仪乞名人诗文,汇为《旌志乘》,以表彰其志节。该集所收曹能始诗歌开头即曰:“句曲三茅岭,临江跨上都。联翩升紫极,兄弟情相于。孰知千载后,其裔在下菰。”[17]也是把湖州茅氏视作三茅后裔。
正因为此,茅氏虽也佞佛,但道教思想对男性族人似乎影响更大。茅维《云壑寻盟》杂剧中,作为正生角色的勾曲外史即以“道服上”,且《云壑寻盟》《醉新丰》等杂剧也都流露了茅维的道教思想。
三是茅维以曾经隐居句曲的两位高士陶弘景、张雨自期。元代张雨居于句曲山黄筏楼,号贞居子,又号“句曲外史”,其集因名《句曲外史集》。
吴郡徐良夫《句曲外史集序》曰:“陶弘景在齐梁时,挂冠居句曲山,自号华阳隐居。……后七百余年,当元盛时,贞居以儒者抽簪入道,自钱塘来句曲,负逸才英气,以诗著名,格调清丽,句语新奇,可谓诗家之杰出者。”[18]张雨性狷介,常眇视流俗,独与湖州赵孟頫相善,赵氏每以陶弘景期之。
茅维则以陶弘景、张雨自期,其堂名“十赉堂”,诗文集名“十赉堂集”,“十赉堂”的命名即典出陶弘景《授陆敬游十赉文》。陶氏在茅山修道,终有所成,他认为弟子陆敬游有功劳,遂赏赐他如意、香炉等十种便于修炼的工具。茅维好道,曾援此例,请友人赠送修道之物,其中陈继儒所赠乃句曲外史黄玉印。

茅维《十赉堂集》
陈继儒《十赉堂甲乙集叙》曰:
《十赉堂集》者,吴兴茅孝若所著也。尝援陶隐居赉陆敬游例,人赠孝若一文物,曹能始贻以沉香枕,董玄宰贻以李邺侯端居室连环玉印,余贻以句曲外史黄玉印,其他不胜纪。(茅维《十赉堂甲乙集》序言,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刻本)
茅维以三茅后裔自许,又有了句曲外史黄玉印,自称“句曲外史”也就顺理成章。
2、剧作中的茅维交友圈
(1)张更生
张更生是《春明祖帐》中主人公,他和勾曲外史有两个约定,一是投老结邻之盟,二是同瞻普陀之约,《云壑寻盟》中他实现了这两个夙愿。细读茅维别集,张更生是茅维好友,且两个约定也是实有之事而非文学虚构。
张更生,即张圣标,字念堂[19]。崇祯初,脱珰祸后,改字更生。侯恪《晤张圣标圣标以忤珰下狱论死今上位始出之》诗“多难逢时字更生”一句可证[20]。
刘曲周《简斋先生集》文选卷三有《大金吾张更生先生七十序》[21],记载张氏事迹甚详。籍父荫,起家武科,倜傥好义,能担大任。天启间,为卫尉治兵。时魏忠贤擅权,势倾人主,诸士大夫有反对者,均被一一治罪。将军某是魏忠贤爪牙,气焰也十分嚣张。张更生得罪了他,遂被下诏狱。崇祯登基,魏忠贤势败,张氏始脱虎口,官升锦衣卫指挥使,即序中所谓“大金吾”。

《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
茅维与张更生的交往始于万历丁酉(1597),其《别张圣标歌》有“交期聚散历三酉”之句,并自注曰:“谓始丁酉迄今辛酉”。辛酉即天启元年(1621),距万历丁酉前后已二十五年,故诗歌曰“我交张长公,略已逾二纪”。
万历癸卯(1603),茅维得张圣标书问,“所陈皆庙社,为忆岂畋渔”,遂寄诗相酬,自述在家乡的寂寞情形,“揆予躭寂寞,怀古独踌躇。尽日书慵把,弥旬发不梳”[22]。
次年,茅维有《答张圣标书》,一方面为张氏开采诸疏叫好,以为“就局斡旋,为功非细”,另一方面念“讹言繁兴,辇毂鼎沸,直木先伐,道在括囊”[23],深为张氏处境担忧。
从茅维与张圣标交游诗歌来看,张氏年长于茅维,两人情同手足。茅维京城应试,多寓居韦园寺,张氏常来联床夜话,“长公北州豪,交谊弟昆笃”[24],“兄事延州弟畜予,风雨连床话萧寺”[25]。
天启元年,茅维应举,十试不第,铩羽南归,作《别张圣标歌》,“我困国子生,十科竟不第”,时张氏亦久居金吾而不迁,“君老执金吾,腰犀官不徙”,故两人颇能共情。诗歌有两人拥被同宿、茅维夜半闻鸡而叹的细节:“我尝对君拥幞被,夜闻荒鸡蹋君起。时无英雄叹广武,岿然灵光吾与汝。”
茅维与张圣标的交游诗多为长篇,不少诗歌有招张氏来江南或洁溪偕隐之意。如乙集卷十三《寄张圣标》,茅维问张氏“何时下吴会,文咏共搴裾”。又丙集卷六《别张圣标歌》,茅维以湖州长兴箬酒之好招张氏,“长安酒人何所是,何不亟寻远游履。偕我江南乐忘死。纵不买田谋徙家,饮酒无如三若美”[26]。

茅维《十赉堂丙集》
天启癸亥(1623)六月,茅维作纪梦诗寄之:“梅雨初收暑气清,山窗频梦故人情。交存白发空相忆,道在青山合耦耕。分宅何须怀小筑,轻装应早卜南征。依然阡陌桃源口,泻出红泉可濯缨。”[27]诗歌邀请张氏早日轻装南下,一起隐居耕作,并明确提到“分宅”,与《云壑寻盟》中描写一致。
次年,茅维作《申别十章甲子冬仲北还舟中作·列人张圣标金吾》诗,写张氏“陆沉三十年,晚进金吾督”,因“飞语起同局”,被革去职务,茅维因此劝说他,不如和自己一起买山隐居,“买山林虑中,寻盟返初服”。他招隐张氏曰:“我必挽子南,洁溪呼黄犊。解汝金仆姑,休我烟萝屋。屋头千琅玕,可敌腰围玉”。由上可知,张氏与茅维的投老结邻之盟是实有之事。
关于剧中同礼普陀之夙约,现实中茅维也有诗寄张更生,催促他早点辞官南礼普陀:“挂冠神武定何如,解印归来好著书。卖友郦寄皮相浅,赴秦张耳设谋疏。陆沉勿恋三升醖,礼佛犹乘四望车。何日南征访桑落,临流濯足一轩渠。”[28]
此诗诗题即作“寄大金吾督张圣标,趣其乞身南礼普陀”,创作于崇祯庚午(1630)后[29]。颈联用典,自注“使沈庆之事”,对应《春明祖帐》剧中人物对话:“更生兄,只你此番锦旋,分明是贺季真乞得鉴湖,长生堪筑千秋观。那羡他沈庆之长往田里,行乐惟乘四望车。”
据颔联郦寄卖友和张耳、陈余由好友变仇人的典故,可知张圣标曾遭遇类似事件。联系丙集卷九《寄慰列人张圣标再用前韵》“知君赦后还乡井,投老江南杖屦从”两句,张圣标还可能曾因此入狱。
出狱后,他辞去官职,故茅维催张氏南礼普陀诗首联有“挂冠神武”“解印归来”之句。上述两诗一写张圣标“赦后还乡”,“投老江南”,一写“解印归来”后,南下访桑落,礼佛普陀,这都与剧中张氏辞官回乡,不久下江南,访友洁溪,同礼普陀的描写一致。

《杂剧三集》目录
(2)刘荣嗣
《春明祖帐》写张更生哭奠友人刘曲周。刘曲周即刘荣嗣,字敬仲,号简斋,一号半舫[30],河北曲周人。他与张更生是同乡兼友人。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清岳濬修、杜诏纂《山东通志》卷二十七,清徐宗干修、许翰纂《济宁直隶州志》卷六等有传。万历丙辰(1616)进士,除户部主事,改吏部稽勋郎中。出为山东参政,历布政司。入为光禄寺卿、顺天府尹,拜户部右侍郎。崇祯六年(1633)以工部尚书身份总理河道,崇祯八年被逮下狱,崇祯十一年去世。有《简斋先生文选》《简斋诗抄》等行世。
据刘、茅二人别集,张更生、鹿伯顺、谭元春、潘朗士等均是两人共同友人,其中张更生是把茅维推荐给刘荣嗣之人,时刘氏官稽勋司郎中,掌管稽核在京文职官员的廪俸。
《丙集》卷六《别刘半舫司勋歌》是茅维京城留别之作。诗歌开头写张氏的引荐和两人一见倾心,“侠烈祗有张金吾,为言刘侯洵长者。介我谒君棨戟下,肝胆如霜一朝泻”。
此次见面是在茅维进场应试之前,刘氏对茅维制艺文十分赞赏,对其后来场中之文也揄扬有加,可惜茅维依然败北。刘氏为慰问茅维,置酒斋中,邀请张更生作陪。
三人畅谈至半夜,茅维拔剑而舞,啸歌慷慨,“丙夜罢酒谈端雄,雄心一片气吞虏。拔剑为君浑脱舞,若泣若歌啸倚柱。失路不唱行路难,抗手别君发长安”。
诗歌后半部分邀请刘氏来江南游玩,“相思许命远游履,勿忘江南好山水”,除了游玩西湖,还应访旧洁溪,“应问幽人洁溪上”。
崇祯二年秋,刘荣嗣与茅维意外相遇于山东兖州西北新嘉驿站,立谈片时别去。后来茅维有诗相寄,刘氏亦赋诗报之,且把茅维视作可以倾吐心声的知己:“人厌我真兼自困,身多古疾苦难痊。何时却向渔山道,郁抱全舒知己前。”[31]

《简斋先生诗选》
刘荣嗣还有《寄怀茅孝若》,写国事维艰,力劝茅维出山:
方今东驱夷,西逐虏,海上有鲸蜀有虎。民命贱于菅,其财轻如雨。风林鲜安巢,君归归何所。君能走笔摇山岳,嘘气凝空作楼阁。肝肠雪白神秋水,许人宁厚不宁薄。使君归长林,知君何用深。多事正须才,君当知此心。英雄但说轻财耳,能持国柄惟管子。圯上老人书一帙,晨兴待君莫相失。(刘荣嗣《简斋先生集》诗选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46册,第521页。)
诗歌赞扬茅维的文学才能和待人之道,说国家处于多事之秋,正需用人,归隐不是上策,希望他能如张良一样建一番功业。
刘氏在顺天府尹任上时,茅维也有诗寄之,称颂对方寿张治河的卓异事迹,“暴胜威稜藏器久,王尊峻节守隄轻”,并以京兆尹张敞画眉的典故戏嘲刘氏[32]。
刘氏官至户部右侍郎,别称少司农,茅维《冬馆吟》有岁末对雪怀人之作《寄刘半舫少司农张念堂大金吾于燕中》,其中“已节金钱归少府”一句,即言刘氏为国家掌管钱财,节省开支。
《春明祖帐》提及刘氏因治理黄河而冤死。此事史料多有记载,其中以陈鹤《明纪》所载较详:
当时骆马湖运道溃淤,霍维华创挽河之议,请求自宿迁至徐州,别凿新河二百余里,以引黄河水通漕。刘荣嗣采纳其计,耗费金钱五十余万,而其所凿邳州,上下悉为黄河故道,其下皆沙,挑掘成河后,经宿沙落,河坎复平,如此者数四。

《明纪》
“迨引黄水入其中,波流迅急,沙随水下,率淤浅不可以舟。及漕舟将至,而骆马湖之溃适平,舟人皆不愿由新河。荣嗣自往督之,入者辄告淤浅,弁卒多怨。巡漕御史倪于义劾荣嗣欺罔误工,南京给事中曹景参复重劾之,逮问坐赃,荣嗣父子皆瘐死”,然“其后骆马湖复溃,舟行新河,无不思荣嗣功者”[33]。
创挽河之议者,史料一般直接言刘荣嗣,或曰刘氏误信“门客游士”之说[34],此处明确为霍维华。关于参劾之人,有些史料只提南京给事中曹景参,而不提巡漕御史倪于义。
这可能是因为主要参劾者是曹景参。他是刘氏仇家,因请托不成,怀恨在心,遂勾结倪于义,诬陷其侵吞治河款。
关于刘氏治河功过,史料评价基本一致:一是别凿新河,耗费金钱巨大,且存在新挖河道被黄河水冲刷后沙落淤堵情况;二是当时骆马湖溃堵适平,舟人不愿经由新河,但后来骆马湖运道再次溃堵,舟人只能经由新河,于是又都认为刘氏有功。
清人康基田认为:“荣嗣之功固可见,而罪亦有”,“与其靡五十万金钱,濬二百里流沙之河,何如专治骆马湖之溃决切近易效”[35],指出其在治河策略上的错误。

《河渠纪闻》
清人孙承泽则认为,“治河之役,鲜有免于吏议者”,但刘氏之所以受祸如此之惨,是因为当时阁臣温体仁方兴党论,“公之受祸,不仅为河”[36]。
据谈迁《国榷》卷九十六、万斯同《明史》卷三百六十二等史料可知,曹景参正是谄媚温氏者。因为刘氏涉及党祸,加上当时河患日棘,崇祯皇帝重法惩下,故即使后来舟行新河者无不为刘氏称冤,而且刘氏置身表表,为户部郎时已负时誉,但仍不免瘐死。
刘荣嗣因参被逮是在崇祯八年(1635)秋九月,去世则在崇祯十一年。《春明祖帐》中刘氏已被诬去世,停柩郊外寓所,张更生辞官后,前去哭别,为其喊冤。
剧中用了两段宾白和两支曲子。第一段宾白曰:“敬仲,敬仲,乡曲忝附襟期,羁囚亦同患难。兄犹自伶俜旅榇,弟何心踽凉还山。魂气既无不之,乡园定当偕返。”
这里提到两人不仅同乡,而且志同道合,还一起进过监狱,这些都与现实吻合。配合这段宾白的唱曲【闹樊楼】有茅维“提起自家旧事”眉批,印证宾白中“羁囚亦同患难”是写实。
第二段宾白和唱曲是张更生对刘氏治河事件的评论。宾白指出刘荣嗣志在治河,治河策略上可能有误,但不至于贪污,他的死是那班科参陷害:“仁兄河渠之役,志在濬复古黄河,不免误议少成,何至侵渔负国。圣里疑团不什,单为那班科参,飞章排陷,致君长恨入地,冤滥谁为问天,可痛可痛!”
唱曲【耍鲍老】指出天灾难料,刘氏治河无功,空费国家钱财:“那漕渠水自桃花发。淇园竹等浮苴,不仁河伯谁豫料,沉茭玉,填版闸。如云畚锸,少府金钱空决撒。臣罪当科罚。”

《明代戏剧研究概述》
宾白结合唱曲的这个评价,基本公允,而这也代表了作者茅维的评价,茅氏眉批曰:“我友敬仲,死非其罪,借此凭吊,尚有余哀。”
又曰:“敬仲误在复老黄河。甲戌春,予书切规之,已无及。至逮入,追论不了,实死于南科曹景参之手。”由上可知,剧本与眉批都涉及刘氏治河冤死这一政治事件。
(3)万炜
万炜是《春明祖帐》中前来为张更生饯行的人,他也是现实中茅维友人。字瞻明,李雯有《寿万瞻明驸马》诗[37],《春明祖帐》中博平侯郭振明即称其为“瞻明兄”。
尚明穆宗第五女瑞安公主,官驸马都尉,掌宗人府令。瑞安公主于万历十五年下嫁万炜,崇祯二年去世。按旧历,公主去世后,万炜的赡地二千五百顷要减一千顷,存留一千五百顷。然有人提议,因边需告匮,应以应存之数,作应减之数,以“少济时诎”[38]。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万历间万炜被辱一事:“戊子冬,驸马万炜奏司宫老婢沈银蟾与内使李忠盗金银等物,反遭诟辱。上大怒,谓圣母生辰烦渎,尽革其蟒玉,并夺所掌宗人府,即送国子监习礼三月再奏,而宫婢、内使盗窃诟辱等事不问也。”[39]
万炜在北京大兴县东建有曲水园。《(雍正)畿辅通志》卷五十三:“曲水园,在大兴县东,明驸马万炜建。”[40]万炜还有白石园,谈迁《北游录》曰:“又西,故驸马万炜之白石庄,花木差存,前为白石闸。”[41]白石园距西直门仅七里,在万寿寺附近,以芍药花著名。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曰:“又万瞻明都尉园,前凭小水,芍药亦繁,虽高台崇榭,略有回廊曲室,自云出自翁主指授。”[42]

《万历野获编》
《春明祖帐》中提到万炜的这个白石园,剧中他对张更生说:“小弟叨兄知爱尤深,岁岁白石小园,花时飞觞累日,下榻联宵。”
据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九,甲申之变前,崇祯曾命驸马都尉万炜以特牲告太庙。
清嵇璜《续文献通考》记载万炜及二子在甲申之变时殉国:“(崇祯)十七年,炜与其庶子长祚、弘祚皆殉难。”[43]
清钱保塘《历代名人生卒录》卷七曰:“万炜,国变死,年七十余。”[44]据此,万炜生年在万历三年前,年长于此年出生的茅维。茅维与他有交游,且交谊不薄。
《春明祖帐》茅氏眉批曰:“郭公交于甲子,万公交于庚午,真君子也,并笃友谊,特表出之。”这与剧中万炜与郭振明请张更生致意勾曲外史时的说法一致:“吾两人与此君交谊不薄,难后久疏闻问,望兄多多致意。弟辈不久乞差而南,决当问津洁溪,重寻林下风气。”
这里不仅“吾两人与此君交谊不薄”是现实中情况,而且“难后久疏闻问”也应属实。崇祯三年四月,茅维牵涉党祸,六月获罪,被械送出京城,次年被羁押候勘禾中铺,直至崇祯五年夏案解后,才回到湖州洁溪隐居。“难后”即指此次祸患被解除后[45]。
又明石文器《附万瞻明都尉》信札提及万炜“遂南游夙志”[46],故后一句“乞差而南”也可以落实,至于是否曾“问津洁溪”,则没有直接资料。
(4)郭振明
郭振明也是与茅维有交游的现实人物。字卫民,顺天府人。明光宗朱常洛郭皇后之兄,封博平侯。故《春明祖帐》中郭振明唱词曰“只我博平印在,带砺天潢”,又对驸马万炜曰:“吾两人忝称戚畹世臣。”
崇祯十四年三月,“博平侯郭振明益岁禄,荫锦衣卫指挥佥事”[47]。郭振明六十岁时,“更闻天爵膺新宠”[48],官左柱国太师,并拥有参加朝会的资格。
《春明祖帐》中有郭振明两段宾白,大致写实:

《戏曲与俗文学研究》第四辑
小弟自光庙上宾,便已落落,不谐于俗。逆珰时,幸免党锢。比十载,殊疏渭阳,宦同嚼蜡,门可雀罗。既无挂冠神武之期,徒切天际真人之想。
小弟在此戚畹朝班中,那里是好驴马不入行,不能自拔泥涂,终只逐人俯仰,食粟而已。奈何,奈何!(赵红娟、何等《新发现的明代戏曲家茅维杂剧两种》,《戏曲与俗文学研究》第4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33页。)
第一段即有茅氏眉批“此实情景”,可知写实。郭振明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
据东村八十一老人《明季甲乙汇编》卷四、彭孙贻《平寇志》卷十、钱士馨《甲申传信录》卷四等记载,甲申之变后,他被李自成军追银,拷打致死[49]。
其中《甲申传信录》对他有正面评价:“振明于戚臣中颇称贤而好义,虚躬下士。二月初,犹募宿儒于五城设教,令民间子弟负笈就学,使贫者不以脯修自用,一时贤之,而无补于时,惜哉!”[50]
太康侯张国纪是熹宗皇后的父亲,傅维鳞《明书》特别指出他亲近正人,而亲近正人的例子就是与博平侯郭振明交好[51]。
郭振明讲义气,谦恭下士。士人中,茅维即与郭振明有交往,“郭公交于甲子(1624)”,“真君子也,并笃友谊”[52]。

《沈德符集》
沈德符更是与他交情深厚,《清权堂集》卷十四有五言长诗《除夕前二夕郭卫民君侯携具见访话旧》、卷十六有七律《寿博平君侯郭卫民社兄六十初度时以左柱太师奉朝请》四首。
五言长诗中“时逢万历圣,交遍一时贤”“吾齿虽悭也,英游偶预焉”“骤报清途至,初疑梦境然”等诗句,都是在写郭氏礼贤下士。郭氏工诗文,“赋手凌云气薄霄”“雄篇时出万人传”等诗句可证之。据“天路神仙好坐邀”“游仙诗句有精神”等诗句看,郭氏好神仙,而这与《春明祖帐》中“徒切天际真人之想”的自谓一致。
然而郭振明谄媚魏忠贤,这颇为人诟病。魏忠贤势盛时,为他歌功颂德、题请建祠的人很多,郭振明是戚畹中的典型代表,“宗室则楚王华奎,外戚则武清侯李诚铭、博平侯郭振明,功臣则总督史永安、巡抚袁崇焕等,皆为题请”[53]。
李逊之《三朝野纪》记载郭振明等“疏请建祠,赐额名德芳”[54]。
朱彝尊《曝书亭集》说:“至都城内外,建祠尤多,勋臣则保定侯梁世勋、博平侯郭振明、武清侯李诚铭。”[55]而据汪有典《史外》卷六记载,郭氏所建魏忠贤生祠在安定门。
郭振明亲近魏忠贤,魏党甚至利用他来打击东林党人。盛枫《嘉禾征献录》卷三记载魏党借博平侯郭振明、新城侯王升的发葬费,来污蔑徐石麒贪污之事:

《嘉禾征献录》
(徐石麒)壬戌进士,除营缮主事,管节慎库,时魏忠贤掌惜薪司,石麒不顺指使,为黄尊素所得士,益忌之。补给皇亲博平侯郭振明、新城侯王升助葬银五千两,诬其受贿,削夺,东林党人榜有名。(盛枫《嘉禾征献录》卷四,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版,第2册,第12-13页。)
作为皇亲国戚,郭振民非但没有得罪魏忠贤,还亲近谗佞魏氏,上疏为他请建生祠,那自然能远离党锢之祸,故《春明祖帐》郭氏宾白中说自己在魏忠贤时代“幸免党锢”是实情。
《春明祖帐》结尾当张更生唱出“洁溪湾,端不让桃源古涧”后,万炜与郭振明接唱“我两人,也蚤晚拭拂珊瑚作钓竿”,然两人一在甲申之变时殉难,一在甲申之变后被拷打致死,均未能早作归隐打算。
(5)王鉴心
《春明祖帐》中万炜与张更生饯别时说,边警不断,朝廷却征讨无计,只会命令列侯掏钱治办军备,自己将成为王鉴心第二:“今日此别,边烽未息,城守徒劳。庙堂不闻挞伐奇谟,但责列侯供办铠马。弟已屡蒙严旨,想不久当为王鉴心之续矣。”这里提到的王鉴心是现实人物,朝廷“但责列侯供办铠马”也是当时实有之事。
王鉴心,即王昺(?~1637),河北保定高阳县人。他与万炜是连襟,万历十六年尚明穆宗第六女延庆公主,官驸马都尉、太子太师,掌宗人府事。为人刚直方正,因多次上疏,为在梃击案中奏对失序的刘光复申辩,而触怒万历皇帝,被革职为民,遣送回原籍。
泰昌帝即位,方从哲上疏,请求宽恕王昺,遂得官复原职。天启间,高阳县令唐绍尧得罪魏忠贤,魏氏欲置其于死地,王昺又与众人尽力申救。
崇祯十年,王昺上疏参奏首辅温体仁欺君误国,被再次夺爵归乡,不久病逝。《春明祖帐》剧本创作于王昺卒后[56],故万炜说自己“不久当为王鉴心之续”。

《明杂剧研究》
王昺有奏疏集《谏草》,当时名闻天下。赵春即膜拜其奏疏,认为不逊贾谊《治安策》,借来原本,恭录后奉还。孙承宗也赞扬其奏疏能尽言“众所不言”,“中间事系宫帏藩邸,俱天下大务”,“若持方药疗宿疴”,“更为救时良药”,可惜“群纷未谙兴制事,遂不行”[57]。
孙承宗有恩于王昺,且与他是高阳老乡,而茅元仪追随孙承宗,也常往来高阳,也许是因了这层关系,他与王昺交往密切。
《石民四十集》卷九十有写给王氏的信札,抬头为“西吴友弟茅元仪致书鉴心君侯道兄盟契”。万历丁巳(1617),王昺上奏疏三篇,论银海、国本及张居正之功,并疏救刘光复,而被革出都门。
茅元仪说自己恨不得被目为同党,这样死且不朽,并遣门人王观国至王鉴心处传达自己心意[58]。万历壬戌,茅元仪赞扬王鉴心练兵一疏,“圣人复起,无以加矣”[59]。而茅维是茅元仪叔父,与孙承宗也有交往,对朝政又十分关注,故其对王鉴心应有所了解,甚至可能有交游。
关于庙堂“但责列侯供办铠马”,剧本有眉批,曰“事详邸报”。查阅相关史料,万斯同《明史》卷二十四、杨士聪《玉堂荟记》卷一、孙承泽《山书》卷十三、李逊之《三朝野纪》卷六、计六奇《明季北略》、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二等对此事均有记载,其中以杨士聪所记最详:

《明史纪事本末》
上尝与韩城言及财用匮乏,韩城对以外则乡绅,内则戚畹。在乡绅者,臣等任之;在戚畹者,非出自独断不可。因以李武清为言,遂传密旨,借四十万金。冉、万二驸马各一万,而周、田等近亲不与焉。此旨间有抄传,复严禁之。李氏殊不在意,而督之日急。武清死,复及其子国安,提家人追比。
久之,国安亦死,而追比未已。周嘉定乃其儿女亲也,上疏为言,又奉严旨,于是李氏尽鬻所有,其房无人售,则拆毁卖之。内阁中书杨余、周国兴者,亦李氏亲也,教李氏云:“有形之产既尽,即不上纳,将如之何?”
久之,韩城侦知其故,密以闻上,因年终举劾两房官旧无此例,始自张淄川,遂劾二人闲住。有旨各廷杖六十,二人老矣,即日死。翌日,韩城夜归,下舆见杨、周二人在门内,忽失所在,韩城惧而计无所出。是时,戚畹人人自危。(杨士聪《玉堂荟记》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44册,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524页。)
韩城,即薛国观,温体仁因其素仇东林党,密荐于崇祯,遂得大用。
责列侯供办铠马事发生于崇祯九年,谈迁《国榷》卷九十五载有当年崇祯皇帝谕兵部圣旨:“今年饱飏,计来年复逞练兵、买马、制器、修边,刻不容缓。连年多故,帑匮民穷,令兵部司官借武清侯李诚铭四十万金发关宁治备,借驸马都尉王昺、万炜、冉兴让各十万金发大同、西宁;令工部借太监田诏金十万治甲胄,借魏学颜金五万治营铺。俟事平帑裕偿之,如尚义乐助,从优奖叙。”[60]
据此可知,剧中“但责列侯供办铠马”是崇祯朝时事,且驸马都尉王昺、万炜都在这份列侯名单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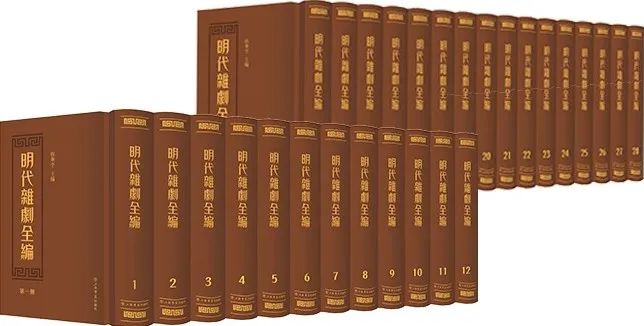
《明代杂剧全编》

《双合欢》的主人公是勾曲外史,而勾曲外史的原型即茅维,故此剧带有很强的自传性,是茅维风流情史的自我写照,剧中蕊珠和文漪的原型有可能是茅维家中仆妇徐碧玉、仆人徐淮。
《双合欢》写勾曲外史为家中小史文漪聘娶村女绛树,文漪姐姐“蕊珠”因弟娶妇而上门,勾曲外史原与她有旧情,遂趁机完了一段姻缘。勾曲外史同日还娶了家中婢女紫兰,于是一男二女同床共欢,故曰“双合欢”。
剧中蕊珠姓张,从小父母双亡,只有一个兄弟。见面时,勾曲外史责备蕊珠硬心肠、太妆乔,“歇过几多年,才肯一度降凡”,“几年来没音耗,并不怕咒人的惊肉飞、害眼跳”,而蕊珠却说,并非她心冷,是她前世没修好,所以今生受孤另,“俺今姿首已长,芳华渐谢,相公怎生尚提那旧话来”。
当勾曲外史打算晚上与蕊珠“尽把数年毷氉,枕边重诉,揾湿鲛绡”时,紫兰取笑说秋宵尚短,“你两人只可略叙新欢,怎好重提旧恨哩”。从上述对话可知,蕊珠是一位风尘女子。
剧中文漪是勾曲外史娈童,勾曲外史与他有私情。勾曲外史对蕊珠曰:“今你姊娣二人呵,连理共根苗。一般好滋味,怎分着苦李甜桃,龙阳怎泣前鱼钓。莫道俺得陇望蜀,吃一看两,福分难遭。”
此处“得陇望蜀,吃一看两”,并非指得了紫兰又想得蕊珠,而是指得了文漪又想得蕊珠。
一是因为“姊娣”一词除“姐妹”义项外,也有“姐弟”义项;二是此时紫兰其实还未圆房,文漪才能归入已得之列;三是“连理共根苗”指向姐弟,“泣前鱼”的典故也指向男性;四是紫兰听了勾曲外史这番话,对蕊珠说:“今日且看你兄弟的面,作成了相公这段姻缘,相公自越越疼着我文漪哥哩”,这里也指向文漪,而这“疼”字更能说明勾曲外史与他有私情。

《古本盛明杂剧》
《双合欢》中蕊珠和文漪的原型可能是茅维家中仆妇徐碧玉、仆人徐淮。徐碧玉,吴江人,曾为妓女,后归茅维。
甲集文部卷六《荐亡仆妇徐碧玉疏》:“亡仆妇吴江徐氏,业缘凑现,宿债都偿。曾以色事人之几何,终并影随君之永已。我离贪爱网,直临一副枯髅;汝脱烦恼缠,当证三生旧石。”
乙集诗部卷十六《客邸吟新诗讫感忆亡者碧玉、均卿并赋二绝以寄余痛》其一“吟罢新诗涕泫然,柔情一种似当年。芳魂倘化双蝴蝶,休近青陵墓草边。”诗有小注曰:“碧玉事详《松陵女儿行》。”
《松陵女儿行》在乙集卷五。从诗歌来看,徐碧玉当年颜色出众,“松陵女儿好颜色”,“初笄红颜玉不如”,虽然与茅维信誓旦旦,但不知什么原因,她拒绝跟随茅维,“直辞不载使君车”。
十年风尘中,她经历了无数挫折,“榜笞幽禁俱经历,甘筑刀镮碎阶石”,最后才回到茅维身边,“洗妆更侍巫阳台”,“巫臣终嬖夏征舒”[61]。
徐碧玉虽然已非少艾,“争妍斗艳非渠时”,但依然得到茅维宠爱,“一番风雨一番新,宛转娇啼若个真。岂思今日专房宠,竟是当年截发人”。徐碧玉为风尘女子,与茅维有过旧情,数年后才归属茅维,这些均与《双合欢》中蕊珠情况一致。
茅维有长诗《怨歌》[62],据小序和梅守箕《诗评》,可知此诗是纪万历壬辰(1592)、癸巳(1593)间茅维情事,完成于万历丙申(1596)。
小序曰:“予旧为《怨歌》一章,纪壬、癸间事,情惨绪繁,未竟辄罢。今复摭思往事,历缀成篇。”
梅守箕《诗评》曰:“(今年丙申)《怨歌》千言,……柔曼之情,委曲殆尽。孝若其有所托耶,抑亲遘此境而为此词也?”
而据诗歌正文,该女子亦为吴江人,“吴江春水木兰洲,是妾生来此中住”,一开始被卖为豪家奴,后入妓院,与茅维相识,“与君始识梳台里,晓镜蟠龙睡新起”。从此阴阳两谐,“颠倒回身就抱间,桂窗桂月影团圞。破瓜怯解鸳鸯扣,啮臂同留宛转环”。

《菰园初集》
两人情意缠绵,信誓旦旦,“蒲苇九秋纫如丝,盘石千年化为血”,但不知何因,忽然分别,“积成贝锦逢人怒,卷却红罗弃妾归。最怜霎时与君别,阿母槌床怒不歇”。
诗歌结尾说,“妾今偷生身尚在,莫问红颜改不改。富贵无忘白首盟,安排油壁车相待”,可见她最后也重新回到茅维身边。因此,该此女子很可能也是徐碧玉,此诗可与《松陵女儿行》互读。
徐淮,字均卿,茅家仆人,茅维与他私情甚厚。甲集文部卷五《亡仆均卿墓志铭》曰:“予童时,从先观察受书,遣仆均卿调护予。均卿长予八岁,遂相嬖爱,同卧起。后予壮受室,鲜闺房欢,益爱均卿不自持。”
茅维应该是一个双性恋者,因早年与同性同起卧,故婚后虽然夫妻感情较好,但很难找到性爱之乐,遂愈加宠爱徐淮。万历丁酉(1597)、庚子(1600),茅维两次进京应试,徐淮皆从行,时茅维是二十余岁的青壮年。
茅维三十岁后,家产日落,困顿不支。面对主人不事生产,旷浪不羁,徐淮忧形于色,时屏人切谏,至垂涕泪。
茅维说自己与徐淮“爱幸终始无间”,“虽亵媠,闻其庄语”,如对畏友。徐淮对茅维忠心耿耿,为其持家务二十余年。万历辛丑(1601),协助办理茅坤丧事;万历丙午(1606),茅维母病在堂,而得以进京应试,亦得力于徐淮为之持家秉[63]。
万历己酉(1609)九月,弥留之际的徐淮,闻茅维科举失利,大叫而卒。而京城落第的茅维,本思出塞散心,闻徐氏病笃,遂“踉跄驰还”,途中得其死讯,悲呼“均卿负予耶,予负均卿耶”。
徐氏卒后,茅维无情无趣,客人来访,“瞪目不语,坐客往往罢去”[64]。茅维有《归来望思曲》悲均卿之逝世[65]。

《明杂剧概论》
在《荐亡仆徐淮疏》中,茅维说:“亡仆徐淮,早岁相依,如左右手;中年见背,若参辰星。岂大恋之所存,犹余痛之莫剗。”[66]
万历庚戌(1610),茅维作诗感忆均卿,抒写余痛:“半生心事汝知侬,梦里伶俜一病容。销骨北邙魂气在,他年同穴定相逢。”[67]期待他年同穴相逢,这确实超出了一般的男男情感关系。
是年冬,茅维为之择地安葬,并铭之曰:“簮裾而婢妾其态,色庄而心若恧;慵奴而士人其操,嘿数而神不怍。是以予之丧均卿也,墓宿草而有余哀,哭诸寝而反缌服。嗣汝而为家监者,爱俪之而庄不属。”[68]
据茅维《亡仆均卿墓志铭》,徐淮娶妻朱氏。朱者,赤也,绛也,这与《双合欢》中文漪娶村妇“绛树”暗合。
当然,《双合欢》毕竟是文学,对现实也会有改造。如现实中徐淮长茅维八岁,而徐碧玉与茅维有过恋情,年纪不可能比徐淮更大,但为了戏剧情节线索的紧凑,剧中则把蕊珠和文漪设置成了姐弟关系。

《双合欢》中出现勾曲外史一僮一婢,僮即文漪,婢即紫兰,而《醉新丰》的主人公虽然为唐代马周,但他巡边建立功名后,华山仙主派骑牛叟,领着金童玉女,来迎接他归仙班时,剧中明确指出这金童玉女即文漪、紫兰:“只俺随侍仙官的文漪、紫兰二人便是,蒙华山仙主法旨,已先召俺们还了素灵宫,耑候仙官同修证果哩。”
据此可知,所谓的唐代“马周”即文漪、紫兰的主人勾曲外史,而勾曲外史的原型即茅维,故此剧带有很强的自传性。与《双合欢》写勾曲外史风流情事不同,此剧通过唐代马周来伤时骂世,并实现作者茅维的政治理想,故兼有较强的时事性。
剧中鵕䴊县令问马周:“秀才,你果行止无玷,怎么概县的多不喜你哩?”按:茅维曾提到自己以直道取怨乡里小人,有显贵者亦附和造谣,导致湖州一地知名人士都对他不满意,与鵕䴊县令所问正合。

《盛明杂剧》
甲集文部卷十一《复张郡伯》:“不肖半生肮脏,一腔热血,既以潦倒见轻于时,复以直道取怨乡曲小儿,遂至贵游和之,造作蜚语,遍憾湖之先达。”据这封回信,有人以茅维在京城“力可冬造雷而夏飞雪者”构陷之,遂使得“人人与维为敌”。
茅维初闻时非常愤懑,思与理论,为友人所阻。至写此信的万历壬子年(1612),茅维说自己意气渐平,大都毁誉听人,“且肆谗者原为通国所摈而不足校,亦有已败露而不必校者”。
剧中大净东门冷、小净西门热当是茅维暗指的“肆谗者”。作者把这两个人物写得极其丑陋。东门冷祖宗坟墓被掘,因老婆半夜调春药,引发大火,烧毁了内室书房。西门热爬灰,被儿子亲见。儿子遂犯了疯病,在家轮刀舞剑,出外四下狂走,被囚禁在木阱中,只喜欢吃狗屎粪渣,成了“逐臭之夫”。之所以取名“西门热”,是因为他口嘴利便,力能钻内,最后叨居清职,加五品服色,很是风光[69]。
西门热自述:
小子少不读书,只靠些口嘴,出入各位老师门墙。又都道小子力能钻内,有些不魐魀的勾当,都来寻着小子。区区难道望得见那司礼、东厂各老公的户槛儿?只靠与他们下掌家、小火者,或司房书办、缉事番子手们,合个瓶头,探些消息,便好去借里边声势,去吓那戴大头巾的。(茅维《醉新丰》第12页,邹式金《杂剧三集》第9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影印本)
可知,西门热是靠着从司礼监、东厂老太监手下人员中探听消息,以此恐吓士人的无耻官员。他还说:“俺与文书房老公个个串熟,曾与崔傅一班结十弟兄。”按:崔傅即明末阉党“五虎”之首崔呈秀,他官至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被封为少傅。
因此,西门热所言全是明代之事。西门热还对马周说:“闻得你有诗‘烈士终须一报恩’,今你报的恩在那里?”茅维确实写过这诗,其崇祯五年所作七律《壬申元日试笔》颔联即曰“幽人只合坚逃世,烈士终须一报恩”[70]。
剧中东门冷对马周说:“俺们浙党,又叫做御党,好不兴旺哩。”又对鵕䴊县令说:“老父母,他是《同心录》《天鉴录》多有名的,贴在御屏上三年,逗漏不死的哩。”马周是唐代人物,而浙党、《同心录》、《天鉴录》等却是作者茅维所在的明朝当代事。

《顾宪成全集》
万历后期顾宪成与高攀龙等讲学无锡东林书院,常讽议时政,裁量人物,被称作东林党。宁波人沈一贯担任首辅后,纠集在京的浙江籍官员,形成反对东林党的“浙党”。
当时反对东林党的还有齐党、楚党、宣党等,但以浙党势力最大,其他各党都依附于它,故东门冷曰“好不兴旺”。天启间,魏忠贤得势后,齐、楚、浙党大都投其门下,形成阉党,残酷镇压东林党人。他们编造黑名单,有所谓“东林七录”:《点将录》《天鉴录》《同志录》《雷平录》《剃稗录》《蝇蚋录》《蝗蝻录》,并兴起党狱。
东门冷所说的《同心录》,清人张鉴以为即《同志录》[71],所列均东林党人。至于《天鉴录》所列之人是东林党、还是非东林党,甚至是魏党,包括姓名与人数,各史料记载多有不同。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以为“崔呈秀作,献逆阉,指东林党”[72],所列名单既有东林党叶向高等二十九人,“又有非东林,为人正直,不附魏党”者三十三人。《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二则著录为“凡一百三人,皆魏忠贤之党也”[73]。大概是书辗转传抄既久,故各本不同[74]。
从《醉新丰》中东门冷将它与《同志录》并举来看,茅维所指《天鉴录》列的应是东林党人或非东林党而不附阉党者。至于茅维姓名是否列入《同心录》《天鉴录》,目前还找不到史料证明,然其侄茅元仪确实列名两书中。
茅元仪《掌记》曰:
逆瑾榜朝堂奸党刘健、谢迁等五十二人,而其中功业理学有王守仁,文章有李梦阳。近日逆贤时,《同心录》所称奸党二百五十八人,《天鉴录》又八十人,不知异日有如二公者否?余曾忝附其中,窃为之惧矣。(茅元仪《掌记》卷三,《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10册,第380页。)

《掌记》
据张鉴《冬青馆集》乙集卷七《书<东林同志录>后》,“茅元仪之名正在赀郞武弁山人之下”。东门冷所言“贴在御屏上三年”亦有出处。
据吴应箕《启祯两朝剥复录》卷八,河南司主事嘉兴沈德先为浙党鹰犬,出死力害人,与湖州韩敬等造《天鉴录》,凡与韩敬辈相厚者俱称为君子,与彼相左之正人俱指为小人,并将此书托人转送给魏忠贤,“逆珰将此录粘于屏”,并据此录名单杀戮削夺海内名贤殆尽。
剧中东门冷进士出身,马周责骂他,“向阉官磕颡”,“昧心肠数黑论黄”,“平白地掀风作浪”,加上其祖先坟冢曾被人掘发,让人联想到茅维被牵涉党籍案、被诬人命和毁冢案。
关于这些案件的过程与细节,茅维《辛未春正待勘羁南卫铺即事书情占得长律十首》小注有详细记载。崇祯改元,朝廷用人,茅维于次年赴京,谋求进用。他先后撰《治安疏》《足兵足饷议》《御虏治标急着》三疏,盛传京城。
崇祯三年(1630)二月,朝廷有用茅维之意,“凶仇闻之,先致参陷”。“凶疏以四月十五上,实出多人锻炼手”,后因四台辅之力,“至三番票拟,不及维名”。茅维当时已拟好辨疏,但被友人张圣标所阻,而张氏阻止茅维上疏,“实劫于凶人恐喝”,以为“一出国门,忌者立解”,结果被追逼得更厉害。
茅维六月离京待勘,“七月杪抵南中,时县借钦犯名,搜捕甚亟”。后被羁押禾中铺两月,“遍求故知,皆阳许,莫为应”。
关于人命和毁冢案,据茅维所言,也是仇家指使人陷害:“俞生孟僴比邻居,日以觞咏从事。予迁葬先慈,在戊辰二月初二,俞求售产于八月廿八。移居之夕,予拉姻友备饯,且赋长歌赠之。俞感甚,详刻公据。至次年,俞受凶饵,遂操戈。诬假命,诬毁冢,不遗余力。”

《皇明论衡》目录
其中“有日夕巧谮愬于明府君者,故称表里,然予两质辨于明府君,未尝不点首韪之,亦无奈萋菲深耳”。茅维感叹患难以来,虽然亦有为他极力昌言持公者,但这些人“皆出远方素交,而桑梓寂无一助”[75]。此后茅维被羁押候勘于南卫铺,并经历了一场春疫,直至崇祯五年才案解还洁溪。
剧中马周写了《安边》《弥盗》二疏,其中《弥盗》一疏提出“弭盗的在守令”,而茅维崇祯七年所作《原盗》也认为弭盗的关键在官吏[76]。
剧中马周得故人执金吾堂上左都督常何推荐,蒙唐太宗“圣恩宣诏”,拜为翰林学士兼兵科给事中,代天子巡边,建了功业,报了朝廷,然后升了仙班。建功立业后退隐是茅维的政治理想,这个理想在他的诗文集中也有反复表述。
茅维通过写唐代马周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醉新丰》杂剧可以说是茅维的一个白日梦。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崇祯二年茅维写了《治安疏》《足兵足饷议》各数万言,请于首辅蒲州韩爌,“韩促上,竟不报闻”。
次年二月,朝廷“册立恩诏”,有意用及茅维,结果“一行恩诏翻胎祸”,引来了党祸,还被诬人命和毁冢。正如郭濬所言,《醉新丰》并非马周之把戏,“乃孝若先生之点点恨墨也”[77]。

《东坡先生诗集注》
另外,茅维所作《羁卫书怀一百韵时三月上巳日》长诗中有“鵔鸃令故贤”一句,这与剧本中塑造的被马周称为“聪明使长”、“合循良”的“鵔鸃令”形象基本一致,他没有因群小环绕而滑向反面。
马周在县堂中责骂东门冷、西门热,侃侃而谈,自视甚高,引得一众大笑,与长诗中“侃侃据案争,县庭满嗢噱”的描写也很呼应。
剧中马周友人执金吾堂上左都督常何,虽然是唐代实有之人,但其“世叨武荫,少中武科,陆沉金吾卫中”的自述,与茅维友人大金吾张圣标经历正同。
且茅维崇祯二年这次出山谋求进用,靠的也是张圣标等友人的上疏推荐,“征聘事,诸公业具荐疏”[78]。也就是说,剧中县令和常何也分别有现实中县令和张圣标的影子。
综上所述,茅维杂剧是有感于时事和自己经历所作,重在表达自己情感志向,特别是《春明祖帐》《云壑寻盟》《醉新丰》《双合欢》四个杂剧,带有明显的自传性和时事性,是自我写照与客观现实的投影。
作者茅维及其友人成为剧中人物,作者隐居的洁溪成为剧中场景;剧中有不少刚发生的政治事件,部分戏剧故事来自作者自身经历,甚至是作者风流情史、人生理想的演绎。
茅维对自己的杂剧创作非常自信,曾以所作杂剧请钱谦益作序,“已而语人曰:‘虞山轻我。近舍汤临川,而远引关汉卿、马东篱,是不欲以我代临川也。’”[79]
从茅维杂剧重在表达思想、才情橫溢、不受杂剧体制束缚等特点来看,其自比汤显祖有一定的道理。曾永义在《明杂剧概论》中,一方面指出茅维杂剧除《闹门神》外,格律、关目与排场“俱不得体法”,另一方面也肯定其杂剧创作才情,认为曲文“能随剧情而或闲谈隽逸、或清丽妩媚、或雄肆朴素”[80]。

《明代杂剧全目》
明中后期以来,随着文人南杂剧创作的兴盛,特别是杂剧创作从舞台演出向案头阅读功能转化,导致作家重个人情绪发泄而轻舞台叙事表演,而茅维正是这类作家的典型代表。
虽然从戏曲舞台演出史看,这是一种退步现象,它对有清一代杂剧创作普遍走向作家个人“写心”的现象有明显影响[81],但茅维杂剧创作才情值得肯定,其杂剧对研究明末清初社会现实和士人心态等也有重要价值。
注释:
*本文为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明代茅坤家族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8AZW016)阶段性成果。
[1] 据茅维《茅洁溪集》所收《凌霞阁新著总引》。按:《茅洁溪集》为茅维崇祯间自刻本,现藏台湾“国家”图书馆,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有缩微胶卷本,本文所引均为该胶卷本。内含《冬馆诗》等十余种作品,有的分卷,有的不分卷,并有一些零散诗文,故本文所引该集诗文有时未能注明卷数。傅惜华认为茅维创作有杂剧三十五个,不知何据,见傅惜华《清代杂剧全目》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页。
[2] 据笔者最近发现的日本内阁文库藏清顺治刊本郭濬《虹暎堂集》卷十八《凌霞阁内外编词评引》等资料,可知茅维在《凌霞阁内外编》之外,还创作有其他杂剧,其创作总量目前可知的已达二十一个,但有剧本留存的仍为八个。
[3] 赵红娟、何等《新发现的明代戏曲家茅维杂剧两种》,《戏曲与俗文学研究》第4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4] 见茅维《茅洁溪集》所收《凌霞阁新著总引》。
[5] 孙书磊《茅维及其凌霞阁杂剧考述》,《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2期。
[6] 茅维《北闱蕡言》二卷仅见于上海图书馆;《十赉堂甲乙集》包括甲集十七卷(以下简称“《甲集》”)、乙集十八卷(以下简称“《乙集》”),万历四十六年(1618)刻本,上海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均藏;《十赉堂丙集》十二卷(以下简称“《丙集》”)已影印收入《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890册;《茅洁溪集》情况则可参见赵红娟《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茅维<茅洁溪集>及其价值》,《中国文学研究》第3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7] 孙文对茅维生平等考述有不少舛误,对此学界已有所补正,参见陈妙丹《茅维的卒年与凌霞阁杂剧的创作时间考》,《中华戏曲》第50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年版;王瑜瑜《晚明戏曲作家茅维生平考辨二题》,《沈阳大学学报》2009年1期。由于对茅维生平研究不到位,导致孙文把《秦廷筑》《苏园翁》等六个杂剧误判为入清后所作,认为“总体上流露出了亡国遗民的情绪”。实际上,据茅维《凌霞阁新著总引》与郭濬《凌霞阁内外编词评引》可知,《秦廷筑》与《苏园翁》完成于崇祯九年。
[8]《茅洁溪集》之《癸酉夏月鸠工建凌霞阁于洁池上将奉龛供大士薰修净业秋中期延净侣数辈惠临落成题诗叙怀得三十韵》。
[9]《茅洁溪集》之《冬馆诗自序》。
[10]《茅洁溪集》之《还山闲适诗》卷一《洁溪山居左偏谋创离垢园规画良备资斧难集姑识一诗为他日劵凡二十二韵》。
[11]《乙集》卷十一《黄晦之为写洁溪图自题四韵》。
[12] 分别见《丙集》卷一、卷十一。
[13]《茅洁溪集》之《还山三体诗叙》。
[14]《茅洁溪集》之《还山酬寄诗》卷三《寄韦叔万万载明府》。
[15] 茅坤《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二十三《亡弟双泉墓志铭》,《茅坤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672页。
[16] 茅元仪《石民四十集》卷三十一《亡姬陶楚生传》,《续修四库全书》138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28-329页。
[17] 茅元仪《石民四十集》卷十一《旌志乘序》,《续修四库全书》1386册,第176页。
[18] 张雨《句曲外史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216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52页。
[19]《茅洁溪集》所收《冬馆吟》之《寄刘半舫少司农张念堂大金吾于燕中》。
[20] 侯恪《侯太史遂园诗集》卷八《晤张圣标圣标以忤珰下狱论死今上位始出之》,《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集部第78册,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474页。
[21] 刘荣嗣《简斋先生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46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419-420页。
[22]《乙集》卷十二《癸卯春得张圣标书问寄酬二十韵》。
[23]《甲集》文部卷十一《答张圣标书》。
[24]《丙集》卷二《申别十章,甲子冬仲北还舟中作·列人张圣标金吾》。
[25]《丙集》卷五《别张圣标歌》。
[26] 按:三若,即三箬,在长兴画溪下流,因箭箬夹岸,其南曰上箬,北曰下箬,合溪而称三箬。
[27]《丙集》卷八《纪梦二律寄友时癸亥季夏八日·一寄列人张圣标》。
[28]《茅洁溪集》之《还山酬寄诗》卷三《寄大金吾督张圣标趣其乞身南礼普陀》。
[29] 颔联自注:“谓庚午夏事。”
[30]《丙集》卷二《列人张圣标大金吾》“予友刘曲周”句自注:“谓刘半舫。”
[31] 刘荣嗣《简斋先生集》诗选卷五《己巳秋偶值孝若于新嘉道中立谈别去孝若以诗见寄赋此报之》,《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46册,第573页。
[32]《茅洁溪集》之《还山酬寄诗》卷三《寄刘半舫大京兆都门》。
[33] 陈鹤《明纪》卷五十四《庄烈纪三》,《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第7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86-87页。
[34] 钱谦益《列朝诗集·丁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56页。
[35] 康基田《河渠纪闻》卷十二,《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辑第29册,第151页。
[36]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十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8册,第863页。
[37] 李雯《蓼斋集》卷二十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93-594页。
[38] 毕自严《度支奏议》福建司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册,第290-296页。
[39]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主婿遭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684页。
[40] 《(雍正)畿辅通志》卷五十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05册,第210页。
[41] 谈迁《北游录》,《续修四库全书》第737册,第234页。
[42]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京师园亭》,第511-512页。
[43] 嵇璜《续文献通考》卷二百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30册,第772页。
[44] 钱保塘《历代名人生卒录》卷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646页。
[45] 参见《茅洁溪集》之《还山感遇诗》卷一《辛未春正待勘羁南卫铺即事书情占得长律十首》《羁卫书怀一百韵时三月上巳日》两诗及自注。
[46] 石文器《翠筠亭集》卷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83册,第641页。
[47] 谈迁《国榷》卷九十七,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5892页。
[48] 沈德符《清权堂集》卷十六《寿博平君侯郭卫民社兄六十初度时以左柱太师奉朝请》,《续修四库全书》第1377册,第198页。
[49] 冯梦龙《甲申纪事》卷二《绅志略》把博平侯郭振明列入“死难诸臣”中,误。
[50] 钱士馨《甲申传信录》卷四,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版,第59页。
[51] 傅维鳞《明书》卷一百五十三,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3035页。
[52]《茅洁溪集》所收《春明祖帐》茅维眉批。
[53] 陈鹤《明纪》卷五十一,《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第7册,第39页。
[54] 李逊之《三朝野纪》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438册,第70页。
[55]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十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8册,第252页。
[56] 按:《春明祖帐》创作于刘荣嗣去世后,而刘氏卒于崇祯十一年。
[57] 孙承宗《高阳集》卷十一《王鉴心都尉疏草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64册,第203页。
[58] 茅元仪《石民四十集》卷九十《寄王鉴心都尉书》,《续修四库全书》第138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7-88页。
[59] 茅元仪《石民四十集》卷八十九《报薛中玄阳武书》,《续修四库全书》第1387册,第82页。
[60] 谈迁《国榷》卷九十五,第5758页。
[61] 此处以春秋时美女夏姬最终归巫臣来代指徐碧玉归了自己。夏征舒代指其母夏姬。
[62] 见《甲集》诗部卷三。
[63]《乙集》卷八《德州附书均卿并示此诗》:“藉尔持家秉,邮程得暂纡。”
[64]《甲集》文部卷五《亡仆均卿墓志铭》。
[65]《丙集》卷六《归来望思曲九阕悲逝作》其八“悲均卿”。
[66]《甲集》文部卷六。
[67]《乙集》卷十六《客邸吟新诗讫感忆亡者碧玉均卿并赋二绝以寄余痛》其二。
[68]《甲集》文部卷五《亡仆均卿墓志铭》。
[69] 剧中提到东门冷与西门热是亲家;西门热官中书舍人,其子也挣了个世袭纱帽;前任省按台与西门热是通家,赐了他家一块“世掌丝纶”的金字牌匾,这些可能也有所本。
[70]《茅洁溪集》之《还山闲适诗》卷二。
[71] 张鉴《冬青馆集》乙集卷七《书〈东林同志录〉后》(《续修四库全书》第1492册,第167页)引茅元仪《掌记》“近日逆贤时《同心录》所称奸党二百五十八人”后,加按语曰:“同心”当即“同志”之异。按:从茅维《醉新丰》和茅元仪《掌记》均称“同心录”来看,当时应该确有《同心录》一书。
[72]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440册,第36页。
[73]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60页。
[74]参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六《天鉴录一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67-372页。
[75] 以上均见于《茅洁溪集》之《还山感遇诗》卷一《辛未春正待勘羁南卫铺即事书情占得长律十首》小注。
[76] 茅维《原盗》收入《茅洁溪集》之《迂谈》。
[77] 郭濬《虹暎堂集》卷十八《凌霞阁内外编词评引》,日本内阁文库藏清顺治刊本。
[78]《茅洁溪集》之《还山感遇诗》卷一《辛未春正待勘羁南卫铺即事书情占得长律十首》其四小注。
[79]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36页。
[80] 曾永义《明杂剧概论》,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488页。
[81] 关于茅维杂剧创作成就的评价,得到匿名评审专家的指导,谨致谢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