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元年五月,于前线军营之中,福康安溘然长逝。当此噩耗奏报传至京师,太上皇乾隆闻之,哀伤至极。旋即降旨,追封福康安为嘉勇郡王,并特允其配享太庙,以彰其勋绩。

自康熙一朝成功戡定三藩之乱后,清王朝于律法层面明确颁行规定,严格限制异姓受封王爵(虽偶有死后追封之特例),尤其着重禁止异姓获实封王爵。此规定在后续历史进程中得到切实贯彻。自康熙时期以降,直至清王朝覆灭,漫长岁月里,于异姓之中,仅福康安一人获实封王爵之殊荣。
乾隆帝对福康安的赏识与偏爱情真意切,其缘由虽不乏因对相关人物的眷顾而推及福康安这一因素,但关键在于福康安自身具备卓越才能。自乾隆中期以降,每逢国家面临重大战事,福康安常膺主帅之任,肩负起统领军务的重任。
乾隆六十年,福康安成功戡定苗疆起义,功勋卓著。因这一功绩,其爵位由一等嘉勇公晋封为贝子。彼时,乾隆皇帝于谕旨中言明,原本意将王爵赐予福康安,然囿于祖宗成法,最终仅能封其为贝子。
在封建爵位体系中,异姓贵族所能获封的最高爵位为一等公。而福康安竟能得宗室贝子之爵,此乃圣上隆恩彰显。从历史惯例及爵封规制综合考量,倘若福康安未于军中溘然长逝,以常规情形推断,其获封王爵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尽管福康安获封郡王爵位,然其并非爱新觉罗氏后裔,故而在待遇层面,相较于宗室郡王,仍存在差距。由此引发思考,福康安所封郡王与宗室郡王,二者究竟在哪些方面呈现出差异?
【其一、不享受系黄带的待遇】
在清代皇室体系中,皇族成员被明确划分为宗室与觉罗两大类别。其中,宗室的地位相较于觉罗更为尊崇。为清晰彰显皇族不同阶层的身份差异,清廷制定了严格的标识制度:宗室成员被特许系黄色腰带,而觉罗成员仅能系红色腰带。
黄带与红带,在封建政治体系中,具有鲜明的身份标识意义,象征着特定的政治地位,为封建等级制度的重要表征。于彼时森严的规制之下,文武官员乃至普通军民,均严禁逾越此身份界限。在封建统治的恩赏体系里,皇帝偶会为彰显对臣属的格外恩宠,而赐予黄带。以乾隆一朝为例,权臣和珅便曾蒙圣上恩赐,获系黄带之殊荣。这一举措,不仅是对臣子个人功绩与皇帝宠信的直观体现,亦反映出封建王朝权力运作与恩赏机制的独特面貌。
然而,皇帝赐予大臣的这一崇高殊荣,通常仅具象征意义。若无特别旨意,大臣在日常情况下,依旧不得私自佩戴使用。
雍正朝时,张廷玉承蒙圣恩,获赐红绒结顶冠。此冠依制,唯皇帝与皇子方有资格佩戴。鉴于此特殊情形,雍正帝特颁谕令,特许张廷玉于每年元旦朝贺之际,得以佩戴此冠一次,其余时段,该冠仅可恭置于家中妥善供奉。

经详考各类相关文献,并未寻得福康安辞世后,其子德麟享有佩用皇帝专属之物特权的记载。此情形有力地表明,在封建王朝的政治架构中,宗室成员与异姓臣属之间,长期横亘着一道难以逾越的森严界限。
【其二、不享受王府和其他的配套设施】
在清代,皇子一旦成年,皇帝会依据其获封爵位的高低,赐予相应府邸。与此同时,为保障王府经济来源,还会酌情赐予一定数量的庄园、当铺等产业。
郡王,作为宗室成员所获的高级爵位,依朝廷定制,可获朝廷拨予的护军、领催及马甲名额总计150个。然而,这些名额所对应的钱粮,实则为皇帝额外赏赐,相关人员无需实际履职到岗。与此同时,郡王按常规配备的护卫人数为15人。
在福康安获封贝子这一历史节点,乾隆帝虽确为其提升了与之匹配的待遇。然而,从护卫配置标准而言,并未达至宗室贝子所享有的十人护卫规格。而是以赐予两杆豹尾枪的方式,旨在彰显其身份地位,提升福康安在朝廷中的身价。
福康安府邸之营建,遵循一等公规制。其薨逝后,子德麟依例降等承袭爵位。虽德麟所得为贝勒之衔,然嘉庆帝并未特赐贝勒府予之。

【其三、家谱不列入玉牒,死后不予谥】
自诞生之日起,皇族成员即需向宗人府进行报备登记,随之享有与之匹配的政治权益及经济待遇。在皇室谱系记载方面,其专属家谱被称作“玉牒”。该玉牒每十年会开展一次重修工作,且在编纂过程中,宗室与觉罗二者的记录是相互区分开来的。
在玉牒这一用以详实记录宗室成员信息的重要文档体系中,仅针对爱新觉罗氏家族成员展开记载。福康安并非此家族成员,故而无法享有于玉牒中被记录的待遇。太上皇于追封福康安的谕旨里明确提及,是以宗室之例赐予其郡王爵位。然而,即便如此,“按宗室例”这一表述,实际上已然彰显出异姓与宗室之间的本质差异。
在封建王朝的礼仪规制中,对于宗室郡王薨逝后谥号的赐予,朝廷有着明确且细致的规定:亲王谥号为单字,郡王谥号则为双字。且无论亲王或郡王,其谥号皆依据特定的道德准则拟定,如“贤”“勤”“忠”等字词,皆为体现道德评判的典型用字。然而,福康安辞世后,乾隆皇帝依照异姓大臣的标准,赐予其“文襄”之谥号。由此可见,这一谥号赐予标准与宗室郡王所遵循的规则,存在显著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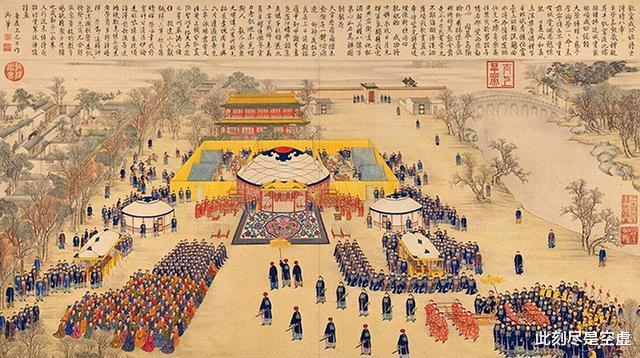
上述内容阐述了福康安与宗室郡王间存在的若干差异,然而,二者是否亦有相同之处?答案是肯定的,其相似点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层面:
其一,享有获取等额俸禄的权益。依据清代宗室俸禄制度规范,郡王每年可获俸禄银五千两以及禄米五千斛。然而,福康安系卒后追封郡王,故而终其一生,未曾实际领取过一日的郡王俸禄。
据史料记载,福康安在世时,获封贝子爵位。彼时,其俸禄依贝子规制发放,年俸为白银1300两,禄米1300斛。相较先前获封的一等嘉勇公,此待遇提升颇为显著。
嘉庆元年,福康安之子德麟承袭贝勒爵位。旋即,太上皇乾隆郑重告诫嘉庆帝,对于德麟的俸禄支给,当依循宗室贝勒的既定标准执行。

其二,爵位承袭模式维持原状。福康安辞世后,德麟依据降级承袭之准则获封贝勒爵位。然而,乾隆皇帝龙御上宾之后,嘉庆帝对福康安展开了一定程度的清查与整饬。嘉庆帝判定福康安在统率军旅期间,生活奢靡铺张,且存在虚报冒领军饷之行为。
嘉庆帝对福康安向来持有特定见解,然乾隆帝在位之际,其碍于形势,未敢表露。待亲政之后,嘉庆帝便将报复之意,落诸福康安之子德麟身上。嘉庆十三年,德麟因于朝会时未能依时赴班,触犯朝规,被降爵为贝子。
在嘉庆帝统治的整个时期,德麟处境颇为困厄,屡遭惩处。自嘉庆二十四年起,相关史料对其记载便近乎绝迹。
德麟辞世后,依例应由其子庆敏承袭爵位。按常规,庆敏所承之爵当为镇国公。然而,嘉庆帝鉴于德麟乃因获罪自贝勒降为贝子这一事实,故而最终裁定庆敏袭封贝子。

自庆敏之后,福康安家族所承爵位恒定为镇国公,此情形与清代宗室郡王承袭规制相符。盖清代典章制度明确,亲王、郡王之爵位递降至镇国公或辅国公级别后,即进入世袭罔替之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