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称街道为马路,南京最早的一条由中山码头通向南京城的路就叫“大马路”,因为那时候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马车。等到烧汽油的动力车辆进入城市,城市交通才发生了变化。
民国时期,南京的黄包车超过万辆,以此为生的车夫以及家属有五六万人,占当时南京人口的十分之一。
除去一部分自备人力车外,大多每日两人合租一辆,分上下午两班拉驶,南京以拉车为业的人口估计在15000以上,其中以20岁至40余岁者占多。

1924年,陈白尘还只是个16岁的学生,在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读书,因患淋巴腺结核症,医生建议他外出游玩,以宽胸怀。陈白尘因此得以游历南京的名胜古迹,最远的一处便是南京城东北角的燕子矶。
当时的南京交通不发达,尚无汽车通达燕子矶,只有人力车可坐。坐着这种完全靠体力拉的车子,一路颠簸,少年陈白尘来到了他向往已久的燕子矶。登临燕子矶俯瞰长江,矶石下滚滚江水东流去,有惊涛拍岸的气概;江风拂衣,又有飘然欲飞的感觉。
许多爱国志士、痴男怨女都选择这一胜地投江了。陶行知为此书写“想想死不得”的牌匾立在燕子矶上,告诫人们珍惜生命。
拉车的人力车夫误以为陈白尘游燕子矶是要自杀,放心不下,竟然跟踪他半天,少不得一番劝说。当误会消释后,两人有了情感沟通,聊起了家常,这对一个身在异乡,举目无亲,又身染疾病的少年来说,那一瞬间得到的温情,是多么的珍贵。
人力车夫竟成了一位16岁少年的好朋友。南京冬天的气候是阴冷的,但一想到南京认识的第一位朋友,陈白尘身上总感到有些温暖。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进攻上海闸的那个夜晚,巴金乘坐由上海开往南京的火车,抵达南京。31日早晨,天落着微雨,巴金刚起床,一个朋友打来电话,巴金立即坐上黄包车去位于北极阁下的中央研究院。
他坐在黄包车上看到南京的景象,耳边只有炮声,传闻日本飞机要轰炸北极阁军用无线电台,很多人一夜没睡,第二天就准备去乡下避难。
在鼓楼一家旅馆,巴金拜访了两个从汉口来的朋友,他们本来要去上海,因为战事,滞留南京。
因为还有事情要办,巴金又让车夫拉着,由城北到城南,到了夜幕降临时,车夫迷路了。巴金焦急地坐在车上,车夫向同行打听路怎么走。
前夜下关的日本军舰向鼓楼方向开炮,沿途运行李往南走的黄包车和汽车接连不断,排成了一条长线,简直没有尽头。
车夫慢慢地走,花了很长时间,终于把巴金送到老下关火车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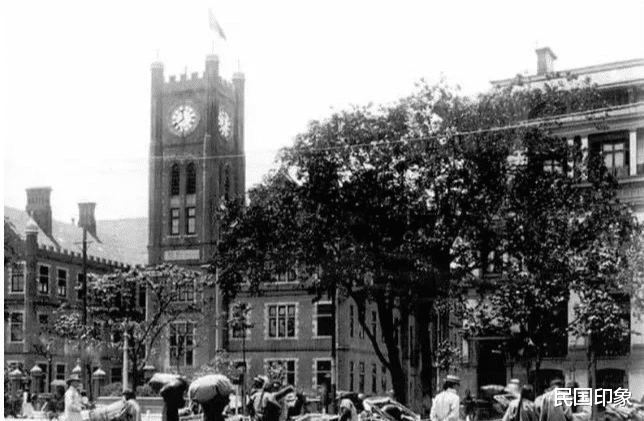
南京的人力车分城南车、城北车两种,入夜由下关进城,雇城南车;或由城南至下关,雇城北车。
城南、城北车的识别方法很简单:凡夜间鼓楼附近及以南各马路上的人力车,以车头向南,迎往北之客者,皆城北车。
反之,凡仪凤门以外,以车头向北,迎南来之客人,皆城南车。
人力车价格低廉,自下关车站至大行宫4角、至状元境5角;下关至丁家桥3角、至成贤街5角、至鼓楼北2角、至玄武湖5角、至燕子矶1元、至幕府山1元、至牛首山1元2角。

民国时期,有文人学者倡导人道主义,出行坚持不坐人力车,他们坐汽车或者步行。
曾经担任过安徽大学校长的刘文典,常在课堂上怒斥人力车的不平等,但是说归说,骂归骂,课后,他依然登上人力车扬长而去,所谓人力车的不平等,是别人的不平等,与他无关。

从事教育工作的陶行知,倡导“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
平时陶行知不坐人力车,有一次因急事坐了人力车,半道上非要和车夫对换角色,陶行知拉着人力车,车夫生平都是拉别人,如今第一次被别人拉,满含热泪地坐了半程的车。
陶行知则累得满头大汗,这拼体力的拉车活,比站在讲台讲课更为吃力,劳动者的苦如果不是切身感受,真的不了解。
这大概也是陶行知建设晓庄学校,普及平民教育的初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