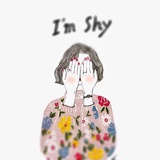1949年1月10日,被解放军铁桶般围困在河南永城东北、安徽萧县西北这片后来被称为“萧永地区”的杜聿明集团,在一场惊天动地的围歼战后,彻底宣告覆灭。
曾经显赫一时的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这位黄埔一期毕业、深受老蒋器重的名将,最终没能逃脱兵败被俘的命运。与他一同陷入绝境的几位兵团司令,结局也各不相同:以“猛”著称的第2兵团司令邱清泉,落了个战死沙场的下场;第13兵团司令李弥,倒是机灵,关键时刻丢下部队,化了个妆,靠着两条腿愣是只身溜了出去。

而要说最“幸运”的,恐怕非第16兵团司令孙元良莫属了。这位同样是黄埔一期出身的将领,不仅在最后关头带着一部分人马冲出了解放军的包围圈,更让人啧啧称奇的是,打了这么个前所未有的大败仗,损兵折将,他回到南京后,居然没挨老蒋的一句重话,甚至连个处分都没有。
晚年,孙元良在谈及淮海战役时,曾盛赞上司杜聿明,说:“光亭兄不愧为一诚实军人。”
时间回到1948年12月5日,老蒋命令杜聿明向濉溪口方向行动,以邱清泉的第2兵团向南面攻击前 进,李弥的第13兵团和孙元良的第16兵团在两翼跟进,负责掩护。
命令是下了,可仗打起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邱清泉的部队虽然装备精良,号称“王牌”,但在解放军层层阻击下,攻击就像一头扎进了泥潭,进展慢得像蜗牛爬。两天下来,也就往前挪了那么几里地,勉强前进到青龙集西边的陈官庄一带。

负责掩护侧翼的李弥和孙元良兵团,情况更糟。解放军抓住他们兵力分散、战线过长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到处开花,这边敲一下,那边打一棍子。很快,两个兵团的阵地就跟筛子似的,被突破了好几处。告急的电话、电报雪片般飞向杜聿明的指挥部。
到了12月6日这天,杜聿明不得不把自己的指挥部从相对靠前的位置,挪到了一个叫李石林的小村子。屁股还没坐热,邱清泉和孙元良就仓惶地找上门来了。看他俩那灰头土脸、眼神慌乱的样子,就知道情况有多紧急。
“光亭兄!”邱清泉嗓门大,性子急,一进门就嚷嚷开了,“这么打下去不行啊!弟兄们死伤太惨重了,根本冲不动!南边共军的工事一层又一层,火力猛得很!”

孙元良也赶紧附和,他向来以“会算计”著称,眼看苗头不对,自然心急如焚:“是啊,杜主任,我们两翼的掩护阵地也快顶不住了,好几个口子被共军钻进来了。再这么硬耗下去,怕是前途不妙啊!”
三人脸色都不好看。杜聿明皱着眉头,沉默了好一阵儿。他何尝不知道眼前的困境?只是老蒋的命令像紧箍咒一样套在头上。最后,他叹了口气:“走,去炳仁(李弥字炳仁)那里,咱们四个碰碰头,好好议一议。”
于是,三位高级将领,顶着刺骨的寒风,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到了不远处的李弥兵团司令部。李弥已经在屋里等着了,屋里生着个小火盆,但气氛却比外面的天气还要冰冷。

人一到齐,孙元良首先发表意见说:“杜主任,依我看,现在攻击是肯定不行了,掩护也快垮了。再打下去,咱们这几十万人,怕是都要交代在这儿。俗话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眼下这情况,只有当机立断,下令突围,或许还能杀出一条血路,保住一部分元气。再犹豫,可就真晚了!”
邱清泉听了,虽然没说话,但连连点头,显然是赞同这个意见。
李弥还是那副样子,低着头,慢悠悠地抽着烟,眼神飘忽,看不出是赞成还是反对。他这人,心思深沉,轻易不表态。
杜聿明听完孙元良的话,声音沙哑地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话,要是三天前,咱们刚就拿出来说,下决心突围,说不定真能把大军囫囵个儿地带出去,也算对得起老头子了。可是今天再说这话,怕是晚了点啊!”

接着,杜聿明顿了顿,语气更加沉重:“你们看看四周,共军的包围圈是越来越紧,铁桶一样。现在想突围,谈何容易?就算能侥幸杀出一条血路,那也是伤筋动骨,重武器、辎重车辆还能保住多少?万一冲不出去,部队被打散了,各自逃命,那不成溃败了吗?到时候,既违抗了命令,又没能保全主力,我们还有什么脸回去见老头子?”
杜聿明的话,让邱清泉和孙元良的脸上都露出了尴尬的神色。他们当然知道杜聿明说的是实情,突围的风险极大。但眼下的僵局更让他们绝望,相比之下,突围似乎成了唯一的“活路”,哪怕是希望渺茫的活路。
“杜主任,话虽如此,可总得试试啊!”邱清泉还是忍不住说道,“困在这里是等死,突围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孙元良也跟着帮腔:“是啊,杜主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先冲出去再说!”
李弥依旧沉默,只是默默地掐灭了烟头。

看着邱、孙二人急切的样子,再看看李弥那不置可否的态度,杜聿明心里也是七上八下,一点底都没有。他深知,无论打还是跑,这责任最终都得他来扛。犹豫再三,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他终于像是下定了决心,沉声说道:“好吧,既然大家都觉得突围或许还有机会,那我就下这个决心。不过,丑话说在前面,突围不是逃跑,各兵团要仔细侦察好各自的突破方向和路线,尽量找敌人防御薄弱的地方下手。还有,重武器和车辆,非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丢,那些实在带不走的笨重物资,可以提前销毁。行动时间,就定在今晚!”
杜聿明看了看表,说:“散会吧,各回各部,抓紧时间准备!”
李弥:犹豫不决,缓兵之计
李弥慢吞吞地走回自己的兵团司令部,脸上的表情比刚才在会上还要阴沉几分。他召集起手下的几个军长、师长,屋子里挤得满满当当,烟雾缭绕,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杜主任的意思是今晚突围,我们兵团负责向东,黄昏时分开始行动,目标是先到阜阳集合。”
话音刚落,底下就嗡嗡地议论开了。一个师长首先忍不住站了起来,他是刚从前线下来的,军大衣上还沾着泥土和血渍:“司令,这也太仓促了吧!弟兄们现在都顶在一线,跟共军搅在一起,枪炮声就没停过。别说组织突围了,就是想从阵地上撤下来,重新集结,都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办到的事儿。敌人盯得那么紧,我们一动,他们肯定立刻就扑上来了。”
“是啊,司令!”另一个军长也接话,“现在天都快黑了,部队散得到处都是,命令怎么传达下去?怎么组织?搞不好突围不成,反而先乱了阵脚,那不更糟?”
“而且,往东边突围?”又有人提出疑问,“东边是山区,路不好走,共军在那边的兵力也不弱。我们对地形又不熟,万一钻进去出不来……”

将领们七嘴八舌,抱怨的,担忧的,质疑的,几乎没有一个对这个仓促的突围计划抱有信心。他们都是带兵打仗的老油条,知道这种情况下强行突围意味着什么,丢掉所有重装备不说,部队能不能成建制地冲出去都是个未知数。
李弥听着部下们的议论,心里本来就没多少底的突围决心,更是动摇得厉害。他本来就对杜聿明这个决定持保留态度,现在手下人又个个畏难,他索性做了个这样的决定。
李弥说:“要不,我们先看看情况,邱清泉、孙元良不是也要突围吗?他们一个向南,一个向西,让他们先动起来。我们再看看,争取到明天,也就是7号拂晓,再做定夺。大家看怎么样?”
这个提议,无疑正中下怀,将领们纷纷点头称是。就这样,李弥兵团的突围计划,在司令官的默许和部下的“反对”下,被悄无声息地推迟了。

邱清泉:猛将咆哮,临阵变卦
相比李弥这边的“拖字诀”,邱清泉那边则是另一番景象。他风风火火地回到第2兵团司令部,立刻召集手下的军长们开会。
邱清泉是出了名的“猛将”,治军严厉,性格暴躁,打起仗来不要命。但此刻,这位“邱疯子”的脸上却也写满了凝重。他把杜聿明的决定一说,底下同样一片哗然。
“突围?现在?”
“往南边打?那不是更硬的骨头吗?”
“要抛弃重武器?那我们第2兵团还叫什么王牌?”

将领们的情绪普遍低落消沉。第2兵团是蒋军的嫡系精锐,装备精良,尤其是重炮和坦克,是他们引以为傲的资本。现在要突围,就意味着这些“宝贝疙瘩”很可能都要丢掉,这让他们从心底里无法接受。没了重武器,第2兵团就等于被拔了牙的老虎,就算侥幸逃出去,也元气大伤,颜面尽失。
就在这时,会议室的门被猛地推开,一个人影闯了进来,带着一身的寒气和怒火,来人是第74军军长邱维达。
邱维达来晚了一步,刚听明白是要突围逃跑,顿时火冒三丈,也不管什么上下级了,指着在座的一干同僚就咆哮起来:“突围?你们就知道突围,怕死是不是?想丢下家伙逃跑,那是打仗的办法吗?为什么不集中我们全兵团的力量,选准一个点,狠狠地打出去,非要搞什么分头突围。共军正好把我们各个击破,你们考虑过这个后果没有?”
邱维达越说越激动,最后猛地一拍桌子,吼道:“我们74军包打第一线,谁要跑谁跑,我们不跑!”

这一通石破天惊的咆哮,把整个会议室都震懵了。原本还在小声议论的将领们,一个个都噤若寒蝉,不敢再言语,邱清泉也被邱维达这番话给镇住了。
邱维达的话虽然冲动,但并非全无道理。更重要的是,他点中了邱清泉的死穴——面子和部队的完整性。邱清泉自视甚高,把第2兵团的荣誉看得比命还重。如果真像丧家之犬一样,丢盔弃甲地逃出去,他邱清泉还有何面目立足?邱维达那句“包打第一线”,反而激起了邱清泉心底那股悍劲儿。
反复权衡之下,邱清泉那刚刚被形势逼出来的突围念头,又被压了下去。他挥了挥手,示意会议暂停,然后匆匆起身,又去找杜聿明商量去了。他要告诉杜聿明,突围这事儿,得再缓缓,再议议。

孙元良:当机立断,抢跑先行
就在李弥犹豫、邱清泉变卦的时候,第16兵团司令孙元良,却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从李弥的司令部开完会回来,孙元良二话不说,立刻召集自己兵团的军、师长开会部署。
孙元良扫视着部下,开门见山地说:“指挥部的决定是突围,邱兵团向南,李兵团向东,我们第16兵团,向西突围。”
他走到地图前,指点着:“行动就在今晚,不要等,我们集结的地点,第一步,到商丘南边的朱集;第二步,到信阳;最终目标,武汉会合,都听明白了吗?”

部署简洁明了,没有任何拖泥带水。交代完任务,孙元良根本没给手下人太多议论和质疑的机会,立刻带着自己的参谋人员,赶到了驻扎在黄庄的第47军125师。
这个125师,原本是作为快速纵队编成的,配备了不少战车,机动性和战斗力在整个16兵团里算是比较强的。孙元良选择跟在这个师一起行动,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要跑,就得跟着跑得最快的。
于是乎,一个极其诡异的局面形成了:原本是三个兵团司令在最高指挥官杜聿明主持下,共同商定好的突围计划,结果转眼之间,李弥决定“再看看”,邱清泉觉得“得缓缓”,只有孙元良毫不犹豫地带着自己的第16兵团,准备抢先开跑了。

夜幕下的混乱突围
当天晚上八点左右,也就是12月6日的夜里,正当李弥和邱清泉还在犹豫观望,甚至可能已经决定暂缓行动的时候,孙元良的第16兵团,在没有得到任何友邻协同的情况下,独自开始了向西方向的突围行动。
在遭受到重大损失后,第16兵团虽然有一小部分人马(包括孙元良本人)侥幸钻出了解放军包围圈,但整个兵团作为一个建制,基本上算是被打垮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孙元良“单独突围”的情况?是杜聿明改变主意后,没来得及通知孙元良吗?还是通知了,孙元良没收到?或者,是他收到了,却故意置之不理呢?关于这一点,后来的说法五花八门。

很多当时被俘的第16兵团官兵回忆说,在他们开始突围后不久,确实听说杜聿明改变了计划,决定不突围了,并且试图通过电话和电报通知孙元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第16兵团司令部的电话线怎么也打不通。
也有人说,是孙元良自己下令,把兵团司令部的电话线全部掐断了。不仅如此,他还命令译电员,凡是徐州“剿总”(也就是杜聿明指挥部)发来的电报,一律不准接收,不准翻译,就当没收到。
更有甚者,还说孙元良当时曾对他身边的人嘀咕:“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停下来就是等死,老子才不回去!” 然后就义无反顾地带头冲了出去。按照这种说法,孙元良是铁了心要“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独自逃生了。

对于这些五花八门的说法,孙元良本人晚年是断然否认的,他是这样解释的:“有人说我故意切断电话线,这简直是无稽之谈。你想想看,那天晚上突围的时候,兵荒马乱,人喊马嘶,车辆堵塞,大家都在拼命往前冲,躲避敌人的炮火。我身边的兵团参谋长张益熙,就在冲锋的时候腹部中弹,当场阵亡了。那种人踩人、车撞车,炮弹就在身边爆炸的情况下,谁还能保证通讯线路一定畅通无阻?电话线被炸断、被车辆压断,难道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孙元良的话听起来似乎也有道理。战场通讯中断,确实是常有的事。
那么,历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是孙元良故意“失联”,还是真的因为战场混乱而通讯中断?或许,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最清楚。

不管孙元良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单独突围”了,他最终是逃出来了。在他历经艰险,九死一生逃回南京之前,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已经先一步,通过电报向南京的老蒋汇报了十二月六日晚上的情况。
出人意料的是,杜聿明在电报里,并没有把责任一股脑地推给孙元良。他如实汇报说,第16兵团的突围行动,是事先经过他批准,奉了他的命令而进行的。至于后来他和邱清泉决定暂缓突围,那是在第16兵团已经开始行动之后才商定的,当时情况紧急混乱,确实没能及时通知到孙元良,也已经没办法再联系上他了。
这份电报,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保了孙元良一命。

当孙元良灰头土脸地回到南京,准备接受老蒋的雷霆之怒,甚至可能是军法审判时,得到的结果却让他很意外:老蒋不仅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并且很快重新任命他为第16兵团司令,让他立刻去四川,负责在后方重新招兵买马,重建第16兵团。
这背后,杜聿明的那份“实话实说”的电报,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
晚年,孙元良在谈及淮海战役时,是这么说的:“光亭兄不愧为一诚实的军人,他对总统讲的都是实话,是他发电报给总统,说我第16兵团是遵照他的命令行动的。你想想看,要是杜主任像有些奸猾的小人那样,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别人头上,一口咬定是我不听命令擅自突围,那我孙元良肯定是要被送上军事法庭的,脑袋能不能保住都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