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99年6月13日,彭云在哥哥彭炳忠陪同下,带着妻子易小治远涉重洋,回到了十年多年的故乡自贡。
在自贡,彭云一行人收到当地领导的亲自接待。市委常委副书记钟历国对彭云说:“盐都的父老乡亲一直想念着你们,关心着你们。你们的母亲是全国人民爱戴和崇敬的英雄,自贡人们都为有这样一个革命英雄感到骄傲和光荣。”
彭云表示:“自贡是我母亲的故乡,也是我的故乡,我多年来都想回来看看,但一直没有机会。我是搞教育的,愿意将家乡建设好。”
彭云和自贡人民心中心心念念的英雄,便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江姐。身为江姐独子,彭云为什么一直没有回来看看母亲呢?

1946年4月,一个婴儿在成都呱呱坠地,父母将他们刚出世的儿子取名为彭云。他有一个好爸爸彭咏梧,他有一个好妈妈,便是江竹筠。
当时的江竹筠临时住在一个姓丁的同学家中,生下儿子满月后便依依不舍离开彭云回学校上课去了。
江姐同学的妈妈丁婆婆格外喜欢小彭云,为她准备了小被盖、小衣服,细心喂养他。小彭云啼哭不止,丁婆婆便抱着他走来走去。
江姐每次来看儿子,都会说:“不能这么惯着他,如此下去,会养成他好逸恶劳的坏习惯。”
彭云又啼哭不止,疼爱他的丁婆婆急忙给他喂糖水。江姐每次看到都说:“不能这么将就她,这样下去会养成他好吃懒做的坏习惯。”
彭云刚出生两三个月,已经受到母亲的严格教育。

几个月后,江竹筠夫妇接回儿子,他们一家人住在重庆大梁子。由于夫妇俩平时还有诸多工作,便让一个称为“四婆”的亲戚帮忙带彭云。
四婆在和他们一家人相处过程中发现,江竹筠和彭咏梧虽然非常疼爱孩子,但从来不娇生惯养,按时喂他吃饭,也从来不给孩子吃零食。
在给彭云的穿着上,都是温暖舒适,从来不奢华,他们更是格外节俭。就这样,他们一家人过了一年多的幸福生活。
1947年,由刘伯承和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掀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
江竹筠意识到自己也要大胆出击,在国统区开辟第二个解放战场,迎接革命高超的到来,她选派了一些考验的通知前往川东各农村,加强地下党组织。
与此同时,江姐也下定决心和丈夫一同前往川东搞武装斗争。因此,她必须将自己出生不满两岁的儿子彭云托付他人。

既然要将儿子托付给别人,这个人必然是江竹筠非常信任的人。最终,她决定将儿子托付给丈夫彭咏梧的原配妻子谭政烈。
江竹筠夫妇带着彭云一同前往大公报社和谭政姴的弟弟谭竹安商议托孤之事,谭竹安当时在大公报社资料室工作。
当时的他还是个单身青年,住在报社的集体宿舍。见到江姐一家人来了还有些惊讶,急忙前去招呼。
自从去年 11 月邂逅姐夫彭咏梧,又与江竹筠建立了工作联系后,内心里为亲姐姐感到惋惜和难过。
但江竹筠的风范和直率真诚的解释,早已使他理解了彭咏梧和江竹筠的特殊婚姻,不再怨恨姐夫彭咏梧了,反倒与江竹筠建立起了亲姐弟一般的深情。

落座之后,彭咏梧这做姐夫的还显得有些尴尬矜持,抱着小彭云的江竹筠倒落落大方,直率地先开口向谭竹安说明了来意:
“竹安弟,我和你姐夫可能很快就要离开重庆,到很远的地方去工作,可云儿托付给谁却让我们一时作难了。我们想让一些朋友帮助带,可那样又不是长久之计;想到了竹安弟你,可你是个单身汉,也不方便……”
江竹筠说到这里,朝彭咏梧看了看。彭咏梧明白,按他和竹筠来前的商量,请幺姐来重庆自然由他开口最好,既显得尊重原配妻子幺姐,又让竹安这个弟弟的感到是情理之中。
彭咏梧便接过话头说:“竹安,我们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你姐姐最合适、最放心。你看能不能请你姐姐来重庆?这样炳忠可以在重庆读书,同时也可以照顾云儿……”
江竹筠也补充说:“竹安弟,我和你姐夫一直都对幺姐心存内疚,也一直觉得幺姐是个最善良、最通情达理、最深明大义的人,我总感觉这样虽然对幺姐是个委屈,但她要是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革命就会接些这个主意的,况且我们终究是一家啊!”
顿了顿,江竹筠又说:“直说吧,竹安弟,不瞒你,这个主意是我先提出的。我们这一走,还真不知道能不能再回来。依你看,幺姐能不能来呢。”

听姐夫彭咏梧和竹筠姐这么一说,谭竹安愣了一下,接着心里好一阵翻腾,既感意外又觉酸楚。
只是咏梧哥和竹筠姐都还不知道,做弟弟的自己至今还一直瞒着幺姐有关这里的一切,一直没有告诉姐姐咏梧哥的下落。
他一直不忍心让幺姐痛苦呀!想想幺姐在云阳老家苦苦煎熬着,整整6年一直在苦守苦盼着姐夫的下落。
若是告诉幺姐这一切,还提出叫她来重庆抚带姐夫和另一个女人的孩子,幺姐会怎么想呢……
谭竹安神情黯然地想了好一会儿,最后才对翘首等待着答复的彭咏梧和江竹筠肯定地说:
"幺姐的确是个深明大义的人。邦哥,你离家时,她就已懂得了革命道理,能顾全大局,不计个人恩怨。我相信她会来重庆的。这事儿就由我来办吧,云儿就先留给我,你们放心地走吧!”

彭咏梧和江竹筠都轻吁一口气,为竹安的话好一阵感动。江竹筠摸了摸啥事不知、睁大双眼到处看的小彭云的头,对竹安说:
“竹安弟,听你这么一说,我们就放心了。只是云儿留给你,肯定不方便。我看还是把云儿托付给的别人的朋友先带带,等幺姐来重庆了,你再接过来,可以吗?”
谭竹安不放心地问打算先托付给谁,江竹筠说“暂时考虑的是你也认识的王珍如,只是还没有与她商量。等事情商量妥当了,就通知你……”
从谭竹安那里回到家,江竹筠立即给王珍如写了封急信,请她进城来有要事商量。这时,王珍如已经不在上海银行李其猷经理家里做家庭教师了。
她刚刚由江竹筠通过地下党组织安排,如今在郊区北碚天府煤矿职工子弟小学白庙子分校任教。
王珍如比江竹筠还大一岁,这时还是个没恋爱成家的大姑娘,但王珍如待人热情豪爽,与江竹筠的感情深挚得像亲姐妹。

江竹筠一直都叫她“珍姐”,王珍如也一直喊江竹筠“江竹”。江竹筠想,虽然一个大姑娘带着一个孩子会被人说三道四。
但事情至此,也只有把云儿先托付给王珍如最合适,王珍如了解了情况也肯定愿意帮这个忙的。信发出去后,彭咏梧和江竹筠便焦急地等待王珍如的到来。
虽然去下川东的事情还未最后决定,但夫妇俩却已经开始做着一旦定下,便马上就奔赴前方的各种准备。
他俩悄悄地整理一些东西,又准备抽一个空日带上云儿去千秋照相馆照一张合影。这时已是9月初,王珍如刚到白庙子分校报到才几天,马上就要开学、
突然,她接到江竹筠的急信,性子急躁的她不知有啥事,立马从北碚赶回了重庆市区内江竹筠的家。
王珍如这么快就来了,彭咏梧和江竹筠都没能料到。他俩正在家里整理一些将要处理的东西,屋子里显然没有以往那么整洁。

王珍如一看,就惊讶地问事情的来龙去脉。江竹筠说着说着,眼圈不禁红了,声音哽咽起来,“万一,我和四哥回不来,你就……就当云儿是你的孩子吧!”
王珍如愣了,有些不知所措。刚与江竹筠重逢不过几个月,就这样又要分别了?听竹筠这口气,好像要去的是特别危险的地方。
她不便多问,心中却万分辛酸。明知道自己一个大姑娘带着小彭云有说不出的难处,但她也明白这是竹筠和彭咏梧对自己最深挚的信任,更是革命的需要。
她一把搂着竹筠的肩,泪水抑制不住下流。事情就这样敲定了,江竹筠夫妇心中如生离死别一般难受。
夫妇俩一同在附近的街上给儿子彭云买衣服。不一会,竹筠拿着一件美军毛毯改制的儿童大衣、彭咏梧拎着一顶小军帽回来了。

江竹筠细心地为云儿穿好大衣,又戴好帽子。三个大人看着穿了新衣戴了军帽的小彭云的高兴模样,不觉眼睛又一阵发酸。
接着,重庆千秋照相馆拍了一张合照当做纪念。真的就要分别了。江竹筠抱着云儿亲了又亲,彭咏梧默默站在一旁注视,眼眶里滚动着泪水。
他们一行人来到汽车站,上了去郊区的汽车。就在此时,彭云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凄厉的呼喊着妈妈。听到这里,一向坚强的江竹筠紧紧挽着彭咏梧的手,哭成了一个泪人。
03 在父母的光环下长大王珍如帮忙照顾小彭云一段时间后,谭政烈(后改名谭正伦)在1948年冒着白色恐怖,从王珍如手中接过了小彭云。
从谭正伦接过小彭云,一直到新中国解放之前的两年时间里,她带着小彭云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劫难,让敌人试图逼迫江姐就范的阴谋没能得逞。
1948年6月,江姐被叛徒出卖被捕。敌人知道除了已经牺牲的彭咏梧之外,唯有江姐知道共产党游击队的情况,便对江姐施以各种酷刑。

因此,敌人没能从江姐口中得到任何的线索。于是,敌人再生一条毒计,派出特务四处抓捕彭云,试图让江姐就范。
1949年8月26日,江姐预感自己即将不久于人世,给组织和谭振伦留下一封遗书。
由于没有纸笔,她便巧妙将棉花烧成灰,加水制成墨水。接着,他用吃饭用的筷子削成竹签当成笔写下遗书。
遗书写好后,她委托策反成功的监狱看守。交到谭竹安手中。1949年11月,即重庆解放前夕,江姐被敌人杀害,她年仅29岁。
于是,江姐的这封遗书,便成为她留给彭云的唯一遗物。在遗书中,她写道:
“我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决不要娇养,粗茶淡饭足矣……”
重庆刚解放时,彭云只有三岁。当时,谭正伦还不知道江姐夫妇都牺牲的消息。她抱着一丝希望,带着彭云四处找寻两人的下落。

江姐遗书
当时,重庆成立了“脱险同志登记处”。谭正伦得知此事后背着她来到杀害烈士的地方寻找下落。不久,她才得知前夫彭咏梧去世的消息。
从小,彭云对母亲没有什么直观感受,所有的记忆都来源于几张照片和他人叙述。可以说,他从小就是在母亲的光环下长大的。
中学时代的彭云,除了脑袋特别大,鼻梁戴着一副瘸腿眼镜之外,没有丝毫特殊之处。学校得知他的特殊身份,专门选派的优秀教师为他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
只要彭云出现的场合,必然会产生轰动效应。当然,他的成绩也很优秀。学校只要有学习竞赛,他总是名列前茅,一直是班里的班干部。
但他从来不声张自己的特殊身份,从不骄傲,保持低调。一次,彭云和同学前往渣滓洞参加纪念活动。
不知为何,大家认出了他就是江姐的儿子,渣滓洞一时间被挤得水泄不通。为了安全起见,同学赶紧让他换上眼镜和衣服进行掉包,他才跑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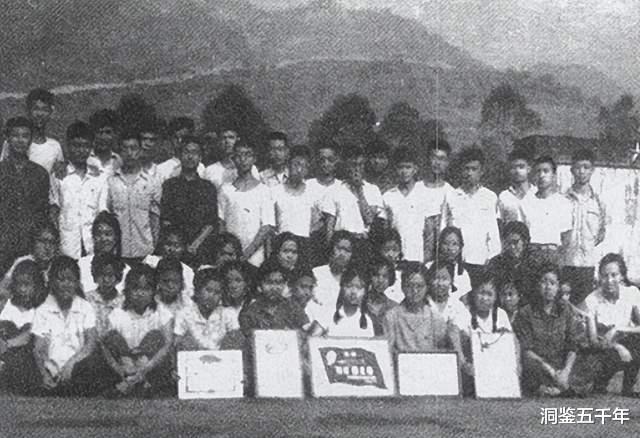
彭云不仅在长相上酷似母亲,也继承了父母的聪慧头脑。1965年6月,彭云从重庆高中毕业。
毕业后,彭云决定继承父业,并报考了大名鼎鼎的哈军工。下定决心后,问题也随之而来。哈军工是一所军事院校,报考条件不同于普通的大学。
在身体条件方面,最低的要求是必须要满足陆军服兵役的条件。当时的彭云只有91斤,体重不够,眼睛度数也不符标准。
后来,学校校长刘居英少将得知彭云的身份后,一锤定音,决定破例录取他。
当然,决定破格录取彭云的原因,除了他是著名烈士江姐子女这一根正苗红的特殊缘由外,还因为彭云是那年四川高考的理科状元。
这个条件,实在是太过硬了!其实,清华大学招生的老师早就盯上了他,几次找他做工作,劝他去清华学习。
04 坦言:母亲的遗愿我只完成了一半说到哈军工,彭云说自己当年铁了心要读军校,大妈对此却是反对的,大概是舍不得他离开她的养母谭正伦。

临行之前,谭正伦流着眼泪送彭云去学校报到,处在兴奋当中的彭云没有多想。到了报到所在地,他还和几个朋友去饭馆饱餐一顿。
1970年,彭云从哈军工毕业。学成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沈阳的一家工厂工作。1973年,他和大学同学易小治结为夫妇,一年后生下了儿子彭壮壮。
1975年8月,彭云被调到北京四机部电子研究所,成为一名工程师。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全国开始招收研究生。
酷爱学习的彭云不满现状,决定投考中科院计算机所。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和领导说明后。领导非常支持,还特批一个月的时间让他准备考试。
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成功考取研究生。在学校读书一个月后,国家开放公派留学的政策,这对他来说是又一次更大的机遇。
有了这次考试的经验,他自然如水得水,成功来到美国马里兰大学读书,研究方向是神经网络和人工智能。

这个方向对彭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科学领域,眼前的一切都深深吸引着他。如同久旱逢甘霖,他如饥似渴学习。
除了保持每天6小时的睡眠,彭云的全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三年过后,他终于成功获取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毕业后,彭云在马里兰大学当了一年访问教授。1987年,彭云回到祖国,并在中科院软件所做了一年多的研究工作。
美国一家知名出版社在看了彭云的博士论文后,决定邀请他前往美国,商讨出版的相关事宜。在这之后,他长年在美国生活和工作。
与此同时,他的妻子易小治也在美国先后考取硕士和博士学位,并来到当地一家研究所工作。

到上世纪的90年代,彭云已经是美国著名的人工智能专家,还是美国马里兰大学博士生导师兼终身教授。他在美国生活和工作多年,一直是中国国籍。
彭云虽然身在国外,但一直关心着祖国的发展和建设。他表示:“我虽然人在国外,但心始终在中国。我的根在中国,永远热爱着自己的祖国。”
1999年6月13日,彭云和妻子越过重洋回到了故乡自贡。在家乡,他和家乡人民汇报了自己情况。
当时,坊间传言彭云夫妇已经加入美国国籍。他斩钉截铁表示:“没有,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烈士的后代。”
在接受采访时,记者曾问起母亲留给他遗书上的内容和遗愿。彭云表示:“我在做人和做学问上应该完成了母亲的遗愿,可惜她的遗愿我只做到了一半,母亲还是希望我留在国内为人民做贡献吧!”

彭云是有遗憾的,好在他的儿子替他完成了心愿。中学毕业后,他来到哈佛大学数学系读书,后在普林斯顿攻读博士。博士毕业后,他便迫不及待回到祖国,为人民发光发热。
如今,江姐已经有了自己的第四代,相信他们能继承先辈的遗志和红岩精神,将其传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