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道德主义的适用有其具体的场景,即陌生人社会结构之下的公共空间乱象问题。
 缘何需要法律道德主义—基于陌生人社会场景的分析
缘何需要法律道德主义—基于陌生人社会场景的分析我们生活的环境正在逐渐脱离费孝通所总结的“生于斯死于斯”的地域性限制下的乡土熟人社会。

因此,乡土社会中依靠五伦而构建起来的,依靠传统道德维系人际关系的境况正在逐渐消失,逐渐形成了弗里德曼在《选择的共和国》中所描述的陌生人社会。
即人与人之间不再是熟悉的面孔,生活与行动的环境也是陌生化的,我们可以将其总结为物理空间的陌生化、人际关系的陌生化。
基于空间和关系的陌生化,使得传统人伦中依靠道德自觉来约束己身的模式难以为继,陌生人社会的生活场景加剧了道德的滑坡,使整体的公共道德变得更加松散。

人们在陌生的空间和关系之中,其行为与德行不再有强烈的约束感或自我谦抑。
人们对于整个社群的福祉或秩序不再负有自觉的义务,所衍生的后果便是整体社会规范的控制力不断下降。
因为“社会规范的社会控制能力取决于社会规模,在小规模社会中有效的社会规范在大规模的现代社会中可能效果相当受限”。

社会控制力的功能发挥受到抑制,加上陌生的空间、陌生的人际关系更容易稀释伦理上的守法负担,使得人们在此场景中更容易作出闯红灯、随地吐痰、逃票等微小违法行为。
与此同时,微小违法行为的治理自身呈现出诸多困境。
一是规制微小违法行为的法条本身多用概括性、抽象性的用语,对一些行为适用的是倡导性规范,处罚方式也较为模糊化;

其次,执法主体多样化,职权界定不清晰,甚至执法主体的执法权出现重叠和冲突;
二是星罗棋布的城市立法、规范性文件致使守法者无所适从,而违法者却有恃无恐,致使违法率长期居高不下。
三是这些受法条、执法模式等掣肘而呈现的治理困境,在陌生人社会的具体场景中被无限放大,使得治理更加难以为继。

显而易见,其在陌生人社会场景的治理适用中,能够通过“道德的法律强制”要旨来规制微小违法行为。
修复公共道德日趋滑坡的境况,重塑共同体在具体生活场景中的责任和共同的善。
可以说,法律道德主义在规制微小违法行为的实践中,能够承担重塑公共道德的功能。

因而,治理微小违法行为亟待以法律道德主义作为规制主线。
通过塑造一套更严厉、更全面、更具程序化和行之有效的规范体系,以此填补伦理约束缺位而造成的道德秩序真空,实现在陌生人社会中的秩序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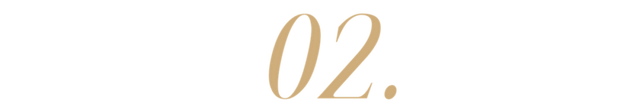 比较与重塑—从治理1.0到2.0迭代
比较与重塑—从治理1.0到2.0迭代从比较法的角度而言,法律道德主义适用于微小违法行为治理获得实效的典型国家是日本。

战后日本面临着经济转型所带来的社会转轨的压力,不断扩大的城市化所带来的陌生人社会难题,即道德滑坡、公共秩序混乱等困境。
与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微小违法行为乱象如出一辙。
随后日本政府出台了《轻犯罪法》,该法规定了“在公共场所言行粗野插队者”;

“制造噪音妨碍邻居休息且不接受公务员制止者”;
“在公共场所吐痰、大小便者,或让人吐痰、大小便者”;
“违反公共利益,随便丢弃垃圾、禽兽尸体,其他污物、废弃物者”;

“妨碍他人行走,或接近、跟踪他人,使他人感到不安者”“随便在他人住宅或物品上张贴东西,或随便移除、污损他人的标示物者”。
该等所列举的行为都将会受到罚款、拘留或者二者并处的严厉制裁,并由警察负责执行,违反《轻犯罪法》者将会面临“书面起诉”,甚至要面临短暂失去人身自由的处罚。
日本城市的微小违法行为也因为这部法而得到了卓有成效的治理,社会生活和公共空间也变得秩序井然。

值得探讨的是,当我们对随地吐痰、便溺、噪音扰民等微小违法行为束手无策,或囿于相关法律的惩罚形同虚设隔靴搔痒时。
数十年前出台的《轻犯罪法》早已将这些行为纳入严格而统一的法律文本中。
具体而言,《轻犯罪法》所规制的行为并没有达到“伤天害理”或严重违背伦理道德的程度。

更未达到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或侵犯法益的刑事违法性,仅是对道德至善的轻微背离,对公共秩序的一种低限度破坏。
而这些微小的过错或违法行为,在法律道德主义进入规范层面之后,成为法律对公共道德合法化的强制约束对象。
英国的Duff教授曾主张,“如果一种行为构成了公共过错,那么我们就有理由使之犯罪化。

通过将某些行为规定为犯罪,社会传达了公共生活的慎思过程和价值立场,以及对犯罪行为的公共谴责”。
对于公共过错行为用法律规制化给予的公共谴责,正是法律道德主义在公共空间治理的具体呈现,也是城市治理获得实效的一种典型路径。
相比于日本,我们在城市空间的微小违法行为治理方面起步晚,多年来一直亦步亦趋地摸索。

在立法实践中,我们已越来越倾向于将道德评价的行为纳入到法律强制中,逐渐将诸多属于文明道德评价范畴的行为纳入法律调整的框架中。
由说教劝止升格为惩罚规制,实现了治理从0到1.0的跨越。
以治理“随地吐痰”行为为例,不同于日本《轻犯罪法》早已将“吐痰”定罪量刑,我们最初在20世纪50年代对于该行为仅作为防痨的卫生治理目标。

通过展开一系列的集体运动,试图通过动员社会力量消除不卫生的行为,防止疾病传播。
随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有《关于禁止在旅客列车上随地吐痰、乱扔脏物和在不吸烟车厢内吸烟的规定》(一九八五年九月二日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铁道部发布)的出台,里面规定“对随地吐痰者。要进行批评教育,令其擦净痰迹,并罚款五角”。
随着时间迁移,如今越来越多的城市立法选择将“随地吐痰”行为作为维护公共秩序治理城市空间的对象,成为执法的目标。

从卫生运动到立法处罚,法律道德主义得到了有限的尝试。
虽然实现了从0到1的跨越,但是相较于《轻犯罪法》的罚则严格、执法者权责明确和程序正当,我们的立法仍然尚缺应有的成熟度。
最直观的体现是法律缺乏硬度,多数微小违法行为仅为警告或者低数额的罚款,从理性经济人角度而言,当前极为低廉的违法成本是众多违法者所能够负担的。

正因违法成本在违法者的可接受范围之内,所以在立法实现从0到1的跨越之后,微小行为的发生概率仍然居高不下,难以因应。
此外,虽然《轻犯罪法》所列举的行为,包括随地吐痰、便溺、制造噪音、妨碍他人行走等行为,在我国的法律文本中也都有所体现。
但却分布在各市的市容立法(例如《市容卫生管理条例》)、《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等大大小小的法律文本中。

这些法律文本显得繁杂、松散、粗陋,执法主体令出多门,繁杂意味着法的安定性受到挑战,而松散意味着法的实效性大打折扣,粗陋则显示了法的适用性缺乏可操控度。
整体而言,与《轻犯罪法》的巨细靡遗不同,我们的法还显得过于疏漏,诸多行为甚至并不在禁止范围之内,逐渐演化为法外空间。
所以微小违法行为的治理实现从0到1.0的跨越之后,应该再从1.0版本向2.0版本迭代。

这种迭代需要在法的密度和硬度层面双管齐下。
一要扩充立法文本的整体密度,改变当前过于疏漏的法律文本,设计出覆盖面更广、更细化的条文。
从具体的禁止性事项到惩罚的类别,都有明晰的依据,使得执法有据且不失正当性。

二要强化法律规制的硬度,改变现有的执法方式偏柔和、处罚力度偏轻微的缺陷。
当前警告、训诫,或者低数额的罚款,对于违法者而言如同隔靴搔痒,唯有提高违法成本,增强执法者的治理底气,才能改变众人将微小违法行为当成日常生活习惯的局面。
通过强化法的硬度,扩充法的密度,将法律道德主义进一步适用于治理中,才有可能获得实效。

 边界与限度—警惕父爱主义法律政策的扩张
边界与限度—警惕父爱主义法律政策的扩张霍布斯在数世纪之前已提出,一个社会若缺乏强有力政府,其不可避免地将会走向“人与人战争”的混沌局面。
因而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来实现社会秩序的有效治理,但强有力的政府在法律层面的意志表达又极易体现为父爱主义。
如何对微小违法行为进行有效治理,所考验的正是强有力政府的能力,但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从法律道德主义的治理实践最终可能向父爱主义越界。

法律父爱主义从立法层面而言,“所设立的干预之法客观上能保护行为人的利益,即可推定法律干预的目的是保护行为人利益。
而在执法层面,只要严格按照立法的规定行使权力,其执法意图并不影响执法行为成为家长主义行为”。
因此,其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土壤,在法治化过程中,往往以政府主导模式作为法律家长主义的外衣,基于正当理由而干预个体自治。

从具体生活场景看,诸如虐童、代孕等游离于道德与法律之间的社会难题,以及大量微小违法行为对公共利益和公共道德造成的冲击,客观上要求法律必须予以回应。
过去这种通过集中公权力的运动式治理模式,以“零容忍”的决心和态度对违法行为科以重罚,能够在短时间之内改善社会秩序,实现安定有序,甚至可以教育人们自觉守法尊法。
但是从实质法治角度而言,这种父爱主义主导下的社会治理仍然避免不了矫枉过正,合法性、正当性缺失等问题。

当下,我们正生活在形形色色、频繁出台的法律、法规、政策所结成的网里,如弗里德曼所描述的“第一个特征是我们的现代生活被卷人了法律的包围中,实际上受到了法律的困扰。
第二个特征是出现了一种激进的个人主义,而它又得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发展,至少在理想层面是这样”。
根据当前语境解读,第一个特征可以映照为父爱主义法律政策的不断扩张,挤压私人自治的空间,使公民自主选择的余地变得更加有限。

第二个特征可以理解为陌生人社会里的公共道德不断消散的过程,取而代之的是罔顾公共利益的自利行为。
这两种特征,正是法律道德主义适用于微小违法行为治理所面临的挑战,在治理乱象与保障权益之间,如何把握平衡,值得审慎考量。
因为法律道德主义与父爱主义有着相似的指向和类似的价值立场,对于增进福利或维护公共利益而言,现阶段的社群权益福祉易受侵犯。

公共空间乱象丛生、公共秩序混沌无序等,客观上都需要法律外力强行介入并给予矫正,以此重塑社会秩序。
正因如此,在治理乱象与保障权益之间,若无法平衡二者,很容易矫枉过正,执法的限度极易失控,导致私人自治空间受到侵扰,进而由法律道德主义转向父爱主义。
所以,把握平衡,需要在微小违法行为的治理过程中警惕法律父爱主义的过度渗透,始终守护边界和把握限度。

归根结底是治理不能脱离实质法治的框架,即塔玛纳哈所强调的法律价值合理性,将公民权利、尊严公正和社会福利都纳入到制度化法律的框架中,避免社会生活变得无法预测。
所以在治理过程中要防止运动式执法对于个人权利的挤压。
其中最重要的是把握一个清晰的界限,在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之间,在公共利益与公民权利之间,应当严守蕃篱,不能任意越界侵入私人领域,或随意干预私人自治。

 结论与展望
结论与展望基于分析法律道德主义在通过“道德的法律强制”来约束微小违法行为的实践,以及从比较的立场观察日本《轻犯罪法》适用所获得的实效。
尤其该法所体现的法律道德主义对违反公共过错、损害公共利益行为的强力纠正。
我们对法律道德主义的功能重新进行了还原与激活,认为其用于治理当前陌生人具体场景中的乱象,仍然具有其独特的功能和生命力。

就我国而言,一方面,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入推进,“我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同样重视政府的作用,更加侧重于制度的建设、运用、执行与变革能力”。
因此,由政府主导的科学、精确、细致的立法正源源不断地进入到我们生活世界。
对于微小违法行为的治理也正逐渐改变过去的无法可依、执法无据甚至是法外空间的混沌状态,实现了从0到1的跨越。

另一方面,在生活世界不断法律化的过程中,如果不能通过立法把最低限度的道德设定好甚至更高。
那么在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对城市空间的微小违法行为乱象的规制更难以落地。
当前微小违法行为治理所面临的困境便难以破局,包括立法模糊、惩罚过轻、执法不严、权责不清、违法概率偏高等症结将无法得到纠正。

因此,唯有从治理1.0向2.0更新迭代,改变偏柔和的法律态度,通过法律道德主义的有效介入,提高法的硬度和密度,才可能扭转当前这种松散无力的治理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可以看到法律道德主义所奉行的通过法律对道德范畴之内的行为进行调整的模式,正努力通过出台新规范和修订旧规范的方式实现。
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八条规定“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促使属于探望老人的伦理义务升格为法律强制。

从伦理规范迈向了立法实践,相信越来越多的属于道德意义上的文化表达会最终成为制度性的内容,从而用以规制伦理滑坡公德失范所演化的微小违法行为。
当然,我们对于法律道德主义的适用仍不能掉以轻心。
在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合法与正当等多组关系中,法律道德主义的实践应当有其合理的边界。
若无法秉持克制态度,维持其限度,法律道德主义的实践则最终可能走向运动式治理,甚至使得社会治理陷入泛刑化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