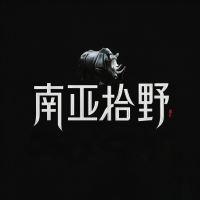历史上的扩张主义传统
印度历史上的扩张主义传统并不像一些西方帝国那样具有持续的全球扩展性,回顾整个印度古代历史,仅有孔雀王朝、莫卧儿王朝实现了对几乎整个南亚次大陆的完全统一,其余时间均处于偏安一隅的割据状态,整体民族意识中并不具有强烈领土扩张倾向。
相反,在被殖民时期英属印度的统治和领土扩张对近现代印度的扩张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的经济和军事力量,逐步征服了整个印度次大陆,并将其纳入英国的殖民统治,推动了印度原有边界的重新划定,以实际行动告诉了印度执政者“强国应该在地缘政治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为近现代印度的对外扩张主义提供了霸权范式。

为欢迎维多利亚女王访问印度修建的孟买印度门(也被视为英国殖民印度的象征)
同样,印度的扩张主义也可以理解为这段被殖民历史的创伤后遗症。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眼中,英国殖民统治造成了印度传统文化的断裂,在独立后的78年历程中,历任领导人都在尝试通过不同方式重建民族自信,但面对这样一个民族、宗教、文化割裂极为严重的国家实体,没有任何一种手段比对外制造战争或者冲突来的更加直接有效。
边界争端与民族主义情绪
印度对阿克赛钦(Akshay Chin)和藏南的狼子野心是印度地缘政治野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印度与中国长期对抗的核心。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中,中国恢复了对上述区域的领土主权(藏南地区在中国军队撤出后被印度实控),尽管战争后双方签署了多项协议,但边界问题始终未得到根本解决,且始终影响着中印关系,这场战争不仅是印度民族主义情绪的根源之一,还为印度日后在战略上对中国进行防范埋下了伏笔。

阿克赛钦风光
西藏对于中印两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印度对西藏的关注,不仅仅是出于文化和历史上的联系,更多是因为西藏地理位置,西藏的高原地形使得我军对印度北部地区具有显著的俯冲优势,因此,印度始终对西藏保持高度警觉和强烈的扩张野心。

藏南风光
“中国威胁论”与区域主导野心
印度自独立以来,其国家安全战略与区域领导地位的构建始终与其地缘环境、历史遗产和大国抱负紧密交织。作为南亚次大陆的主导力量,印度在维护国家安全一直面临严峻挑战。在巩固南亚次大陆主导地位方面,印度在军事干预、经济合作、核威慑与军事现代化方面进行了大量尝试,但因为体制机制、内部弊政、外部干预、小国对冲策略影响,始终难有大的建树。
军事干预的典型代表事件是印巴战争(1971年孟加拉国独立战争)和干预斯里兰卡内战(1987-1990)。对巴基斯坦,印度通过第三次印巴战争直接军事介入击败巴基斯坦以及1998年确立对巴基斯坦的核威慑,正式确立南亚霸权地位,但加深了巴基斯坦的敌意。对斯里兰卡,印度于1987-1990年向斯里兰卡派遣维和部队却卷入内战,最终撤军导致印斯关系恶化。这两起事件集中暴露了印度“大国外交”的局限性:想要高高在上以“德”服人,但最终却不得不撸起袖子直接下场。

孟加拉独立

斯里兰卡内战
印度妄图蚕食中国边境领土,更多是在争夺南亚及亚洲的领导地位的驱动下进行的。
南亚领导地位:印度一直视自己为南亚地区的自然领导者,尤其在对抗巴基斯坦的同时,它也对中国在南亚的影响力保持警觉。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对巴基斯坦和南亚周边国家的投资和合作,逐步增强在印度周边地区的影响力,印度对此产生了强烈的战略不安,认为这可能威胁到其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
印度洋战略:印度对中国在印度洋地区日益增强的存在感到担忧,特别是在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推动其港口建设、基础设施投资等经济项目时,印度认为这可能会使中国在印度洋上形成战略包围。因此,印度的对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防止中国在区域内“蚕食”其影响力的战略意图。
霸权愿景与现实约束直接导致了印度在历史包袱、地缘竞争与内部转型中艰难的寻找平衡。尽管其凭借体量优势在南亚保持主导地位,但因国内治理短板、族群矛盾、周边大国崛起、小国的实用主义外交,使其难以实现绝对区域霸权。为保持霸权姿态不得不极力维持“大要有大的样子”的体面,忽视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在军事上穷兵黩武、对周边小国肆意凌辱、在大国博弈中摇摆不定、缺乏战略自主。
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焦虑
中国的崛起,特别是在经济、军事和技术领域的迅猛发展,使印度感到了巨大的战略压力。作为世界上两个最人口众多的大国,印度与中国的竞争不仅仅体现在地缘政治层面,还涉及到全球的经济与军事竞争。
军事压力:中国在西藏的军事设施建设和对拉萨、日喀则等西藏城市的强化,实质上是中国了为加强边境安全的保障措施,但在印度眼中,这些举措都被视为一种威胁。印度认为,如果中国在西藏建立更为强大的军事基地,可能会直接威胁到印度的安全,特别是印度的东北边界。因此,印度对西藏地区保持高度警觉,并加强对该区域的军事部署。
经济与技术竞争: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以及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主导地位,成为印度与中国竞争的一大焦点。印度认为,为了确保自己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它必须在战略上保持对中国的平衡与竞争,防止中国占据过多资源和影响力。
对“印太”地区的战略重视
印度在全球战略中,越来越注重“印太战略”,即通过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合作,形成对中国的制衡。印度加入了四方安全对话(Quad),并且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军事、经济合作,目的就是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占据战略优势。
“四方安全对话”(Quad):印度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是一个多国合作框架,旨在加强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协调。印度通过这个平台与中国进行间接对抗,尤其在军事、技术、经济等领域的合作,目的是提升印度在区域内的影响力,抗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

四方安全对话
印度洋地区战略:随着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扩展,印度不断强化其在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地位,将自己定位为印度洋地区的主导国家,并通过加强与邻国和全球大国的合作来提升自己在全球战略中的话语权,旨在确立对印度洋的主导权、保障海上通道安全、遏制外部势力渗透,并通过经济与军事手段巩固区域影响力。
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裹挟
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tva):执政党印度人民党(BJP)的思想根基和胜选法宝,以“印度教特性”为核心,主张印度是“印度教徒的国家”,将穆斯林、基督徒等少数群体视为“外来者”,其意识形态可追溯至20世纪初的“国民志愿团”(RSS)。莫迪政府视印度教民族主义为强力政治动员工具,将其与大国叙事绑定,将民族主义与“新印度”(New India)愿景捆绑,宣扬“印度第一”(India First),将经济发展、军事崛起与印度教文明复兴挂钩。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强化国家凝聚力与政策执行力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加强中央集权化方面:通过削弱地方政党(如西孟加拉邦、泰米尔纳德邦)、统一税制(GST改革)、推进印地语官方化等措施,削弱地方离心力,强化中央权威;在增加改革合法性方面:民族主义情绪为争议性政策(如农业法改革、劳工法修订)提供民意缓冲,促进了相关政策实施。

印度教徒与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 vs Hindutva)
但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印度教民族主义为印度人民党胜选和顺利执政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又如同一把双刃剑,既为大国崛起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改革合法性,也在文明自豪与现实多元、强硬外交与务实合作、本土保护与全球融入方面被民意裹挟,最终耗尽国家信用,可能将印度推向“中等强国陷阱”——拥有大国抱负,却受困于内外矛盾难以突破瓶颈。
印度的地缘政治野心本质上是其大国复兴诉求与现实主义生存逻辑的结合体。尽管其凭借地理优势、文化底蕴和人口规模占据一定先机,但内部治理短板、区域国家博弈及大国体系性竞争,使其难以实现绝对主导,这使得印度利用对外强硬姿态来转移内部矛盾、增强国内凝聚力的重要法门,“攘内必先乱外”已成为印度统治者多年来惯用的政治手段。但如果印度在民族主义与包容性、军事投入与经济发展、霸权姿态与多边合作之间无法实现动态平衡,则其必将陷入因战略冒进与资源透支而止步于“有声无实”的区域强国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