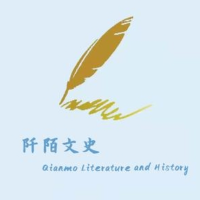她叫王叔晖,1912年出生于天津的一个富裕家庭。5岁时,她已是天津竞存小学的一名无忧无虑的小学生,“红椅子上的常客”。

那时,老师会根据孩子们的表现,将座位分为红椅子和黑椅子,乖巧懂事的同学能坐到前排的红椅子上,调皮捣蛋的则坐黑椅子。
后来,王叔晖却因上课总是偷偷画小人画,从骄傲的红椅子上被贬到令孩子们避之不及的黑椅子上。
但这并没有影响她的快乐,画小人画的乐趣从此在她心底扎了根。快乐的童年在1924年起了一丝波澜。
这一年父亲被免职,全家迁往北京,王叔晖告别童年伙伴与熟悉的家乡生活,与家人北上。
到了京剧之都,10岁的她很快迷上戏剧,心中萌生出成为女侠行侠仗义的梦想。
为了追梦,她在后院特意挖了个大坑,在腿上绑上沙袋,来回奋力跳跃。
这野小子般的行为却让父母直摇头,“一个女孩子家,整日蹦蹦跳跳像什么话?”
“那我要学画!”王叔晖脱口而出。

对于绘画,她的兴趣只增不减,火柴盒上的小人、月份牌,她见到什么就画什么。
本就期待女儿文静娴雅的父母喜出望外,欣然答应,还不惜下重本专门请来周肇祥、孙诵昭、徐燕荪、吴镜汀、吴光宇等大师教授女儿。

王叔晖不出所望,博采众长,刻苦练习,进步飞速,被获赞为“闺秀中近百年无此笔墨”。
细腻笔触中透着苍劲有力,这得益于她常年跟随孙诵昭练大字,“只有通过写大字锻炼腕力,勾画时才能得心应手”。
就在王叔晖朝着梦想快乐前行时,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降临。
1930年,突遭家庭变故,父亲竟带着姨太太远走高飞,家庭的重担一下子全落在了王叔晖的肩头。
昔日养尊处优的大小姐,不得不开始为生计奔波。
她每日不停地作画,常常通宵达旦。寒冬冷夜,三伏酷暑,日复一日。实在熬不住时,就点几支烟提神。

她省吃俭用,把一切好东西都优先留给母亲和弟弟,自己连一分钱都舍不得花。在一个女孩子最爱美的年华里,她从不曾给自己添置一件新衣裳。
她就这样一天天熬着,将弟弟抚养成人,为母亲养老送终。新中国成立后,她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曙光。

经朋友介绍,王叔晖进入出版总署工作,后来又加入了新成立的人民美术出版社,有了稳定的收入。
生计问题得到解决后,她重拾初心,全心全意踏上艺术追求之路,在条件极为简陋的屋里开始了创作。
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桌子,便是全部家当,客人来了也只能坐在床上。尽管物质匮乏,她的精神世界无比富足,全身心投入到绘画创作之中 。

就在这间阴暗潮湿的房子里,她默默地、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创作出《木兰从军》《孟姜女》等令人惊叹的作品。
在《西厢记》中,张生出现15次,竟换了七八套风格各异的服装,让人大开眼界。
后来,亲人回忆道,半夜醒来,外屋灯光格外明亮,那个瘦小的身影仍坐在画案前聚精会神地作画。
别人劝她休息,王叔晖不胜其烦地解释道:“你们怎么不理解我?对你们来说来日方长,对我而言却是来日方短。我能画几幅自己喜欢的画,比什么都强。”

在有限的生命里,她无限地追求艺术。她对这份事业的热爱,是对生命的一次重塑。
1977年,65岁的她被委以重任,开始创作《红楼梦》人物画。为了专心创作,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谢绝一切来客。

十几天后,栩栩如生的林黛玉在她笔下鲜活起来。
她说:“现在条件好了,我应该抓紧画。将来我死时,若只能留下一幅未完成的杰作,也许我就死在这画案边。”没想到竟一语成谶。

1985年,王叔晖身体已极度瘦弱,然而,她握着笔的手却依然有力,不停地挥动着。
7月23日,她倒在了一幅画旁边,那幅未完成的《惜春作画》成为她的遗作。
爱默生说,“人生最幸运的奖赏和最大的幸运产生于某种执着的追求,人们在追求中找到自己的工作和幸福。”

王叔晖一生历经磨难与坎坷,但因为心中有绘画,有追求,她在磨难之中绽放出绚烂之花。
她一生虽未婚未育、无儿无女,但她的精神世界却无比富足,留下栩栩如生、令人惊叹的作品,画出了世间最美的爱情。
她这种精益求精、对艺术永无止境的追求精神,如一盏明灯,激励着我们,向着更好的自己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