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元代以曲闻名,但实际上元代诗歌也很有特点,今天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下元代诗歌!
一、诗之本源的研究
元代诗格对作家修养论的建构,延续了中国古代“人品与诗品合一而论”的阐释模式,将情性看做是诗的本原,重视诗人情性的涵养与抒发。并在继承前人“情性论”的基础之上,朝细密化方向拓展,对“情”与“性”做了更为细致而详尽的分析。

但在涵养“情性”的具体方式上,又生发出两种分歧性的意见:一是“约情养性以立诗本”;二是“情性之悟自然而然”。元代诗歌在明确“情性乃诗之本原”的基础之上。又主张“涵养未至当益以学”,重视诗者的学识修养。认为读书不仅能改变学诗者的气质“学者以变化气质,须仗师友,所习所读”。而且还有益于扩充眼识,掌握更多的创作素材和技巧,故提倡“读书以厚诗资”。并为此提出“一观”“二学”“三作”的读书之法。

早在汉代的《诗大序》中,以“情性”亦即“性情”论诗的诗学传统就已经产生。《诗大序》中所谓“呤咏情性,以风其上”,即是从社会教化的角度对“性情”进行阐述,这里的“情性”体现了一种“达于事变”致用意识。但随着汉儒的衰退和魏晋玄学的兴起,对“情性”一词内涵的诠释也开始变得多样化。

如:钟嵘《诗品序》里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则是指诗人受外物的激发,自然有感而产生了创作的冲动。这里的“性情”不再是社会意志的传达而是诗人个人情感的特指,且包含了对情性抒发“自然”、“本真”的诉求。而元代诗论家在撰述诗格时,沿着前人所开创的“诗品与人品合一而论”的阐释模式,重视情性的涵养与抒发,将“情性”确立为“诗之本原”。并由此展开立论,讨论诗歌的形式建构同作家情性涵养的相互关系。

二、元代诗歌建构
元代诗格在建构其“情性论”时,按照“情”与“性”在诗歌创作活动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对“情性”的内涵进行了纵深层次的理论拓展。“元诗四大家”中的虞集,就曾在他所撰述的诗格类著作《虞侍书诗法》中以“世皆知诗之为者情性,而莫知所以情性”立论,并借助佛教“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思辨智慧对“何以为情”、“何以为性”展开细致的分析,他说:“心之色为情,天地、日月……草树,响答动悟,履遇形接,皆情也”。

同钟嵘《诗品序》中对“情性”是因有感于外物而生焉的观点相似。虞集认为,诗人之“心”是因有感于天地之“色”而生“情”,正所谓“情染在心,色在境,一时心境会至,而情生焉”。故“色”生“情”,“情”与“色”相连。而至于“性”则与“空”相等。他说:“性之于心为空,空于心等,……必非空非性,而性固存矣”。但正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故也可借助有色之“情”来得悟似空之“性”。但要想让诗中之“情”遇乎“性”,则此情“往往不属于常情,必其胸中有以绝乎众见,入乎无有”,如此方使“其天性流行,随地自在”。

具体来说,就是要使此情“拾而得之为自然,抚而出之为机造”,“由之而得乎性”。而虞集所指“自然”并非上文所说的天地、日月等自然景物。而是与天地自然相合“厚而安”的心境,“厚而安者,独鹤之心、大龟之息,旷古之士,君子之仁”。而其所谓“机造”也并非“切磋分寸、雕刻华藻”,而是能使“绝乎众见,入乎无有”,“往而深”的诗法功力,“往而深者,清风浥浥而同流……,抚青春而如行舟”。

所以情要遇乎性,关键在得之为“自然”,出之为“机造”。而这既包含了对诗人情感“自然者厚而安”的诉求,又有对诗歌创作“机造者往而深”的祈望。虞集说:“常闻古人两句三年,一呤双泪,是盖未至天性,……,雕刻华藻,面目非无所悦于人性,而遇之者远矣”。就是因为其“情”未出于“天真”、“自然”,又流于“切磋分寸,雕刻华藻”未有“往而深”之功力,故“未至天性,遇之者远矣”。

而在他看来诗的最高境界即是使诗中之情,得遇乎性。如杜甫平生之诗,虽遍集颂咏典歌、哀怨流离等各类情思,但“唯在目接而成之,似无非其固有者”,即其皆得于安厚自然,而非为文造情,出之于诗法却能超越于法,大匠运斤,大巧若拙。由此观之,诗中之“情”虽有不同,但也无不同。因为“善遇者,当有遇乎性”。而对“情”与“性”的分辨,最为鞭辟入里,最能体现元代诗格类著作细致批评这一特色的,当推陈绎曾的《诗谱》。

三、“十二感”的深究
陈绎曾将情分为“喜、怒、哀、惧、爱、欲、恶、忧、羞、惜、思、乐”十二种情感,称之为“十二感”。并对这“十二感”在文中所应遵守的规范、法度予以介绍,例如:“怒始欲张而终平”、“哀极之而后反”、“爱在言外”、“欲歆动而终归于正”、“恶欲忠厚”等等。

由此观之,可知陈绎曾十分重视诗歌情感的雅化,要求诗中之情与诗教相合,“发乎于情,止乎于礼”,使诗中之情既“真”且“雅”。故其所设置的表达规范,均是以温柔敦厚的诗教为旨归。陈绎曾在此基础上,指出诗中之情的审美效果应以“含蓄”为上。若非如此,则既有失于诗教之“温柔敦厚”,又会产生“思之切矣”、“叹不可忍”,“言不可禁”等“五不足”。故在其看来只有谨遵“温柔敦厚”之诗教,“思之切矣,仰而勿思。言不可禁,噤而勿言。叹不可忍,止而弗叹……含蓄至此使可言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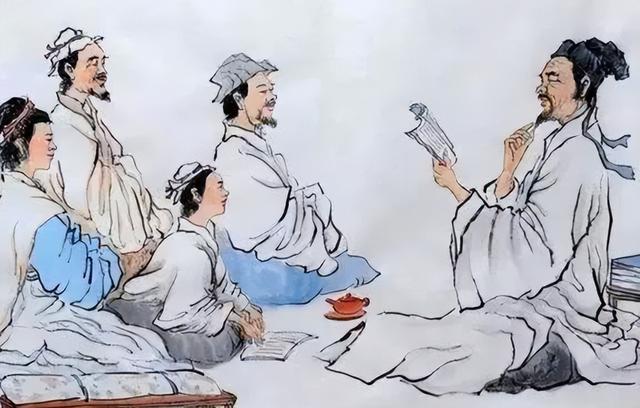
陈绎曾还在《诗谱》中将“性”分为:“仁、义、礼、智、信”这五种。并吸收了宋代朱熹有关“性即理也。当然之理,无有不善者”的思想。对这“五性”予以界定:“仁喜怒蔼然,皆爱人之心”、“义情之极载之以理”、“礼让谦有节,用物得度”等。由此可知,人之“五性”皆与诗教的“雅正”之旨相合,无有不善,正所谓“诗正礼义,性之本体”。故由此“五性”发而为诗,自然使诗既“雅”且“正”。但“仁义礼智”既乃“人之本性”,即非人力强求可得。故“须平日涵养”,方能“自然而然”。

而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则应使“心悟者随理而用之,不可执一也”。亦即警惕作诗者不要刻意锻造,执悟于技法规范。而要让自己娴熟的诗法技巧,依“五性”之不同,“随理而用之”,以达“理所当然,不知其然而然”的自然之境。而与虞集在《虞侍书诗法》中由“情”得“性”的观点有所不同,陈绎曾在《诗谱》中将“情”、“性”、“诗”三者的关系界定为:“诗本人情,性之妙用”。所以,在他看来“情”虽为诗之本,但“情”乃为“性”之用。由此构成了性→情→诗的逻辑联系。

因此,“情”的抒发也应遵循“自然而然”的原则。他首先指出:“喜怒哀乐,人之至情,未尝有意如此也”。故“情”与“性”均不可强求而得。为此,他提倡“心悟者随感而应之,不可执一也”,意即诗者在抒“情”的过程中,亦不可为文造情、雕刻锻造,而要使自己诗法技巧的运用,随外物对情感的感发而变化。做到“事至物来,不知其然而然”,同苏轼所说的“随物赋形”之法有相通之处。

同时,陈绎曾还指出诗人之“性”的抒发与“情”的抒发一样,除了要做到“自然而然”以外,还须有“含蓄蕴藉”的审美效果。例如:他在评点《诗三百》时就曾指出:“凡读三百篇,要会其情不足性有余处”。而所谓“情不足”就是上文所说的思之切矣”、“咏不能矣”、“言不可禁”等“五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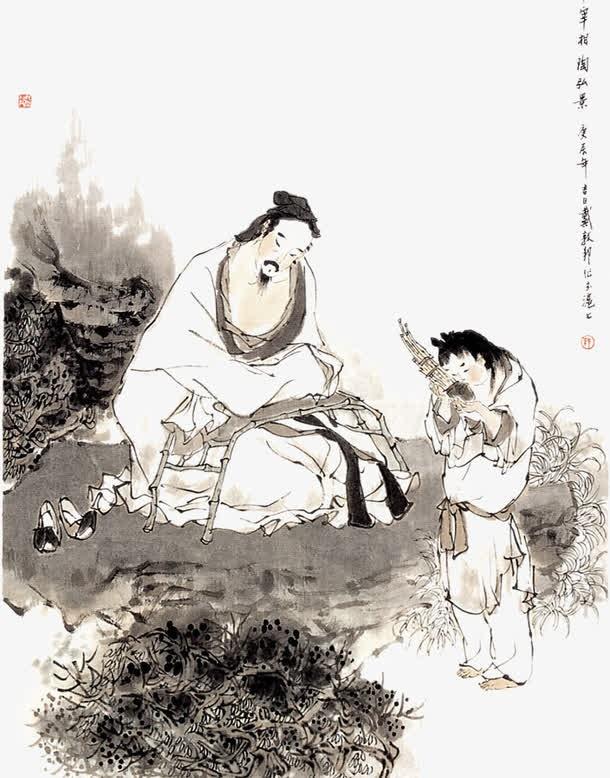
为此,他提倡“情不足,故寓之景”。主张将诗人的深情借助外景表现出来,让人言外求之,含蓄不尽。而所谓“性有余”亦是对诗人情性传达应含蓄蕴藉的强调,为此他主张“性有余,故见乎情”。即是让诗人之“本性”发而为诗中之“深情”。

四、“自然而然”且“含蓄不尽”的诗性诗情
以此之法,让诗人之“性”借助诗中之“情”委婉含蓄地表达出来。综上所述,无论是虞集《虞侍书诗法》中的“情”可得乎“性”,还是陈绎曾《诗谱》里“性”可发为“情”,“情”再发为“诗”的逻辑结构。都体现了元代诗格对诗中情性“自然而然”且“含蓄不尽”的理想追求。

而要想达到“自然而然”的至臻之境,获得“含蓄不尽”、“情往而深”的审美效果。既需要诗者掌握娴熟通变的“机造”之功,又须注重平日的涵养。唯此,方能使诗者“情性”的发挥自然而然,无矫揉造作之嫌。

而在涵养情性的具体方式上,元代诗格又生发出两种极具分歧性的观点:一是主张通过砥砺风义,调变性灵的方式,达到约“情”以复归雅正“真性”的目的,由此发而为文自然“既雅且正”;二是主张情性的涵养应自然而然,以保诗歌出自诗人真性情,再由至工而入于不工,以达天真自然的至臻之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