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刘呷了口茶,笑着摇摇头:“你小舅这倔脾气,真是十年如一日啊。”
可不是嘛,这已经是第八次了。每月一千,不多,可对在农村生活的小舅来说,也够他零花好一阵子了。可他就是不肯收,每次都原封不动地退回来,还附上一张字条,写着“我自己够用,你留着”。

想起小舅,记忆就像潮水般涌来,回到了四十年前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那会儿,我才六七岁,家里穷得叮当响,住在村口一间破旧的泥草房里。冬天,西北风呼呼地往屋里灌,冻得人直打哆嗦。小舅那时在村里的砖厂做工,一个月下来,能挣个二三十块钱。他省吃俭用,每月底都会去村口的供销社,往柜台上放5块钱,让供销社的王婶帮我存着。5块钱,在当时能买十斤大米,或者两尺好布料,对我们家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我记得很清楚,小舅每次去存钱,手上都磨出了厚厚的老茧,他从破旧的蓝布褂子里掏出皱巴巴的5块钱,小心翼翼地递给王婶,就像对待什么珍宝似的。“给我妹家的孩子存着。”他总是这么说,语气里带着掩饰不住的骄傲。王婶每次都笑呵呵地应着,还打趣道:“李建国,你这舅舅当得真够格!”

村里有些人背地里说小舅傻,说他放着好好的媳妇不娶,把钱都贴补给我们家。可小舅从不在意这些闲言碎语,依旧默默地为我们付出。
1985年,我八岁那年冬天,妈妈得了重病。那时候村里医疗条件差,要去二十里外的县城医院。小舅二话不说,把攒了大半年的钱都取了出来,骑着自行车,顶着鹅毛大雪,连夜把妈妈送到了医院。在医院里,小舅衣不解带地照顾妈妈,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给妈妈盖上,自己却只穿着一件单薄的中山装,在走廊里来回踱步。我记得,那几天小舅瘦了一大圈,脸色蜡黄,但眼神却异常坚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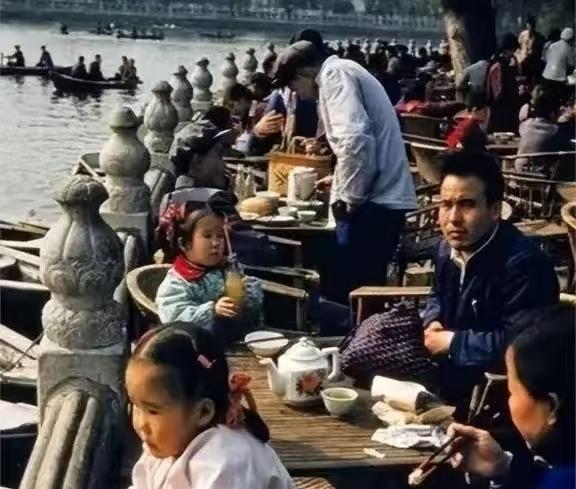
后来我才知道,小舅不光给我存钱,还偷偷地给妈妈存了一笔“应急钱”。爸爸当时感慨地说:“要不是你小舅,咱们家早就撑不下去了。”
1987年,我考上了县城高中。小舅高兴坏了,把这些年存的360块钱全都取了出来,用蓝布包袱包好,连夜骑车送到我家。那晚煤油灯昏黄的光线下,我看到小舅脸上写满了欣慰和疲惫。他把包袱递给我,说:“大侄子,这是舅舅这些年给你存的,供销社也快倒闭了,再存下去怕不保险。这钱够你读完高中了。”当时县城高中一年的学费和住宿费加起来要三百多块,小舅给我的钱刚好够用。

高中三年,每逢寒暑假回家,我都能看到小舅在地里忙碌的身影。有一次暑假,我看到小舅在烈日下收麦子,汗水浸透了他的衣衫。我跑过去想帮忙,他却把镰刀藏到身后,笑着说:“你读书的手,可不能干这个!快去树荫底下歇着。”那一刻,我的鼻子酸酸的。
1990年,我考上了大学。临走那天,小舅骑着他那辆破旧的自行车送我到村口。他语重心长地说:“大侄子,舅舅没文化,就盼着你能出人头地。”那一年,小舅四十多岁了,头发已经花白,却依然孑然一身。后来我才知道,早些年,曾有人给小舅介绍对象,对方条件还不错,可小舅为了照顾我和妈妈,怕娶了媳妇分心,就婉拒了。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城里工作。2020年,我的生活渐渐稳定下来,我开始每月给小舅寄1000块钱。可他就像当年妈妈生病时一样倔强,每次都把钱退回来。他在电话里说:“我种点地就够了,你自己留着用,城里开销大。”
去年夏天,我特意回老家看望小舅。远远地,就看到他在地里除草。他头发全白了,腰板却依然挺直。我走到他身边,问他:“小舅,你还记得供销社的王婶吗?”

小舅直起腰,用袖子擦了擦汗,说:“咋不记得,她去年走了。临走前,她还念叨着以前的事,说她这辈子最值得骄傲的事就是帮我存了那笔钱。她说,看着我从一个‘泥猴子’变成城里人,她比谁都高兴。”
“王婶走的时候,我去看了她。”小舅的声音有些哽咽,“她拉着我的手说,‘建国啊,你这辈子没娶媳妇,但你把妹妹的儿子培养成才,比别人生十个八个都强。’”
我递给小舅一瓶水,说:“小舅,要不是你,我可能早就辍学了。现在换我来照顾你,你怎么就不肯收呢?”
小舅喝了口水,望着远处的青山,缓缓说道:“你外婆走得早,我答应过她要照顾好你们娘俩。那会儿村里人说我傻,说我错过了好几个说亲的机会。可我心里明白,这不是傻,这叫亲情。”
那一刻,我的心里五味杂陈。原来,小舅为了我和妈妈,付出了一辈子。
那天晚上,我趁小舅睡着,偷偷在他枕头底下塞了一个信封。第二天早上,我发现桌上多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旁边还有一张歪歪扭扭的字条:“大侄子,记得按时吃饭。”这回,他终于没把钱退回来。
看着那碗面条和字条,我的思绪又回到了童年,回到了那个小小的供销社,回到了小舅每月存5块钱的日子……窗外,朝阳初升,新的一天开始了。小舅给予我的,远不止那360块钱,而是一份沉甸甸的亲情,一份永远也还不完的情。这份情,将伴随我一生,激励我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