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存在绝对的道德真理一直是道德哲学的基本问题。
 波斯纳关于道德的理论
波斯纳关于道德的理论之所以将这一文题目定为“关于道德的理论”,是为了区别于“道德理论”这个概念。

前者是波斯纳提出的一套理论,是有关(ABOUT)道德的理论,“是人类学、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或经济学家会研究的问题”。
简言之,它主要探究道德是什么、道德的来源、道德对人的影响等,但它并不指导人们的行为。
后者则是“一种关于我们应当如何行为”的道德的(OF)理论,也是波斯纳批判的理论。

它探讨的是“溺婴是否道德?安乐死是否道德?限制移民是否错误?”等问题。
它试图获得关于我们道德责任的真理。
波斯纳是通过批判道德理论来发展出关于道德的理论的,本文亦按照如此思路,根据波斯纳对道德理论的批判过程而得波斯纳关于道德的理论。

(一)道德是相对的
自希腊以来,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实在论之间的争论就不断出现。
近代以降,由于科学主义的巨大魅力和哲学上反形而上学的思潮,道德是相对的这一命题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客观道德真理不断受到质疑。
但是,坚持道德是相对的往往容易导致道德虚无主义,而承认道德客观性既可以保证道德可知论,又可以赋予道德规范以权威,保证道德规范的实施。

因此,在道德的相对命题蔚为大观的今天,道德实在论仍有较大市场。
对于反基础的实用主义来说,无疑,道德实在论是其头号敌人。
而波斯纳主要引入了社会学知识和生物学理论对道德是相对的进行论述以及对道德实在论进行反驳。

首先,波斯纳指出,道德是属于文化的、社会的,每个群体都拥有各自的道德法典。
现代社会厌恶溺婴,斥之为不道德行为。
但在物质贫乏,负担不起过多婴儿的社会中,溺婴却是司空见惯之事。

道德法典多样,是社会难以回避的现实。
但是,这种社会学常识的表述却不得不面对以下问题:在每一个文化系统中,都有天经地义,不可侵犯的道德真理,它与我们的直觉深深一致。
托马斯·内格尔就认为“客观性无须是要么到处都有,要么到处都没有的。

只要实在论在某些这样的领域中是真实的,我们就能合理地寻求客观的反思的方法,直到我们适应了这种方法。”
换言之,他主张我们可以通过诉诸主体间性所带来的普遍性来建构一种弱的实在论,从而承认道德真理的存在。

对此,波斯纳认为:
其一,这些从文化中延伸出来的公理都是“没有意思”的公理,因为它们太过抽象以致于无法解决任何道德疑难。
其二,许多道德公理是与目的相关的。

比如让美国人深恶痛疾的女性割礼,但在非洲穆斯林中确是普遍又普通之事。
美国社会以个人自由至上为据对割礼进行指责,但认可割礼的人会以维护家庭为理由对其正当性进行论证,在此,我们就无法论证个人选择或性愉悦的价值高于家庭稳定的价值。
这种道德分歧的观念只在于双方的目的不同、立场不同。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常常诉诸于道德公理去解决道德疑难,可能还会掩盖争议双方真正的目的与利益,从而导致道德疑难更加难以解决。
其三,波斯纳提醒我们注意美国的内部道德多元主义。

“一个来自纽约或坎不里奇左翼自由派世俗人文学者同一个魔门老人,一个福音派传教士,一个迈阿密的古巴血统商人、一个正统犹太人、一个空军指挥员或一个爱达荷农场主并不分享同一道德世界。”
所以,这一事实也就意味着在美国寻求道德公理的失败。

其次,波斯纳认为我们要慎用道德进步话语,这一点可能与大多数人的直觉相反。
假如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重新引入了奴隶制,显然,这是一个道德退步。
对此,波斯纳认为,“我们在说引入奴隶制是道德倒退时,我们只是在描述我们现在的道德感受,而不是在诉诸一个使我们也许可以把自己同前人进行道德比较的客观的道德秩序”。

更为重要的是,以进化论的观点来看,道德进步的实质含义是因为道德适应了时代的发展,道德先进与否是一个适者生存的游戏。
并且由于我们有了更多的知识我们才得以获知某些道德并非是达致社会目标的有效工具。
因此,道德进步的实质是知识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进而展现出了进步社会中道德的优越性,而非进步社会寻求到了所谓的道德真理。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波斯纳并没有从哲学上直接论证道德真理的有无。
其主要通过论述社会现实来论证道德的相对命题,通过“有用即真理”的检验标准来论证道德真理并无存在之必要,其思维方式是典型的实用主义逻辑。
另一方面,波斯纳在论述“道德是相对的”这一命题时,是踟蹰与徘徊的。

他似乎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但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又有深信不疑的真理,似乎他又变成了一个道德实在论者。
在相对主义和实在论之间,波斯纳似乎失去了自己的道德立场。
笔者以为,波斯纳所谓的“实用主义道德怀疑论”是存在于“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实在论”之间的一种道德立场,我们可以称他为温和的相对主义或者柔性的道德实在论。

相较于道德相对主义,这种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都是温和的、相对的,而不是激进的和绝对的。
“教义学上的怀疑主义怀疑世界独立于我们而存在,波斯纳的实用主义的怀疑主义则相信世界独立于我们而存在”。
教义学上的相对主义不认为一些命题比另一些命题更有道理,而波斯纳的实用主义的相对主义则相信一些命题比另一些命题更有道理。

因此,尽管实用主义者很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但他又拒绝接受教义学作为哲学立场的那种不可知论和相对主义。
具体到道德判断上,他拒绝粗俗的相对主义,即拒绝绝对地宽容与我们文化不同的道德观点。
相较于道德实在论,波斯纳的道德立场更具怀疑主义的色彩。

道德实在论认为,任何道德问题都是有正确答案的,总有一些我们不用怀疑的道德原则。
正如王海明教授对绝对道德的判断:虽然说我们没有道德的终极标准,但是我们却有认识和衡量其他一切道德原则的绝对原则。
是故,对于道德问题的解答,便能从绝对的道德原则推理到相对的道德原则,进而利用道德推理便可解决道德疑难。

波斯纳对绝对道德是持怀疑态度的。
他并不认为道德理论家能推导出绝对的道德原则,他怀疑这种判断是否真实,他认为任何关于道德的绝对性的断言都太过鲁莽。

并且以实用主义的态度观察这些绝对的道德原则,我们可能会有如下疑问:
如果没有这些普遍的道德原则我们就无法生活了吗?
如果没有这些普遍的道德原则我们就无法解决道德疑难了吗?

如果道德推理不是解决道德疑难的最好方式,为何还要苦苦追问绝对道德原则呢?
当然,波斯纳的道德立场还是具有实在论色彩的。
他认为,我们在将道德问题化解为事实问题后,是可以得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的。

对于他的这种观点,波斯纳说:“非教条的道德怀疑论者与柔性道德实在论者在这里汇合了”。
(二)道德论证无法推动道德行动
这一命题应是波斯纳最为核心的命题,也是波斯纳最为坚定、最为有力的论点。
他关注的是一个人行动的动力问题,他认为道德理论家的道德论证根本无法推动道德行动。

波斯纳主要从以下四个层面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论证:
第一,波斯纳认为,认可合乎道德的行为和实际的行动是没有关系的。
道德理论家可以向一个人展示某个行动是具有道德性的,但这并不能推动这个人的下一步行动。

比如一个道德理论家说服了一个人捐献肾脏给自己生病的兄弟是道德的,这个人说:“我应当这样做但我不打算这样做”是没有什么逻辑矛盾的。
第二,波斯纳指出,道德是一个义务的领域,是为他人服务的。
现实中很少有人愿意支付高昂的代价,放弃自己舒服的生活,去做一个高贵的善人。

这就表明了在没有强力的情况下,道德理论家需要克服人性的自利,驱动一个人去做不利于自身之事,这无异于天方夜谭。
或许有人会举出斯密难题进行说明:人不仅是自利的,同时也是利他的。
所以,某个具体的利他行为是否会为爱、为道德责任感、为某个伟大偶像的经历所召唤,所推动呢?波斯纳认为,其实人类拥有一种自我发现的功能。

一个道德理论家无法通过从一个道德推理到另一种道德的推理的方法来说服你。
但他可以给你提供让你骄傲自在或便利的理由来打动你,抑或是他可以提供一套精密的词汇来表达你本来就拥有的道德观点。
蓦然回首之中,你只是发现了自我,你只是受到了情感的召唤,这与利他行为和道德推理并无关系。

同时,波斯纳还对利他行为做了一个生物学的解释。
在他看来,利他行为是从“包容适应性的生物进化命令中衍生出来的。”
波斯纳指出,生物皆有基因数量最大化的冲动,作为社会生物的人,更具有帮助亲人的倾向。

在原初社会,亲密无间的生活让我们区分彼此并没有那么重要,于是,这种利他倾向也就被深深地刻在基因中并被保留到大群体中来了。
可以看出,波斯纳在此强调的是,利他行为是一种生物本能,他接受情感的召唤却不接受理性的论证。
第三,道德法典是深植于每一个的内心的,一旦进入我们内心,就极难更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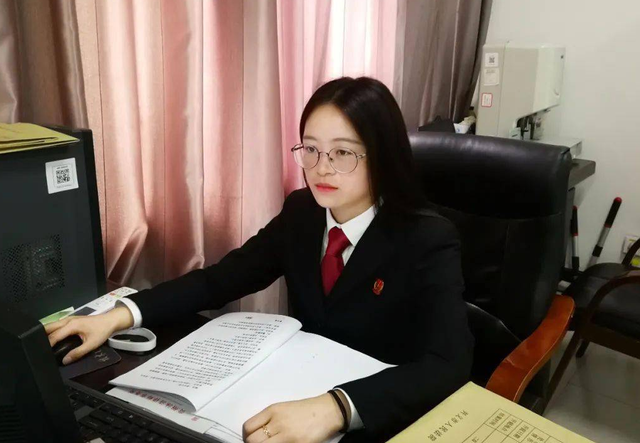
在《性与理性》中,波斯纳还提出一个更为重要的论点:“厌恶以及其他强烈的情感事实上为道德感觉提供了最为坚实的基础。”
如果一个人内心坚信胎儿便是婴儿,一想到堕胎就如想到杀生一样厌恶,你便无法通过论证堕胎是正当的,来清除这种厌恶。
在波斯纳看来,“一个人的道德法典并非气球,哲学家的针尖就会使它破灭。它是一个自我密封的轮胎”。

第四,波斯纳谈到了如何改变一个人的道德行为或道德观点。
其一,在波斯纳看来,要让人们行动起来,走出他们的自我利益,就需要“胡萝卜”和“大棒”,从而改变激励和惩罚机制;
其二,波斯纳指出,我们也可以像宗教那样,构建共同体感觉的仪式,制定众多习惯法则,从而凝聚群体忠诚的心理。

其三,波斯纳认为,诉诸于道德情感也是改变道德行为的良方。
像道德实业家那样,运用各种非理性的劝说技巧,绕过人们的理性计算,激发人们的荣誉感、自豪感。
其四,波斯纳提出,技术才是改变道德观点的关键所在。

在堕胎问题上,我们的道德观点是随着技术对胎儿生命的定义而不断摇摆的;
在同性恋问题上,几个世纪以来我们总把同性恋看作是道德的缺陷,但现在的技术已表明同性恋偏好是由基因决定的,我们之间的道德争论也就随之烟消云散。
在此,波斯纳认为,技术具有除魅的作用,它能让我们知晓道德的来源,让我们明晰道德的前提是什么。

比如,波斯纳用经济学分析了为何围观者越多受害者就越难以获得救助的问题,这是因为求助者的预期利益会减少。
他还认为:“我们决不能通过灌输道德训条来培养出生机盎然的道德正义感,我们所应关注的是:道德信念和道德行为是如何自然地从人类存在的境况中发展出来的”。
因此,法律应该求助于科学而不是道德理论。

对道德问题的研究亦不在于对道德观念的论证,而是经验性地观察我们“沉重的肉身”。
应当说,波斯纳这个论点是相当有说服力的。
中国著名哲学家陈嘉映教授曾经谈到过波斯纳的这个观点,他说:
“我自己也不相信辨名析理这类哲学论证在实际事务中有多大作用,也认为学院道德家在塑造道德观念方面恐怕为自己提出了不切实际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