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两点,我站在县档案馆的阅览室里,手里捏着一份已经发黄的借款合同。窗外蝉鸣阵阵,风扇转得吱呀作响,可我却感觉浑身发冷。
合同上写着”借款人:周建国”。这是我父亲的名字。日期是2008年8月15日,那年我刚上初中。合同下面还有一行小字:“连带担保人:李秀琴”。那是我母亲的名字。

我记得那个夏天特别热。热到连我们家门口的老榕树都蔫了,树下的石凳烫得没人敢坐。父亲总是穿着那件褪色的蓝色衬衫,在镇上跑来跑去。那时我只知道他在做生意,具体做什么,我从来没问过。

后来的事情像一场噩梦。父亲突然就不见了,只给母亲留了一张字条:“对不起,我欠了钱,实在没脸见你们。”那天晚上,我听见母亲在厨房里抽泣。她以为我睡着了,其实我躺在床上,数着蚊香燃烧的圈数。

第二天一早,母亲就把我转学到镇上的初中。我们从原来的三层小楼搬进了一间破旧的平房。房东是个老太太,看我们可怜,租金便宜了一半。平房的天花板上有个大窟窿,下雨时要用脸盆接水。母亲在市场卖菜,晚上还去餐馆洗碗。

有一次我发烧,母亲请不了假。她把退烧药和一瓶矿泉水放在床头,说:“难受就喝点水,我晚上回来看你。”那天下午,我躺在床上,听着外面的雨声,看着天花板上的水渍慢慢扩大。突然听见邻居家的收音机在放着旧歌:“让我再看你一眼,从别后,愁绪满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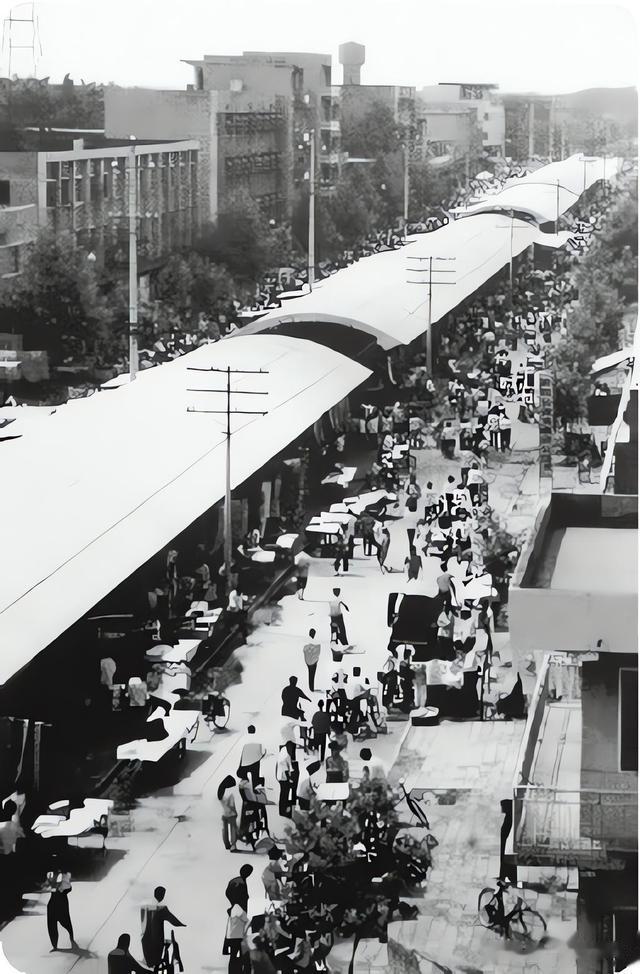
母亲总说我们家的事不要告诉别人。可镇上人多嘴杂,流言还是传开了。有人说父亲是被人骗了,也有人说他是自己赌博欠债。更难听的话也有,说他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我在学校经常被人指指点点,但我学会了装作听不见。

记得有一年冬天特别冷,母亲的手冻得裂开了口子。她舍不得买药膏,就用缝衣针挑破水泡,涂上老家带来的艾草油。那股苦涩的药味,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晚上她还要给人送外卖,骑着自行车在寒风里穿梭。我问她冷不冷,她总是笑着说:“不冷,运动了反而热。”

高考那年,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母亲拿出一个旧手提包,里面装满了零钱和皱巴巴的票子。她说:“这些年我一直在存,够你上大学了。”我知道那些钱里有多少是血汗钱,可能还有借来的。但母亲从来不说,我也不敢问。

大学毕业后,我在省城找到了工作。现在工资还不错,买了房子,把母亲接来一起住。她总说不习惯,想回老家。其实我知道,她是放心不下那些还没还完的债。
昨天,我专门请假回县里,想查查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想到在档案馆里发现了这份合同。合同显示,父亲借了五十万。背面还有一张纸条,是母亲写的:“我自愿作为担保人承担还款责任,请给我十五年时间,我一定会还清。”
就在我看这份合同的时候,手机突然震动。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我是你爸爸。这些年,我一直在关注你们。知道你妈妈把你培养得这么好,我很愧疚。我现在在广西做点小生意,手头宽裕了,想把欠的钱还上。”
我站在那里,眼泪不停地往下掉。阅览室里的风扇还在转,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窗台上有个老式暖水瓶,瓶身上的花已经褪得看不清了。
这十五年,母亲究竟是怎么熬过来的?那些深夜里的叹息,清早的泪水,被债主上门时的惊慌,全都被她藏在了心里。她从来不抱怨,只是默默地干活,存钱,盼着把我培养成人。
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母亲的钱包里一直放着那张发黄的全家福。那是我上初中时照的,父亲还在的时候。照片已经模糊了,可母亲却一直舍不得换。
晚上回到家,母亲正在阳台上收衣服。我从后面抱住她,她吓了一跳,手里的衣架掉在地上。我说:“妈,让我来收吧。”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你这孩子,突然这么懂事。”
我看着她被岁月刻上皱纹的脸,忽然发现她的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廊灯昏黄的光线下,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我知道,不管父亲回不回来,这个影子都会永远守护着我。
阳台上晾着几件还没干的衣服,风吹过,轻轻摇晃。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悠长而孤独。我想起小时候,每次听到这声音,都会幻想父亲坐着火车回来。现在我已经不会再这么想了,因为我早就明白,有些人走了就是走了。但是,有些人永远都在,比如我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