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特朗普所推行的经济政策,并非想带领美国穿越回工业社会,而是在后工业社会中如何保留适当的制造业比例。
在服务业占GDP 80%、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现实背景下,特朗普团队试图通过有限度的产业政策修复全球化过度扩张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构建起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竞争优势。

一、政策动因:后工业社会的结构性矛盾
1. 经济安全与供应链韧性提升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及2020年的新冠疫情暴露了美国长期以来深度依赖全球化供应链的脆弱性。
大量关键资源和生产能力外移使本土经济在面对危机时显得被动。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第一任期内特朗普政府“买美国货”行政令及应用《国防生产法》(如呼吸机生产)的案例,旨在强化关键物资的本土生产能力。
这些政策并不单纯强调产业规模扩张或回归传统制造,而是关注如何在美国本土维持一定比例的制造能力,确保经济安全。
2. 技术霸权与产业空心化的担忧美国核心高端制造业(如半导体)自1990年以来持续面临全球竞争压力,全球份额从1990年的37%下降至2020年的12%(SIA数据),而同期中国从0%跃升至15%。
核心技术及其相关产业的外迁不仅威胁到美国的“技术霸权”,还导致创新能力流失和产业空心化。
《CHIPS法案》的通过虽发生在拜登政府时期,但其政策思路与特朗普时期的“技术民族主义”如出一辙,目的是遏制关键技术脱离本土产业链,同时防止创新生态的进一步削弱。
3. 政治基础与社会稳定的维持美国中西部“铁锈地带”地区的蓝领工人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显著的失业危机,例如2000年至2016年之间,像密歇根和威斯康辛这样的关键摇摆州制造业就业机会萎缩了30%,直接增加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和社会裂痕。
特朗普通过关税政策(如针对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及《减税与就业法案》等措施,将企业税率从35%大幅降至21%,试图吸引资本流入并缓解区域经济失衡,借此遏制民粹浪潮并化解社会矛盾。

二、实施路径:适应性政策工具的选择
1. 通过成本重构而非产能复制实现制造业稳定美国制造业回流长期以来面临劳动力成本的巨大劣势。
根据Statista 2022年的数据显示,美国制造业平均工资是中国的4.6倍,这使美国无法直接依赖传统模式恢复大规模制造产能。
因此,特朗普政府聚焦在降低综合制造成本,以增强本土制造业的竞争力,具体措施包括:
能源成本优化通过放宽页岩气开采,降低工业电力成本,使其仅为中国工业电价的70%(EIA数据)。
税收成本削减跨国企业海外利润汇回税率由35%降至15.5%,促进企业资本回流,美国财政部统计显示苹果等跨国公司回流资金超过3000亿美元。
监管成本降低通过废除《清洁电力计划》等环保规定,减少企业合规性支出,提升制造业经营效率。
2. 选择性产业保护特朗普对特定产业采取了精准保护策略。
例如,他通过加征25%的关税,直接打击中国“2025计划”涉及的高新技术产业(如机器人制造、航空航天),并对日欧汽车企业采取关税压力谈判策略,迫使跨国车企在美国进行实质性投资。
数据显示,丰田、宝马等企业在2017年至2020年间增加了220亿美元在美投资。
此外,《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强化外来投资审查制度,直接阻止了中资对于关键技术企业(如莱迪思半导体)的收购,为美国科技产业链的本土化提供保障。
3. 就业质量的结构性调整特朗普政策接受了制造业就业“量减质升”的现实。
例如,2017年至2019年间,美国制造业新增就业约50万,但60%集中在食品加工、化学品制造等传统且自动化程度相对较低的领域。
相比之下,高端制造行业由于自动化水平更高,岗位扩张依然有限。
例如英特尔在亚利桑那州投资200亿美元建设晶圆厂,尽管规模庞大,但实际仅新增了3000个就业岗位,这表明制造业的资本密度正显著上升。

三、政策效果:有限调整下的战略缓冲
1. 制造业对经济的贡献未见显著提升尽管政策推动了制造业的局部反弹,但其带来的结构性变化有限。
据世界银行数据,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从2016年的11.7%略微上升到2019年的11.8%,与1980年制造业占GDP比重20.3%的巅峰时期相比仍然相去甚远。
显然,这些政策更多地是在现有基础上稳固制造业存量,而非实现显著的增量突破。
2. 供应链“近岸化”取代“回流”趋势虽然特朗普试图促使企业将制造基地搬回美国,但更多公司选择了“地理套利”策略,即把生产转移到墨西哥等劳动力成本更低但地理位置接近的国家。
数据显示,美墨加协定(USMCA)生效后,美国对墨西哥的直接投资从2017年的120亿美元增至2021年的320亿美元。
3. 技术封锁的意外反噬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实施的半导体出口管制政策在短期内确实削弱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一些能力。
然而,这种技术封锁也加速了中国自主研发的投资,据IC Insights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在芯片研发上的投入达到了440亿美元。
这种趋势正在推动全球产业链加速“去美国化”,一定程度削弱了美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主导地位。
四、历史镜鉴与未来走向
1. 与里根时期政策的本质差异1980年代,里根政府的自由市场政策鼓励公司全球化布局,通过产业外迁降低成本以提升资本回报。
而特朗普政策的逻辑更接近“嵌入式自由主义”,即把保护主义策略嵌入开放的协调体系中,其政策结构与德国“工业4.0”战略相似(德国制造业在GDP中占比达22%)。
特朗普推行的是一种试图在开放全球化中构筑产业保护的新模式,而非单纯的保守主义。
2. 两党政策基线下的延续趋势尽管第一任期内特朗普政策具有较强的个人色彩,但其政策基调已被拜登政府大体延续。
据彼得森研究所统计,拜登政府在上任后保留了特朗普时期81%的对华关税。
此外,《基础设施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的推出,进一步强化了对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等前沿制造业的投资,显示出制造业保护已成为两党共识。
特朗普再次上任当然继续第一任期内的经济政策。
3. 数字工业化的新路径特斯拉的德州超级工厂和亚马逊自动化仓储机器人的应用案例表明,美国制造业的复兴很可能不是依靠大量劳动力的传统模式,而是向“无人工厂”和“数字化服务”方向发展。
未来的美国工业结构可能呈现制造业与高端服务业的融合特征。

结论:后工业社会的再平衡实验特朗普时期的经济政策实质上是一场全球化过度扩张背景下的调整实验。
它明确服务业主导经济的同时,通过战略性保护政策在本土保留高附加值制造业的关键环节,这种做法兼顾了经济安全、技术竞争力和社会稳定等多方面目标。
尽管这些政策效果有限,但它为数字化时代美国重组全球经济竞争力提供了战略缓冲。
然而,未来的政策制定者需警惕保护主义可能带来的高成本和技术民族主义对创新环境的负面影响。
美国如何平衡工业化与开放经济的长期关系,将是未来经济政策面临的核心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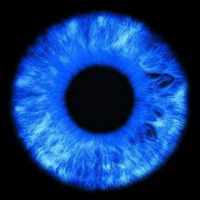
还有舔神经病的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