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易.讼卦》
内容提要:围绕英文right一词的中文翻译,晚清以来至少出现了四种语词创造,开启了本土权利理论的起步探索。尤其是当年的美国在华传教士丁韪良和本土学者严复,曾对语词翻译作出重要贡献。
梁启超接迎外来权利,除了借用杨朱哲学,还曾借用儒学。胡适则主要借用儒学。刘师培和蔡元培更是赋予权利深刻的儒学意蕴。各方的思想表达都曾让权利二字像容器一样容纳着中西各种学说。
探究权利理论缘何不为本土原产和近代中国缘何又会接纳外来权利的根由,都需要把目光瞄向儒学,说明权利必然会与儒学相遇。
如果说语词创造只是让权利观念在中文世界具有了语言载体,可以避免人们明明想要言说权利的内容却没有语言可供使用,那么借用儒学阐发权利,则会让原本属于外来的事物深深嵌入中国社会。借儒言权和语词创造,就构成了本土权利理论早期书写的两部分内容。
关键词:权利 儒学 杨朱哲学 墨家 容器论
何谓权利?西方学者要么解说为受法律保护的利益,要么界定为能获得法律尊重的意志。 当代中国学者鉴取西方理论,把它视为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人们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完全不同于本土古代的表述。
据《荀子•劝学》所言,权利不能倾,群众不能移,天下不能荡。生死皆由是,夫是之谓德操。据《史记•郑世家》所言,以权利合,权利尽而交疏。《荀子•君道》《商君书•算地》《盐铁论•杂论》等史料,亦有相关论断。
权利二字在其中,时而作为名词,意指权力、权势、利益乃至它们的结合体,时而作为动词,意指权衡利弊。既然当代中国的权利言说放弃古论而移自西方,那就有必要追问,难道中国全然没有自己的本土权利理论?本文想要指出,晚清以来,通过中英文翻译和语词创造,西式权利开始在中国出现,构成了对本土权利理论的起步探索。
回溯中国近代思想史,可以看到梁启超曾借用杨朱哲学和儒学接迎外来权利。既曾涉及权利造词,还曾借用儒学阐发权利的,当属胡适和刘师培。蔡元培也与刘师培有类似的理论旨趣。
因儒学属于本土原有文化,借用它,一旦促使权利具有浓厚的儒学意蕴,就可算是对本土权利理论展开了更深刻的早期书写。本文除了要分组考释先贤们的理论探讨和贡献,还会追索解答历史脉络中的某些问题。第一部分首先关注当年缘何要把“right”译为“权利”。
一、丁韪良和严复:新词新意的创生在英文世界,right作为名词,除了可以指涉中文权利,还能指涉正当,类似于正义,但又不像正义那么强势;作为形容词,则意指正直的、正确的、正当的、合法的、偏右的、直的。
若无权利二字出现,在中文世界的确难以找出能与right完全对译的语词。此种对译的最早发明者,是当年的美国在华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他的贡献看似只是翻译,其实却是创造性造词,促使西式权利语词在中国实现了从无到有。
具体说来,同治年间,丁韪良在主持翻译《万国公法》时把right译为权利,该书刊行于1864年。1878年,丁韪良翻译刊行《公法便览》时,交代了当初的考量:“原文偶有汉文难达之意,用字往往似觉勉强。如权字,书内不独指有司所操之权,亦指凡人理所应得之份,有时增一利字,如谓庶人本有之权利。此等字句,初见不入目,屡见方知不得已而用之。”
毫无疑问,在丁韪良看来,中英文无法完全合拍,只能勉强等同。他的思考中,犹有三点,需引起注意:其一,所谓有司所操之权,指向有司具备公权力,而有司属于公共机关;其二,所谓凡人理所应得之份,则指向人人都具有一定份额的私权利,即私人以权利与公共机关交涉,而并非公共机关独掌权力;其三,所谓庶人本有之权利,尤其是翻译时凸显出的利字,指向人人可得的利益。
比照中国古代对权利的表达,丁韪良通过翻译,让权利一词的语义在内容负载上实现了增设。正如学者所言,经他之手,权利二字依旧可以指涉公权力和利益,能与中国古代的权利二字相通,同时还让私权利成为其内在胚胎。
更重要的是,他还让利益成了私权利的内在构设。无论丁韪良是否知晓中国古代的权利论述,都不能否认他让中国古代词汇具有新意,甚至可以说,他让古语变成新词。不过,也正是丁韪良的翻译,让right的英文原意丢失了大半。
严复的翻译贡献其实并不亚于丁韪良,而且严复作为本土学者,原本就以中文为母语,当然会考虑如何避免出现翻译纰漏。他在翻译《天演论》和《群己权界论》时,就曾把right译为权利。据他在1902年的交代,如此对译实属强译。
追索背后的付出是,严复曾参考《汉书》《经义述闻》《管子》等古籍,一度认为以直字或职字对译rights,尤为铁案不可动。况且right原本就有直义,故几何直线谓之right Line,直角谓之right angle,但英文还有born right和God and my right诸词,严加比对,把right译为直或职恐怕并不合适。
显而易见,严复求索对译,所下的苦功比丁韪良更多。既然以权利对译right早已是包括自己在内的译界惯例,若改用新译,新旧共存,难保不会扞格,故此仍需沿用旧例。
区别于丁韪良的不得已而为之,严复是在遵照惯例把right译为权利的思考上表现出了不得已而为之。他的贡献在于,已经尽可能地全盘考量了中文权利和英文right各具有哪些语义,意在让翻译更加严谨和缜密。
既然他的翻译工作已经达到了如此高度,其他学者即使仍会对right的中文译法发表意见,恐怕都难以超越。这就隐含着以权利二字对译right会成为无需再质疑的定论,至此就为权利理论自晚清以来在本土的开显奠定了稳妥的语言根基。
二、梁启超和胡适:新词旧意的并立同样是在1902年,梁启超指出,吾民数千年来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权利二字断绝于脑中;杨朱曾倡导人人不损一毫,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人人不利天下乃公德之蟊贼,但人人不损一毫乃权利之保障,杨朱实为主张权利的哲学家。
梁启超既然认为国人脑海中无权利思想,那就是认为西式权利并非本土原产,但他同时认为杨朱是权利哲学家,似乎有些前后不一。但学界公论,梁启超那代人正处在中国思想界紧锣密鼓输入西方知识的时期,思想表达中的前后矛盾比比皆是。
更有人指出,梁先生出于一时愤慨,呼吁我们都学杨朱,但中国人缺乏权利观念的确是事实。 梁启超还指陈中西差异,谓国人重视交融互利,西人则重视你我分立,严格划清界线,只求不宜相扰。 认定西方善言义,难免会让本土儒家时常并举的仁义实现分立,义字就具有了指涉西方的新意,但又搭接着杨朱哲学,因而塑造出的便是新旧并立。
梁启超还指出,人生之有权利思想,天赋之良知。或强或弱或隐伏或澌亡至不齐者,常缘历史政治之浸润。孟子牛山之喻,先我言之。 所谓牛山之喻,是指人性趋善,一旦放任性情,必会使得善心不存,就如同牛山光秃,并非山上本来无木,而是不等树木生息,就要以斧斤进击。
梁启超借用牛山之喻,无非是要强调,且待人们养成权利观念,不可不待养成便要破坏。他明言孟子先己而发,其实就是想要让孟子之论成为自己表达思想的注脚,说明梁启超的权利思想中还混杂着儒学成分。

胡适
胡适在1933年指出,权利二字是近三十年来渐渐通用的新名词。在初输入时代,梁任公等屡作论文,申言中国人向来缺乏权利观念,于今必须提倡。随即指出,权利的本义是人人所应有,正确的翻译应是义权二字。
让人嗟呀是,胡适接着又指出,中国古代未必没有义权观念。孟子说得最明白:非其义,非其道,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此言就含有权利之意,不以与人是指尊重自己所应有,不以取诸人是指尊重他人所应有。孟子还曾倡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言指向人人自尊其所应有,自行其所谓是。
胡适既然认为中国古代存在义权观念,那便是认可古代存在权利观念,因为他把二者作了等同对待,甚至认为二者在本土以儒学作为根基。前后比对,他明明认为权利属于新词,透视出他在晚清以来的权利是否属于本土原有的问题上同样表现出了态度游移,促使新词与旧意并立。
迄至后来,胡适曾发表演说称,大丈夫应具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格,堪称中国经典里自由主义的理想人物。自由二字在中国古文里的意思正是自己做主而不由外力。
就此看来,胡适借孟子之论指陈人人自尊其所应有,自行其所谓是,即是主张人人各有自由,而自由就是权利。正如他所说,孟子言表不以与人是指尊重人人自己所应有的权利,言表不以取诸人是指人人皆要尊重他人所应有的权利。经此构思,便夯实了他所认为的晚清以来的权利属于本土原有且以儒学作为根基的论断。
综合审视,在胡适和梁启超的手里,权利二字简直成了填塞中西各种思想的容器。尤其是他们把西式权利视为本土原有,于史不合,但又未必不具有任何意义。具体言之,视外来事物为本土原有,能拉近本土与外来的距离,可以让人们更易于理解和接受外来事物,避免把外来的权利视为陌生的异己,即避免西学入华不为本土所识而酿制排斥心理,以便于助推着全社会以更快的速度萌生和发展出权利观念。
同时,更能体现出本土思想界未曾对西方学说囫囵吞枣,鹦鹉学舌。容器论一旦出现,本身就表明权利观念在中国滋生和发扬不必把它的肇始源头置换为本土文化,但要考虑到中国人对权利的理解不同于西方人。哪怕权利在中西盛行能表明中西趋同,但趋同的面向仅限于此。
三、刘师培和蔡元培:权利的儒学意蕴刘师培在其1906年出版的《伦理学教科书》中曾指出,中国古昔思想咸分权利与义务为二途,证据便是孔子曾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紧接着又指出,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实乃只尽义务而不享权利。杨朱则言,利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损一毫利天下而不与。此乃不侵他人权利,亦不为他人尽义务。杨朱和墨子皆不明人己权利应当持平。据《周易》所言,利物足以和义。以权利与人,即可使人尽义务。
显而易见,在刘师培看来,权利义务需以人己关系为依托,不宜像杨朱和墨子那样走极端。更重要的是,刘师培论定权利义务,曾借用孔子口中的利和义,但让它们摆脱了分别对应小人与君子的绑定,俨然成为了具有一般意义和指涉的用语。既不同于古代的权利表述,更不同于丁韪良和严复通过翻译创造了权利二字,可谓独辟蹊径,发前人所未发。
刘师培还曾指出,思想自由,行为自由,固为己身之权利,但自由不能无所限,故古人并言仁义。仁者,勉行善事;义者,勿为不当为。有益于人者,谓之仁,无损于人者,谓之义。事得其宜者,即持人己之平,裁制一己之自由,而不复损人益己。
据《礼记•表记》所言,义者,天下之制。制字同限,所谓无形之裁制。此番论断点明了自由不等于为所欲为,怎能不有所限制,否则就容易与人冲突。自由有所限,便是权利有所限,要受何限?即仁和义。仁引导着人彼此互益;义则规制着你我避免互损。
二者一正一反,在人己之间调配着何事当为不当为。人人皆应适当地自我约束,方能事得其宜。刘师培依据《周易》《礼记》和孔子所言立论,其实已经把权利放入儒学的义理框架,但他还曾做出更艰深的探索。
正如他所说,人心自由若不加详审,必生粗率和纷扰。宋儒咸言主静,静字同敬亦同整,一曰涵养,化粗率之性,一曰收敛,革纷扰之念。张横渠曾言,世人之心,止于见闻之狭;圣人尽心,不以见闻梏其心。程明道曾言,扩充己心,斯学求自得,不复流于拘;立志高超,不复偏于狭。
刘师培借用宋儒主张点明了自由能涵摄意志考量。内心不加详审,人所难免,终究需要化解由此而产生的粗率和纷扰,否则人己和睦未必能实现。如何化解?你我皆有必要提高各自的涵养和熟稔收敛,扩充己心,以无比大的胸怀容人容事,不宜斤斤计较,即可超脱拘谨和偏狭。你我各有权利,并非只能用来对垒。若能不失权利,还能和睦,那就会实现精神意志层面的更高自由,促使权利具有了满满的儒学意蕴。

蔡元培与北大
蔡元培在1912年出版的《中学修身教科书》中曾指出,我不欲人侵我之权利,亦慎勿侵人之权利,即恕道之义。我知某事有益于社会,力或弗能举,则望人举之。我若穷,常望人救之。人若穷,吾必尽吾力而救之,即忠道之义。二者皆是道德本务,前者兼为法律上之本务。若仅欲不为法律上之罪人,前者足矣;如欲免于道德上之罪,又不可不躬行后者。
蔡元培用儒家忠恕之道理解权利,恰与刘师培的做法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具体说来,你我互不相侵,便是对彼此权利的尊重,大致等同于义即勿为不当为。人们不仅不应该互侵权利,还应实现道德上的超越,尽己所能互助,不宜自私,换一种说法,便是人们应该扩充己心,立志高超,在面向他人的层面上保持心灵的开放。
你我互助即使并不被法律所要求,免不了仍会受到内心道德的驱使,无异于仁字的寓意就是让人勉行善事。
何谓忠恕?首先来看恕道,其意就在于我不应把我不想接受的事物推置给你,即是以心揆心,推己及人,以此作为你我权利的界线。我若任性妄为随意推置,难免会对你构成侵权。在我要不要把某些事物推置给你之前,我应当考量自己能否接受,藉此避免我做出侵权行为,就是要把侵权的可能性封锁在我自己的内心考量中。
我若能接受某种事物,我能否直接推置给你,其实仍需考量你能否接受,因为忠道强调的是你我彼此成就。若要让你接受,那就必须通过你我相互成就的方式共同承担未必两利的风险,怎能让你独自承担我给你带来的不利后果。
忠恕同样蕴含着心性考量。蔡元培和刘师培的区别只是在于,前者取径孔子的忠恕之论阐发权利,认为你我互不相侵,同时被法律和道德所要求,后者则取径孔子的义利之论,没有言及法律,但已经表明自由并非无度。
蔡元培还曾指出,我有行一事,保一物的权利,彼即有不得妨我一事,夺我一物的义务。我有此权利,人或侵之,我得而抵抗,若不得已,则借国家之权力予以防遏,是谓人人所有之权利,而国家宜引以为义务。
就此看来,蔡元培同样关注权利与义务的关联性,并且伸张了国家公权要为私人主张权利所用的基调。人们若非不得已,怎会借用国家公权,由此便赋予了国家公权有必要出场尽责的缘由乃至正当性。
综合来看,蔡元培和刘师培的权利观念同样具有容器论的倾向,填塞在容器中的正是中西交接必然会发生的文化互融。关键问题是,既然互融,缘何还要赋予权利以儒学意蕴,一则在于近代中国已非古代中国,区别恰恰可以表现为权利外来,二则中国依旧是中国,而非西方。
把两方面指向结合起来,那便是中国自古代发展至近代哪怕已经今非昔比,但仍旧不会跟西方完全雷同,岂能直接以西方的权利观念全盘掩盖中国的权利观念。如此看来,蔡元培和刘师培致思的目标其实都是想要把外来的权利妥当地安置在中国社会。
四、权利理论缘何不为本土原产?晚清以来,思想界一旦认定本土原有西式权利,自然就不会再去追问权利缘何不为本土原产。但是,外来权利最初在中国出现,只要涉及翻译和语词创造,本身就说明本土并不存在西式权利。
学者指出,中国社会历来崇尚和谐,不具备孕育出西式权利的条件。西方自宗教改革以来,人们搭接着基督教信仰都可以与上帝单独沟通,获取温暖,促使人与人的紧密交往在俗世生活中被看淡,因而盛行你是你和我是我的个体主义,早已是通识。

程燎原、王人博:《权利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权利便诞生在人与人保持高度分立的社会环境中。若有争议,可交由诉讼,诉讼的主要功能就是廓清你我各自的权利。中国人崇尚和谐并不意味着全无纠纷发生,若能展示出就连纠纷化解都要尽量促和,自然会以最大的力度证明中国人的确尚和,一并确认了权利不为本土原产的主要根由。
据《史记•周本纪》,虞国人和芮国人因争讼而赴周求裁,发现周境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经自我反思,放弃争讼。此番记载显示出周境情形被虞国人和芮国人所羡,甚至展开了优劣比较。争讼是一种负面的人际交往,难免会酝酿出终凶的结果。
遇有矛盾,与其争,不如让。若是一味去争,即使能争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恐怕仍是免不了伤神耗时。双方相争,在其他人看来,同样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因而争来争去的确能引来终凶的结局,至此足以显示出无争无讼是绝大多数人的共同追求。
若是果真发生了纠纷,且争执不休,又该怎么办?要么仍要自行和解,要么交由第三方,别无他法。虞国人和芮国人赴周的目的原是求裁,实际上就是想要通过第三人化解纠纷。假设文王曾出面帮忙,不外乎还有两种解决方式,要么调解,要么依据当时的某种具有权威性的公共规则裁判。
两者的指涉范围,相去甚远。后者需要顺延着纠纷的原有走势,直接依据公共规则决出谁胜谁败,目标导向并非弥合矛盾,反倒需要充分查清矛盾的来龙去脉,以便于做出精确的对错界定,难免就会对矛盾加以显扬。至于当事人日后是否会彼此视为仇敌,甚至愈发积累矛盾,则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即使日后果真引发了更大的矛盾,仍是不妨再次诉诸于依据规则裁判。
前者则是要扭转纠纷的原有走势,弊端在于未必能对双方的对错做出精确界分,优点恰恰在于促和,不仅可以确保双方在当前各退一步,不再相互仇视,更要助推着日后能和睦。
人们到底应该如何相处?据《论语•颜渊》记载,颜渊问仁,孔子答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又问其目,孔子解答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深究此言,视和听属于由外而内的信息接收,言和动则是人的外在行为,属于由内而外的信念输出。
礼是一种用来调整外在行为的规范,甚至可以指向由外而内,直至内心的落实。何谓克己,无疑指涉由己式自我克制,囊括着外来信息的内在处理,继而避免做出让他人感到不适的行为。何谓仁,古往今来众说纷纭,但它最常见的字形结构从人从二,意指人们在与人耦的关系中寻求定位。何谓克己复礼,无非就是要通过内外结合的方式促使人际交往保持和睦。
争讼的发生的确能表明凭借内外结合未必总会有效。关键问题是,如果就连内外结合都产生不了任何效果,那么人际交往终将失去一切凭藉。若是果真要通过抉择胜败的方式化解纠纷,无非只是把外在于人的礼加诸当事人,何须关注当事人的内心思考,但只要出现了内心不服判的情况,纠纷解决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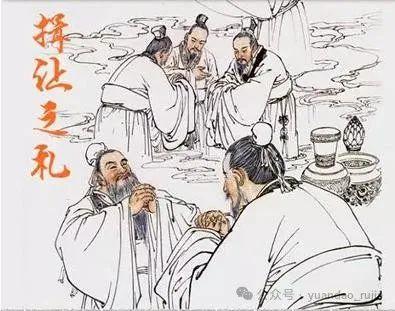
调解反倒可以兼顾内外,促使当事人在第三方劝说的情境中反思自我,并且主动地做出自愿的互让。就此看来,调解原本就是一种儒家化的纠纷解决方式。它在历史上的诞生何尝不是因为人们一直追求人际关系和谐,势必需要创造出一种能对此予以囊括的纠纷解决方式。
既然《周易》曾申言争讼的后果,说明调解的最初问世不会晚于《周易》对争讼的阐发,创造者理应是早已消失在历史中的普罗大众。尽管《周易》中没有出现调解二字,但与讼字相对应的另一种纠纷解决方式无疑就是调解。既然已经提到了争讼终凶,那便是在强调最好不要产生纷争,若是避免不了,最好能以调促和。反观虞国人和芮国人的故事,他们通过自我反思化解纠纷,即是诉诸于内,大有各自克己的意味。
以上种种,无不说明中国社会自先秦以来的确极致尚和。既然儒家与此相关,是否需要让它为中国古代没能孕育出西式权利观念担责?答案其实是否定的!因为中西原本就有差异,西方所产必为西方所需,中国不曾产则为中国不曾需,还谈何承担责任!
五、近代中国缘何接纳外来权利?既然西式权利不为本土原产,而且中西文化颇有差异,接下来需要追索的便是中国缘何又会接纳外来的权利?尤其是儒家,不具有排斥异己的倾向,足可以担任中国社会尚和的代言人。
据《孟子•滕文公下》所言,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赢天下。杨氏为我,是为无君;墨氏兼爱,是为无父。无父无君是禽兽。孟子在此的确对杨朱和墨家展开了批判,但没有予以扼杀的意思,顶多只能算是在感慨世风日下,潜在用意便是主张社会发展需由儒家引领。
相较于此,孔子则表达出了更加豁达的态度。据《论语•子路》记载,他曾言,君子和而不同!申言之,不同而和即为君子。深究其里,无异于宣称你我没必要事事保持一致,不妨彼此以开放姿态面对,我不能否认你存在的意义,你亦不能诋毁我存在的价值。
你我越是不同,若能以和相待,反倒越会说明你我皆有博大的胸怀。如此一来,由人到文化,塑造出的正是各种学说伴随着纷争的共存景象,而差异和纷争并不会对共存构成致命的威胁。
哪怕杨朱学说、墨家和儒家都属于本土的原生文化,它们又何尝不具有极大的差异,却又共同塑造着中国文化多元共存的格局。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自古以来一直如此,方才让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表现出了丰富多彩的面貌,无疑能为外来权利的存身提供空间,而且西学入华必然会让各种文化在中国的共存实现扩容,变得更加多元。
一言以蔽之,各种文化各有拥趸,差异阻止不了共存,至少儒家已经表达出了想要与非儒家和谐共存的意愿。中国社会之所以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不得不说儒家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
梁启超兼提杨朱和儒家,刘师培则兼提杨朱和墨子,最终把落脚点锁定在了儒家,何止曾把本土原有的各种文化摆在了各自的面前,更是通过具体的思想书写表达出了对本土文化原本就极其多元的肯认。
尽管梁启超和胡适曾声称中国本土原有西式权利,但他们并不曾全盘认为权利只以中国为滥觞源头。更稳妥的说法,应该是中国古代不曾孕育出西式权利,但不能否认中国人完全产生不了类似于西式权利的观念。 正是因为类似但又不同,方才让翻译难行。若是完全不同,那就失去了对译的可能。

更重要的是,西式权利入华终究需要面对本土文化环境,难道要让它始终只能以英语的面貌存在?因而通过翻译让它融入本土无疑是必要乃至必然的。丁韪良、严复乃至胡适就此做出的贡献不可磨灭。既然中国社会极具儒学底色,那么权利怎可避免会与儒学相遇!即使不能马上相遇,恐怕只是时间问题。
就此看来,刘师培和蔡元培堪称早期先行者,恰恰为权利融入儒学提供了难得的示范样本。即使胡适未曾像他们那样深挖,但同样曾提点权利与儒学具有关联性,因而亦可算是先行者。以胡适为比较对象,越能凸显出刘师培和蔡元培不仅有开创之功,甚至还能算是提出了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以儒学打底的权利理论。
综上所述,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至少出现了四种关于权利的造词:其一是丁韪良以利字搭配权字;其二是严复曾申言直字或职字,最终却遵循惯例照用权利二字;其三是胡适意在把权利订正为义权,但又认可更常见的权利二字;其四是刘师培取儒家的利字,配以权字,再搭接上仁字和义字。
伴随着语词创造,权利二字已经作为新词融入到了中文世界。如果说语词创造只是让权利观念在中文世界具有了语言载体,可以避免人们明明想要言说权利的内容却没有语言可供使用的状况,那么借用儒学阐发权利,则会让原本属于外来的事物深深嵌入中国社会。
语词创造与借儒言权便构成了本土权利理论早期书写的两部分内容。更重要的是,中西社会固然存异,但在权利是为利益和意志的层面上仍可寻求通约。尤其是刘师培和蔡元培,并没有让权利与西学割裂,而是在西学的基础上又赋予了权利特定的儒学意蕴,无异于为本土权利理论与西方权利理论有可能展开对话预留了空间。
本土权利理论的确像是一种容器,以开放的姿态容纳着中西的各种理论和文化基础。就此看来,借用儒学阐发权利其实只是关注到了中西社会对权利的言说语境不同,即中西方人们如何主张和运用权利完全可以各行其是。
既然中国社会尚和,那么中国人在表达自己的意志和利益诉求时仍有必要考虑本土的社会环境。刘师培和蔡元培的思考,为本土权利理论的书写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本土理论之所以区别于西方理论,可以借用儒学作为表征。追索缘由,并不是因为儒学诞生在先秦,以至于越古就越能强烈地凸显出中国社会的特质,而是在于中国社会自先秦以来一直具有儒学底色,即儒学在历史和社会发展中未曾退场,哪怕到了西学入华的时代,都一仍其旧。
在该种层面上,让外来权利融入中国,其实就等同于要让它融入儒学。甚至可以说,唯有让权利融入儒学,方能算是彻底嵌入到了中国社会。
文章来源:本文载《原道》第43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不做其他用途,若有侵权,敬请联系,十分感谢!
欢迎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