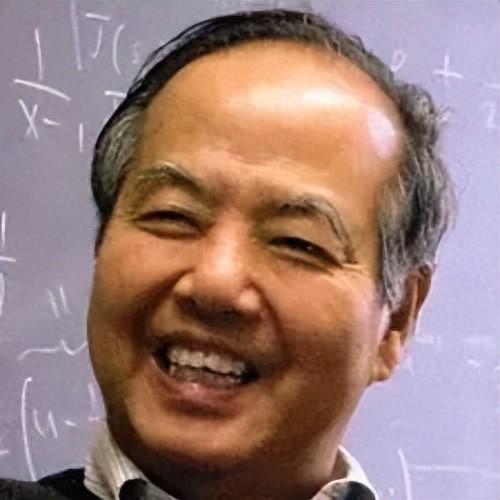
李政道
科学的发现和艺术的表达
题记:科学和艺术是不可分割的,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共同的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
除真空以外,什么都是由物质构成的。物理的、天文的、生物的、化学的物质体系,都是由同样的有限种类的粒子、原子、分子构成的。科学的目的就是研究一切物质的基本原理,即“物理”。中文名词“物理”,乃物之理也,最初包罗所有的科学,不限于西方名词“physics”所指的范围。
“物理”一词,可从杜甫的诗句中找到。杜甫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于唐肃宗乾元元年所做的《曲江二首》中有如下诗句:
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
这一非凡的诗句,道出了一个科学家工作的真正精神。不可能找出比“细”和“推”更恰当的字眼,来刻画对物理的探索。由此可见,在辉煌的中国文明历史中,艺术和科学一直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新星和超新星的发现
近世出土的中国古代甲骨文中,留有世界上第一次发现新星的观测记录。新星是一种爆发变星。它本来很暗,通常不易看见,爆发后的亮度却可在几天到一个月的短暂期间内突然增强几万倍。使人误以为是一颗“新星”,故得此误称并沿用至今。在一片于公元前十三世纪的某一天刻写的甲骨文上,记载着位于心宿二附近的一次新星爆发。在这片甲骨文上,说到“新大星”时,所用的甲骨文“新”字中,包含着一个箭头,指向一个很奇怪的方向。这个古老生动、具有艺术形象的象形文字强调了科学发现的创新性,显示了科学发现和艺术表达的一致性。
在另一片于几天后刻写的甲骨文上,又记载了这颗星的亮度已经明显下降。新星爆发是因核的合成而发生的。在一颗恒星的整个演化过程中,可以数次变成新星;而变成超新星,却只有一次机会,那就是它“死亡”的时刻。超新星爆发是一种比新星爆发猛烈得多的天文事件,爆发时的亮度高达太阳亮度的百亿倍。它意味着这颗恒星的最后崩坍,或是变成星云遗迹,或是因其质量的不同而变成白矮星、中子星或黑洞。
超新星是罕见的天象,在《宋史》中有关于超新星的最早的完整记载。其中说到,在宋仁宗至和元年的一天,即公元1054年8月27日,大白天的天空中突然出现一个如鸡蛋大小的星体,其亮度缓慢地减弱,两年后,即于1056年4月变得难以观测。这颗超新星位于蟹状星云的区域,现在我们知道其中心确有一颗中子星(脉冲星)。《宋史》中对其亮度变化的详细记载与现代的天文知识完全相符。事实上,这是现存的第一个这样的科学记录。
屈原如何推断地球必须是圆的
另一个艺术与科学统一的杰出的例子是屈原的文章《天问》。在现存的屈原的十七卷作品中,它属于第三卷。这篇以气势磅礴的诗句写成的文章,完全可能是基于几何学分析、应用了精确推理的最早的宇宙学论文之一。我在这里抄录其中的两段:
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隅隈多有,谁知其数?
东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顺椭,其衍几何?
诗中的“九天”指天球的九个方向:东方昊天,东南方阳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东北方鸾天,中央钧天。
在第一段中,屈原推理道:假定天空的形状是半球,若地是平的,天地交接处必将充满奇怪的边边角角。什么能够放在哪里?它又属于什么?宇宙这种非解析的几何形状太不合理,因而不可能存在。因此,地和天必不能互相交接。两者必须都是圆的,天像蛋壳,地像蛋黄(当然其间没有蛋白),各自都能独立地转动。
在第二段中,屈原推测,地的形状可能偏离完美的球形。东西为经,南北为纬。屈原问道,哪个方向更长?换句话说,赤道圆周比赤经圆周更长还是更短?然后,他又问道,如果沿赤道椭圆弧运动,它又应当有多长?
今天我们知道,地球的赤道半径(6378.14公里)略长于地球的极半径(6356.755公里)。而公元前5世纪的屈原,在推论出“地”必须是圆的之后,甚至还能继续想象出“地”是扁的椭球的可能性,堪称一个奇迹。这一几何、分析和对称性的绝妙运用,深刻地体现了艺术与科学的统一。
璧、琮、璇玑和正极
按中国的传统,玉璧代表天,玉琮代表地。《周礼》中就有“以苍壁礼天,以黄琮礼地”的说法。玉璧和玉琮,形状精美悦目,都是绝妙的艺术品。然而,人们却不知道它们的来源。这里,我想尝试地给出一种个人的新推测:也许璧和琮是某种更古老的天文仪器的艺术表现。
我们不妨设想,有一位生活在新石器时代的聪明祖先,他为美丽的夏季夜空所吸引,从入夜到拂晓,一直仰望着星星闪烁的清朗天穹,夜夜如此。当他发现天幕中所有的星星都缓缓绕着自己旋转时,自然会奇怪:什么宇宙之力能引起这样无限宏大的运动?而且,天空中有一个点是不动的,这又是为什么?
所有的转动都应当绕着一个不动的轴进行。天空中转动着的星星也一定绕着一个固定轴,即使我们看不见它。这个轴与半天球的交点决定了天空中的一个固定点(称为“正极”)。今天我们知道,这根轴就是地球的自转轴。我们的祖先虽不知道这些,但却聪明地领悟到,无论支配它的机制是什么,这一固定点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必须用仪器对它作精确定位。这就是我推测的璧和琮的来由。
璇玑是商代和商以前时期工艺品中的又一个谜,它很可能是新石器时代使用的一种真实仪器的艺术表现。按照西汉文献记载,璇玑是一种“径八尺,圆周二丈五尺”的圆盘,是“王者正天文之器”。自汉世以来,绝大多数人认为它是浑天仪的前身——璇玑玉衡中的一个部件。
最近我在想,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天文学家,要把天空中的固定点准确定位到零点几度,可能设计一台怎样的科学仪器。
我想,他需要一个直径约八尺、中心有孔洞的大圆盘,盘的边缘刻有三个近似方形的凹槽。圆盘借中心孔洞,套装在一个约十五尺长的直圆柱筒上端,柱筒截面的中心有一个孔。当天文学家在柱筒的下端通过盘边的凹槽观测天空时,可以看到每个槽中都嵌有一颗亮星。在庞阳教授的帮助下,我推测这三颗星很可能是大熊座(北斗)的η星,以及天龙座的η星和λ星。随着夜色的推移,这三颗星在天幕上转动。为了使每个凹槽继续跟踪同一颗星(方形凹槽对此最有利),圆盘也需要作相应的转动。如果能精确地作这样的跟踪,就能从柱筒中心孔自动观测到天空中的固定点。
在盘的边缘有三个凹槽,这是决定圆心的充分必要条件。槽的位置,又取决于对需跟踪的三颗星的选择。为了得到最高的精确度,理想的设计是选择接近相等的间距。显然,盘越大、圆形越精确、圆柱筒越长,定位就越准确。在新石器时代的技术条件下,要以竹、木材料制作直圆筒,十五尺恐怕是极限长度了。为了使圆筒牢固与准直,还要在空心圆柱之外加上一个更结实的套筒,比如一个硬木制的用石头加固的方形套筒。这样,就成了一台仪器,我们不妨把它叫做“璇玑仪”。
如果天空的固定点——正极,恰处于某一颗星的附近,人们定位的好奇心会更加强烈。如今,正极靠近小熊座的α星。过去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只是在公元前2700年左右是个例外。在更古老的年代,天龙座的α星几乎与正极相重。前面提到的三颗星,即天龙座的η星、λ星和大熊座的η星,在当时都是相对比较亮的星。巨大的“璇玑仪”很可能就是那个时期制造的。而天龙座的重要性也由此得到重视。
从新石器时代进化到商代,这一科学的成就又激发了艺术的创造力。巨大的“璇玑仪”的部件演变成象征性的精细抛光的玉制艺术品:刻意带了槽的玉片是商代的玉璇玑,不带槽的玉片是商玉璧,而圆柱筒和它的方形套筒则演化成商玉琮。
圆盘追踪于天,而方形套筒和圆柱筒则置于地。这就是璧表示天,琮表示地的原因。两者都是中华古代文明的杰出象征。作为玉雕,它是艺术;作为原始仪器,它是科学。艺术与科学如此紧密的联结,这正是中国文化固有的内涵。幸运的是,我们至今还保存着这些精美的商代玉器。通过这些艺术品,我们才得以一瞥祖先的科学成就。
在构思重建这一古代仪器的过程中,袁运甫教授的一幅关于汉镜与自由电子激光的画作,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几年前,亚洲的第一束自由电子激光在中国成功地产生。1995年,CCAST组织了一次国际研讨会,庆祝这一成就。袁运甫教授奉献的杰作,用自由电子激光为桥梁,沟通了我国古代的成就和现代的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