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像石中的山水树石大多以简略的象征性符号出现,提供大概的想象,而不做具体刻画。由玄而隐而游而寄情,这种玄学冥想式的“山水”使物象注入心象,并用心象定义物象;由发现并相信物之动人心处,而心寄于物,使山水物象实际上成为文人士大夫心物一体的理想。而一直延续到近现代的中国式的文人山水理念在这个时候基本形成,文人并以山水诗画进行了千余年的行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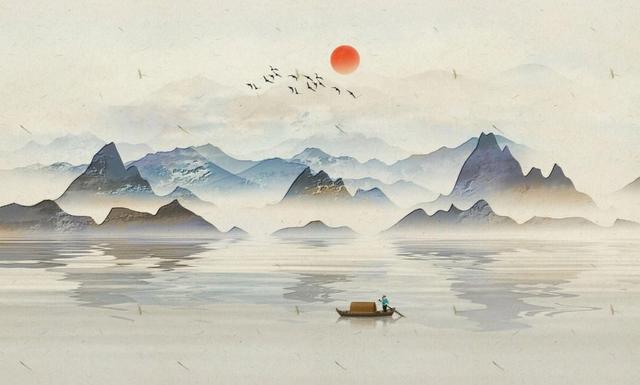
1、独立山水画产生的背景
魏晋南北朝,社会的动荡不安使传统礼教的作用显得薄弱,文人士大夫这个文化群体,或为安全感遭到破坏,或者为政治上的失意,或为厌倦人事纷杂,而逐渐开始思考自身存在的价值,而山林正好提供了这么一个可以用来避世的场所:它结构的曲折盘旋与外表丰富的植被,在游玩欣赏之前,首先有个天然掩体的作用。

对于那个时代的人,关于山的集体印象已经有很多,山由于地形陆哨难以攀登,而基本上是野兽与神仙的家园,人迹罕至,除了它本身高大浑厚的体积感,以及人站在面前或行走其中产生的实体与实体之间悬殊的大小对比,和在此之前就形成的隐士传统,都吸引着他们去探求。

“老”庄”与佛家思想似乎同时在他们身上施展作用:老子的无为合一,庄子的自在畅达,以及佛教的轮回世界观,又促使他们对存在产生疑问。怀着这些目的,文人“进山”了。而魏晋风流,也正从山林开始,从对自然的感受开始。“山水诗”这种以描写山林景物以及在山林中居住或行走的经验为内容的诗歌也在这个时候逐渐形成。

从早期的召隐诗里描绘的对想象中山林的险恶,不宜居住,以及劝隐士返还世间生活,到召隐过程中逐渐发现隐士生活的快意与亲近自然的感受,并对山林生活产生向往,而成为“寻隐诗”,并在寻隐的过程中产生归隐的念头,进而主动置身山林,自己切身感受与山林感情呼应带来的震撼与偷悦。

这个时候表达人生感悟的玄言诗也逐渐与山水亲近。“山水”逐渐成为可以欣赏,可以体味,并能与人的感情相呼应的“情物”。文人进入山水的这一动向,也促使了山水画成为了独立题材。既然是独立描绘山水,画者对于自然景物的专注,自然与以前简略示意图似的配角地位不可同日而语,绘画者亲近自然的感受,以及山水的特性与各种象征意义融为一体,在描绘景物的同时注重景物引发的感受(物象之神,之韵)寓情于景,加上“玄”的渗透成为了早期山水画的创作心态。

2、政治动乱导致社会价值观的转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局势复杂,政权更替频繁,曹魏代汉、晋谋代魏,西晋“贾后之乱”、“八王之乱”,北方游牧势力侵入迫使晋王室仓皇南迁。连年战乱导致人的生存环境受到很大的威胁,曹操《嵩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应该就是人们流离失所、命不保夕的真实写照。

政治斗争、同党伐异中,不少名士为政治立场而受到牵连,《晋书阮籍传》:“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不稳定的因素不仅仅存在于政治局势和社会生活当中,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与凝聚力对士大夫来说逐渐变得不可靠,对社会体制的依赖并不能带来稳定的安全感,礼教、制度的稳定性被不断交织更替的时局打破,变得暂时并难以信任。

两汉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而持续“倡儒”的手段很快失效,儒学伦理纲常、等级制度逐渐沦为一种表面的学识,与原来立命的意义脱节,成为精神负累。对个性的提倡在发挥了个人价值的同时,名教的力量加速淡漠。
何宴和王弼以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提出“名教出于自然”,这个“自然”是自然而然的意思,是“道”的原因,人意制订的法则仅仅是这个“自然”的产物之一。

到竹林时期猫康阮籍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对名教是直接的否定,认为固定的标准掩饰了天性,在人身上是用一种标准而取代所有,是一种强制的行为,并与老庄自在无为的玄机思想相违背。魏晋南北朝佛教的盛行给了人们对生命意义的另外一层理解,使“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行为准则无法独倨跟。

崇尚玄学引发回归自然的精神潮流正始以来,文人士大夫热衷《老子》、《庄子》、《周易》三玄典籍,“玄”逐渐成为魏晋南北朝的审美意识的主要潮流,庄子所主张的“齐物”、“心斋”、“坐忘”,逍遥尘世之外而游于自然之境的人生体验,为文人们开启了另外一扇窗户——在自然造化中解放人性,因此他们对自然的感情中夹带着冥想和思想远游的性质。

关于人的自我与物(客观存在)之间的关系以及存在的本质,老子的理解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的行为模式与存在方式由所处环境、境界(地,或地上万物)而来,而天象征整个宇宙,地上万物又是整个宇宙运行的一部分,并依宇宙运行的规律运行,这个运行的规律与“道”保持一致,而道源于本来如此(自然)。

这个本来如此或自然而然,就是老子对世界本质的描述。因为本来如此,对事件人为地加以干涉或不干涉而任其发展都是这个自然而然的进程的一部分,改变了的事态也仍然是这个“自然发生”,所以与道保持一致就是认同自然发生。又因为无法不与道保持一致,人本身就是自然发生的一部分,为与无为本质一样,所以老子以无为淡泊为态度。

这种自然无为的思想揭开了天地自然观的法门。而后庄子继承老子,以“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悦于万物”的齐物论或物我一体论,并以这种“我即我知觉到的世界(客观存在)”的天人合一为生活态度,从而泥灭了主客观。庄子的齐物论,把自然物提到和人自身一样的高度,由自然之物又反观人自身的存在感。这引发了后世对自然物的重新注视。

3、隐士传统与大规模的遁迹山林
文人士大夫在精神层面选择玄学佛释的同时,行为上选择遁迹山林、不问世事,逃离人世纷争。中国文人的隐士传统可以追溯至远古时期的许由和巢父。“隐”不再是为实现经世治国目的而釆取的手段,而是从心性出发的一种内在探索式的生活方式。
农耕社会后,山林成为了离群隐修之地,隐逸的方向有意识地指向山林。《逍遥游》中,亮因山林之胜廓而忘天下,以及《让王篇》里舜以天下相让,而善卷不受,“于是去而入深山”,这些高人的留恋之境和最终去处都是山林。古人心目中山因其高而成为接近天的地方,而神仙高士居住其中,并因其外表的地形与植被可以蔽身而堪隐,因其气息的宁静奇特而让人乐在其中。

无论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和目的“进山”,山水已经逐渐成为文人士大夫人生理想和内心情感的直接承载体。由此人们幵始了一场大规模的与自然之间的观照活动,观照活动是相互的,是“我”与“物”之间,而自然物引发的人的主观情绪很快成为诗歌,绘画,音乐的表达对象,物”象成了“心”象的载体,玄的世界观与情感相撞,相融,进而折回到“物”上。
从此,山水既包含了主客观合一,即天人合一”的精神追求,又与人的情感相应,真正成为了可以寄情的东西。

4、与山水自然的情感观照引发以山水为题材的表达——山水诗
自然山水的变化与恒定,稳重与高深带来的任何一丝感受都可能引发内心丰富的情感体验,山水似乎可以触发复杂的情思,并成为延续这种情思的强烈提示。左思和陆机的招隐诗中行情主体想象自己深入山林找寻隐士,反而被“逍遥”、“至乐”的自然山水吸引,开始表现出对自然山水的亲和态度。

羽化成仙的生命追求至先秦以来就深深植入人心,人们甚至幻想和构建出神仙“一池三山”的住所,游山水很多时候是带有“游仙”的氛围。同时,文人游览的自然山水承载着对超然玄妙的神仙境界的向往,山水在人们心里的情感和体验延展开来,山林生活仿佛就是神仙生活,身临山水之中的过程融入了更为丰富的精神感受,这种感受包含着文人的生命意识。

东晋玄言诗主张以玄对山水,他们置身山林,通过对清秀空灵的自然山水的直观体验,体悟“能矿然无累,与物俱往,而无所不应也”的淡然超拔。玄学大师在孙掉追忆庚亮时说“常在尘坂之外,虽柔心应世,獲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置身湛然的山水之间,内心矿达释然,山水之间玄思萦绕。“以玄对山水”便是这种以“开潘”之心观自然山水尽而“神明清朗”的综合审美感受。

庚阐“寂坐挹虚恬,运目情四豁”(《衡山诗》,置身于自然山水,在寂坐中拾起老庄式的虚静恬淡,在运目四野中情感也空豁恬静,人可以在亲历山水中“冥然玄会”庾友《兰亭诗三十七首》),目光所触、心神所应,仿佛万物皆蕴玄理。宗炳在“质有而趣灵”的山水间寄畅、散怀,自然山水成为了是合乎道本体的演绎,主体在作为对象的山水里更能发现、体悟一种生命情调,如此以虚静的内心去迎接自然山水而产生“畅神”的审美体验。

刘總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记述了由晋入宋时的想象情境:“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山水已经不仅仅是悟“道”的场所,对山水自然的直接感受就是对道的体悟。

谢灵运《游名山志序》“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山水已经成为了这位山水诗人的精神居所,他认为对自然的热爱是天然的,山水本身充当了他心中的“爱物”。谢灵运《初去郡》中“野矿沙岸静,天高秋月明”,仅仅是对客观自然的朴实的描述,他把景物情感化感受化,风景的背后则是看风景的直接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