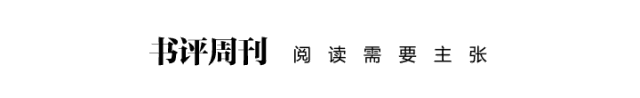
坐在候机楼的咖啡店里,喝着热美式,想起父亲讲过的一件小事。
前年他回江苏老家,返程去机场,二伯的儿子开车送他,二妈硬要同去,说她想看看机场是什么样。六十九岁了,从没坐过飞机,没见过机场。父亲说到了也进不去,啥也看不见的,她仍坚持要去,说哪怕从外面看看也行。
我似乎瞥见一个农村妇女,穿着笨重的红棉袄,裹着绿头巾,双手操在袖口,正从落地玻璃窗外往里瞧。二十多年没见,她当然认不出我。
 撰文 | 三书
撰文 | 三书  客心争日月
客心争日月

《蜀道后期》
(唐)张说
客心争日月,来往预期程。
秋风不相待,先至洛阳城。
回家六天,既漫长又短暂。村里有一种凝滞的氛围,几乎催眠般,使人变得迟钝,无法思维,甚至无法感觉。
县城景物萧条,行人稀少,单向度的物质现实,强大到封闭其他一切可能,想想就令人窒息。这里不是我的故乡,而是我从小就决心逃离的地方。
1月17日,中午的飞机,早晨七点起床,天尚未亮。下楼到后院,看见月亮,月亮挂在西边的天上,掩映在墙角的石榴树梢头。去年母亲寄石榴给我,还拍了视频,视频里这株树发疯似的茂盛,累累果实压弯枝条几乎垂到地上。
楼下房间亮着灯,我知母亲早就起了,悄悄推开门:她端坐在床上纳鞋垫,桃红被单桃红窗帘,柔和灯光映照下,房间里恍惚香气流溢。我多想抓住那个时辰,哪怕一小会儿。
前面房间还黑着,父亲还没睡醒吗?平日他都起得很早,何况我今天要走。忽然有些害怕,洗漱时禁不住胡思乱想:如果万一……这次专程回家给父亲过生日,果然古稀之年,既喜且惧。不是不可能,也许某天就会这样发生。洗漱出来,看见灯亮了,我松了一口气,父亲立在大衣柜前取什么,苍老的身影,他没有发觉我在看他。
我与这首唐诗中的方向相反,与许多人正在移动的方向相反,你们返乡的时候,我正在离去。父亲来到院子里,天即刻就亮了,他用清晨的声音问我行李收拾好没有,母亲也出来要给我煮饺子,我故作轻松地回答,尽量缓和临行前的紧张空气,想让父母觉得我随时都可以回来。
全家送出门,父母立在路边,也不说什么话,只是看着我,一脸不舍。出租车从西桥头下来,转瞬就到跟前,我把包丢进后座,上车前抱了抱母亲,也抱了抱父亲,他们的身体那么轻,好像正在消失。
我不仅是客,心也成了客心,来去匆匆,如同做了一个梦。以前如诗里所说:“客心争日月,来往预期程。”算好日子,归心似箭,尤其假期,来往皆有预定的程期。古人日程松弛,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我们,假期就像月亮,带着石头和重量,围绕工作行星旋转。我这次的境况另有不同,诗人张说怅惘他落在秋风的后面,我怅惘我离开在春节之前。

渭水东流去

《西过渭州见渭水思秦川》
(唐)岑参
渭水东流去,何时到雍州。
凭添两行泪,寄向故园流。
渭州,唐时属陇右道,在今甘肃陇西县西南。渭水即渭河,源出渭州鸟鼠山,东流至陕西境内入黄河。秦川即陕西关中地区。诗题中的这些地名,渭水秦川是我的家乡,甘肃我仅到过天水,即杜甫避难所至的秦州,那里山高野迥,四月犹冷,陇西在天水西北,更加荒寒。从长安到宝鸡,平原渐尽,群山陡起,使人忽觉在天一方,此等心情,北朝西行服役的游子唱过:“陇头流水,鸣声呜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陇头歌辞三首》其三)杜甫、岑参以及每个西行至此的人皆有同感。
岑参这首诗作于出塞途中,经过渭州看见渭水,油然而生思乡之情。去年我在宝鸡看见渭河,虽然离家并不很远,高铁也就四十分钟,但明显风土异样,在大桥上望着亲切的黄泥水向东流去,顿时亦有遥望秦川的惆怅。岑参此时走得更远,一路西行,尚有渭水相伴,直到渭州,过此风景尽是他乡。
他望着渭水东流,多么幸福,渭水会流到雍州。雍州即京兆府,在此指长安。“凭添两行泪,寄向故园流。”眼泪随渭水流向长安,也就把思念带回了故园。
今人还有这样质朴的感情吗?还会对着河流哭泣,还会望月怀远吗?现代交通和网络媒介改变了物理时空,别离不再是山川阻隔,远方在祛魅之后,不再是某个地理上的异域国度,而是回到它自身的隐喻——一个难以抵达的当下。
我们的情感生活需要重新定义。当我站在宝鸡市区的渭河大桥上,俯瞰河水漠漠东流,汩汩水声如此渺远,仿佛仍在古代的梦中。这就是渭河,我对自己说,它会流到家乡,成为我们的河。当我这样想时,我已站在童年的河岸上,河水风尘仆仆,仍在赶路,就像我。
我再次离开。出租车一下开走,毫不耽延,快得来不及看清,那个离别的时刻,饱含其中的生命体验,就这样草草萎缩。出了村,就是世界,白茫茫的海,父母和童年留在后面,我披上另一种身份,切换到另一个时空,和故乡分属两套系统,两种文明。
火车经过“马嵬驿”,站台上这几个字表示地名之外,更散发出寂静的古意。窗外是工业区,灰蒙蒙的天空,车里没有人在意“马嵬驿”,然而这并不等于和过去没有联系。我上车时,才把背包卸下,靠窗的老人立即伸手以邀请的姿势说:“可以坐!”他双手握着水杯,凝视窗外,神情和大地一样谦卑。斜对面也坐着一位老人,头戴高高的驼绒帽,足蹬卡其色长筒靴,身子微微倾斜,隔过道与一中年男子交谈,声音低沉而平静,我喜欢看他的脸,他脸上有一种遥远,仿佛从前的民间。
 岭南又是春来到
岭南又是春来到

《广州江中作》
(唐)张说
去国年方晏,愁心转不堪。
离人与江水,终日向西南。
出咸阳火车站,穿过空空的广场时,我邂逅了一首诗:“又将鞍马送残春,吹尽征衣染尽尘。还是前年旧时候,渭城花柳一番新。”北宋邵伯温的《过渭城馆》,不就是我现在的写照吗?我虽在春节前离开,前年春天回来,却正是渭城花柳一番新。这几句诗就像在等我,虽然写自久远的古代,也能与我不期而遇,即便在现代化的城区,我们也毫无阻隔,相视莫逆。
唐朝宰相张说流放岭南期间,心情愁闷,在路上作了不少诗。“去国年方晏,愁心转不堪。”离开京城,年岁方晏,思归之心更切。写这首诗时,他正坐在船上,不知具体是哪条江,滔滔江水让他深感自身的漂泊,心之所往和脚下道路不在同一个方向。
我坐在机场想到这首诗,不合时宜。在碎片化、原子化时代,我们的感情即生即死,我们既在这里,又不在这里。已经没有任何地方能留住我,没有任何人值得我思慕。机场距离我家四十八公里,感觉如同四万八千里,这里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在机场,大家都说普通话,虽然我一眼就能认出他们是本地人,和我一样。他们很自然地说着很不自然的普通话,尤其和他们的孩子,似乎想要融入全新的世界,似乎急于摆脱自己的身世。只有在洗手间,我才听见清洁阿姨和她的同伴说家乡话,聊着家乡事,她们都有一张乡下的脸。曾经有几年,我努力把普通话说得标准,但现在我更愿意保留我的口音,它就像胎记和我在一起。
回到广州。“回”已不再指向家,或者说每个能住上一段日子的地方,去那里都可以称“回”。不过一周,我发现这里的空气已经变了,潮湿和温暖告诉我,春天已经回来,新的季节开始了。我感觉熟悉,却不再欣喜。
路边的梅花开了,枯瘦枝条上,零星七八朵,粉红小花,开得有些疲惫。路上汽车来去如飞,电动车疾驰而过,没人顾得上看花。公园里的梅花,开得盛大,游人喧嚣,亦不得静好。花与人两相失,春天也不过自来自去,这就是我们生活的语境,一个广大到相忘的现实主义,诗歌也不再具有唤醒功能,而更像是失眠症患者的呓语。
昨夜下了一场雨,干渴的草木发出欢喜的啜泣。早晨下楼,湿润的尘土气息,带给我王维的诗句:“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那样的春雨,“浥”字真好,多么温柔,多么新鲜的早晨。
眼看就要过年了。小区南门外,两个五十多岁的妇人,手里各提一只鸡,满足而懒散地走着。那鸡被揪住翅根,惊耸着身子,脚爪缩起,喉咙里发出喑哑的叫声。广东有吃鸡的文化,对鸡的命名也很诗意,比如“杏花鸡”“怀乡鸡”“香草鸡”,这两个妇人提在手里的,和我在地铁广告上见过的那种鸡很像,叫“黄鸡”。她们走到一辆黑色轿车跟前,等在那里的是个同样年纪的男人,神态同样懒散,他打开后备箱,里面有个蛇皮袋子,鸡被丢了进去,袋口扎牢,后备箱门砰地关上,几人说说笑笑开车走了。
重回诗经原野 看天地镜像 听万物回响 “周末读诗”第三辑 《既见君子》
《既见君子:诗经十五国风行读》
作者:三书
版本: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5年1月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三书;编辑:张进;校对:赵琳。封面图为齐白石《渔村小景图》,有裁剪。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最近微信公众号又改版啦 大家记得将「新京报书评周刊」设置为星标
最近微信公众号又改版啦 大家记得将「新京报书评周刊」设置为星标

打开2024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