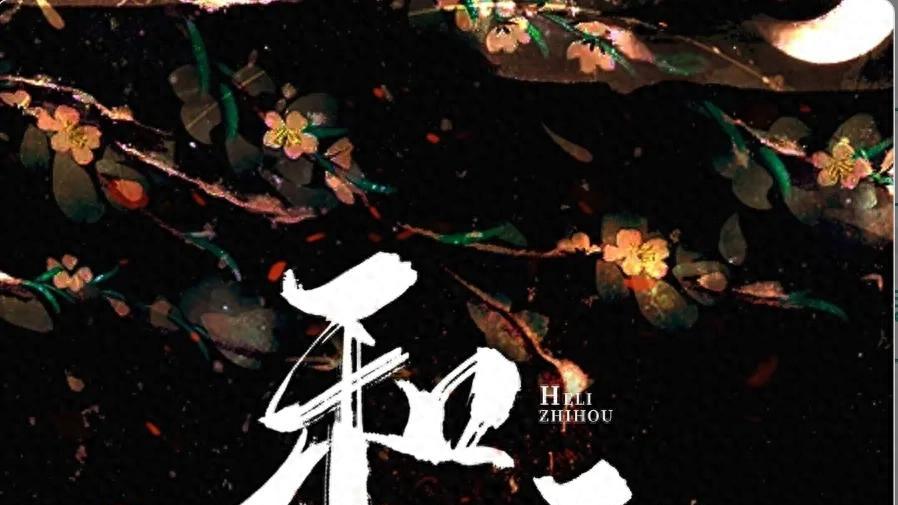各位看官您且看,两千年前那个血色黄昏,西楚霸王把剑往脖子上一横,惊得乌江水倒流三丈。要说这位战神死得也忒憋屈,明明有船可逃,偏要学那扑火飞蛾。今儿咱们不唱高调,单说北宋有个叫王安石的狠人,四句诗就把英雄皮袍下的小给抖搂干净了!

话说晚唐有个才子杜牧,打马路过乌江亭,看着江水拍岸,突然文青病发作:“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题乌江亭》)这调调就像村里穷秀才,总觉着皇帝老儿用金锄头耕地。
这位杜大人怕是话本看多了,以为打仗是小孩过家家。他哪知道,江东父老早把算盘打得噼啪响:当年八千儿郎跟着项王出征,回来只剩二十六具棺材。这要是放在现在,村口祠堂的族谱都能哭湿三卷。
您瞧他后两句“包羞忍耻是男儿”,活脱脱站着说话不腰疼。这就好比劝被退婚的姑娘:“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男人满街跑。”话是没错,可人姑娘绣好的嫁衣还压在箱底呢!

转眼到了北宋,有个叫王安石的硬核老干部路过乌江。人家可是在基层摸爬滚打二十年的老江湖,提笔就戳破杜牧的粉红泡泡:“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叠题乌江亭》)
这话说得透亮!好比村里张员外败光家产,还想找乡亲们集资翻本。王大人早把账算明白了:项王七年征战,把江东儿郎当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垓下大败时楚歌四起,将士们心里明镜似的,跟着这老板混,早晚得把命搭上。
要说王大人这双毒眼从哪练的?当年他在鄞县当知县,三伏天戴着斗笠下乡劝农,深谙“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看项羽团队,活脱脱反面教材:
鸿门宴放虎归山:好比厨子捉了偷米的老鼠,反倒在油缸里养着。
分封诸侯埋祸根:活像撒芝麻盐,看着热闹,转眼就被刘邦串成糖葫芦。
火烧咸阳毁家底:简直败家子烧祖宅,还美其名曰“断舍离”。

咱们把时光倒回公元前202年,看看项王的“糊涂账”:
①、八千子弟变纸钱:当年带出去的江东儿郎,回来时连抬棺材的人都凑不齐
②、范增玉斗碎成渣:亚父气得掀桌:“竖子不足与谋!”比现在老头摔象棋还响
③、乌骓马泪映残阳:连战马都通人性,晓得主子是条绝路
最绝的是项王那句“天亡我,非战之罪”。这话翻译过来就是:“不是我不行,是老天爷使绊子!”活像赌徒输光家当,反怪赌桌不平整。要按这个理儿,当年巨鹿之战破釜沉舟,莫不是老天爷给开的VIP外挂?

咱们拿三个镜子照照这位霸王:
①、百姓的铜镜:楚汉相争时,关中父老箪食壶浆迎刘邦,看见楚军像见了瘟神
②、谋士的菱花镜:韩信、陈平这些大才,在项羽帐下连梳头机会都没有,转身帮刘邦戴上皇冠
③、时间的青铜镜:太史公笔下那个“重瞳子”,说到底就是个放大版的村头二愣子
您说项王不懂人心?人家临终前还知道把头颅送给故人换富贵。可偏偏活着的时候,把人心当鞋底泥踩着玩。这就好比财主捧着金碗要饭,临死才想起碗能换馍。

杜王二人的笔墨官司,堪称史上最早“神仙打架”。杜牧像茶馆说书人,专捡英雄落难处描金绣凤;王安石则是县衙师爷,账本翻得哗哗响。
这差别好比看戏:
杜牧在台下抹眼泪:“霸王别姬真感人!”
王安石在后台打算盘:“光这月戏服钱就亏三十两!”
难怪钱钟书先生点评:“唐诗如牡丹,宋诗似老梅。”杜牧笔下是热血传奇,王安石纸上却是冷峻现实。
如今站在乌江亭遗址,仿佛还能听见当年的对话:
亭长:“江东虽小,尚可称王”
项羽:“无颜见江东父老”
王安石:“不是没脸见,是没人愿见”
这场景像极了现代爷孙对话:
孙子:“太爷爷当年为啥不逃?”
老人:“逃?债主都在村口蹲着呢!”

结语:
项王剑锋抹过脖颈时,带走的不仅是一个时代,更照出千古人性真相。杜牧的诗是英雄的遮羞布,王安石的话是现实的解剖刀。如今乌江水依旧东流,告诉我们:再硬的拳头,打不散人心;再浓的血色,染不红江水。所谓英雄气短,有时不过是把“面子”当成了“里子”。
下次您路过和县乌江镇,不妨对着江水说句掏心窝的话:老项啊,要是当年听王荆公劝,咱安徽早多个“霸王渡”景区喽!
声明:本文内容和图片均来自网络,仅用于传播积极正能量,不存在任何低俗或不当引导。如涉及版权或人物形象问题,请及时联系我们,我们将立即删除相关内容。对于可能存在争议的部分,我们也会在接到反馈后迅速进行修改或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