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那次采访前,没人会意识到,这俩人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和以往采访的你问我答不同的是,杨南生没有顺着她的思路回答问题,相反的,俩人聊诗歌、聊小说。因为保密制度的存在,张严平看不到他真实的样子,却看到了一个不同于以往严谨科学家的形象。两个小时的采访,她没拿到自己需要的素材,却感受到了灵魂的碰撞。她采访的这个人,太厉害了。简单概括:杨南生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开创者和组织者之一,当年为了让航天事业完成从0到1的起步,这群科学家们,都吃了不少的苦。为了设计中国第一枚发射卫星的运载火箭,杨南生从英国留学回来后,便一头扎了进去,在西苑旅行社里租了几个房间,趴在水泥地上设计图纸,用蜡烛和手电筒,开始了中国卫星、火箭雏形的设计与研制。为了设计探空火箭,为卫星上天探路,他带着科研团队扎根荒草丛生的发射场,那里的防空洞破败不堪,杨南生和科研人员连续十几天都要吃住在这里,大家挤在稻草铺成的地铺上,身上都生了疥疮。为了攻克固体燃料发动机这一世界难题,杨南生每夜挑灯苦读,灯光从来没在凌晨1点前熄灭过,829页的书,都有他用英文写下的长长短短的阅读笔记,和密密麻麻的各种记号。他还扎根荒无人烟的内蒙古戈壁,隐姓埋名,一呆就是三年。这还不算什么,当时的新中国什么都没有,更难的要数是日日夜夜的艰难、努力,换来的往往不是成功。而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是一次又一次的绝望,和他们不断的在烟雾、热浪中的经验复盘。靠着这样的毅力和奉献精神,他带领团队做成了——中国第一台复合固体火箭推进剂发动机。中国第一颗东方红一号卫星第三极火箭发动机。中国第一枚潜射战略导弹“巨浪一号”两级火箭发动机。中国第一颗科学实验卫星‘实践一号’火箭发动机。中国第一颗地球同步轨道通讯卫星的远地点火箭发动机……不少航天人在提到他的时候都会说一句:他为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就是杨南生,他是固体火箭队伍当之无愧的开拓者、领军人。
在那次采访前,没人会意识到,这俩人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和以往采访的你问我答不同的是,杨南生没有顺着她的思路回答问题,相反的,俩人聊诗歌、聊小说。因为保密制度的存在,张严平看不到他真实的样子,却看到了一个不同于以往严谨科学家的形象。两个小时的采访,她没拿到自己需要的素材,却感受到了灵魂的碰撞。她采访的这个人,太厉害了。简单概括:杨南生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开创者和组织者之一,当年为了让航天事业完成从0到1的起步,这群科学家们,都吃了不少的苦。为了设计中国第一枚发射卫星的运载火箭,杨南生从英国留学回来后,便一头扎了进去,在西苑旅行社里租了几个房间,趴在水泥地上设计图纸,用蜡烛和手电筒,开始了中国卫星、火箭雏形的设计与研制。为了设计探空火箭,为卫星上天探路,他带着科研团队扎根荒草丛生的发射场,那里的防空洞破败不堪,杨南生和科研人员连续十几天都要吃住在这里,大家挤在稻草铺成的地铺上,身上都生了疥疮。为了攻克固体燃料发动机这一世界难题,杨南生每夜挑灯苦读,灯光从来没在凌晨1点前熄灭过,829页的书,都有他用英文写下的长长短短的阅读笔记,和密密麻麻的各种记号。他还扎根荒无人烟的内蒙古戈壁,隐姓埋名,一呆就是三年。这还不算什么,当时的新中国什么都没有,更难的要数是日日夜夜的艰难、努力,换来的往往不是成功。而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是一次又一次的绝望,和他们不断的在烟雾、热浪中的经验复盘。靠着这样的毅力和奉献精神,他带领团队做成了——中国第一台复合固体火箭推进剂发动机。中国第一颗东方红一号卫星第三极火箭发动机。中国第一枚潜射战略导弹“巨浪一号”两级火箭发动机。中国第一颗科学实验卫星‘实践一号’火箭发动机。中国第一颗地球同步轨道通讯卫星的远地点火箭发动机……不少航天人在提到他的时候都会说一句:他为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就是杨南生,他是固体火箭队伍当之无愧的开拓者、领军人。 那年采访结束后,俩人建立起了连接,车马慢,书信长。他们用书信传递着幸福,也诉说着彼此的思念。聚少离多的日子,年龄上的差距,使得杨南生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情感。但人这一生,无论取得怎样的成就,无论身处怎样的位置,都难以逃脱爱情的魔爪。一封封的书信加深了俩人感情的同时,也让这样一段忘年之交变得更为厚重。那时候,俩人见面很少很少,只能趁着开大会的日子匆匆见上一面,又一次“两会”,杨南生在聊着各种趣事时,突然靠近张严平,在耳边轻声说了句“小平,我们结婚吧。”那一刻,俩人由朋友过渡为爱人。不用想都知道,结婚这个决定要遭到多少人的反对,尤其是女方的家人。毕竟,没人愿意将自己年轻的女儿嫁给年过花甲之人,即便他一身光环。张严平的父亲甚至下了通牒:“如果你要和这个人结婚,就永远别再进家门,这个家没有你这个女儿!”但这天下,很少有真的能拗得过儿女的父母,父母最终还是同意了。但跟随杨南生来到西安后,张严平才发现,杨南生一直过得很清贫,50多平米的小屋,水泥地,白灰墙,家具简陋破败。朋友来庆贺新婚时,用了四个字形容——家徒四壁。
那年采访结束后,俩人建立起了连接,车马慢,书信长。他们用书信传递着幸福,也诉说着彼此的思念。聚少离多的日子,年龄上的差距,使得杨南生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情感。但人这一生,无论取得怎样的成就,无论身处怎样的位置,都难以逃脱爱情的魔爪。一封封的书信加深了俩人感情的同时,也让这样一段忘年之交变得更为厚重。那时候,俩人见面很少很少,只能趁着开大会的日子匆匆见上一面,又一次“两会”,杨南生在聊着各种趣事时,突然靠近张严平,在耳边轻声说了句“小平,我们结婚吧。”那一刻,俩人由朋友过渡为爱人。不用想都知道,结婚这个决定要遭到多少人的反对,尤其是女方的家人。毕竟,没人愿意将自己年轻的女儿嫁给年过花甲之人,即便他一身光环。张严平的父亲甚至下了通牒:“如果你要和这个人结婚,就永远别再进家门,这个家没有你这个女儿!”但这天下,很少有真的能拗得过儿女的父母,父母最终还是同意了。但跟随杨南生来到西安后,张严平才发现,杨南生一直过得很清贫,50多平米的小屋,水泥地,白灰墙,家具简陋破败。朋友来庆贺新婚时,用了四个字形容——家徒四壁。还有一个摆在两个人面前更难的问题:两地分居。

这些年,为了工作,杨南生多次辗转,多次调动,从北京到上海,从上海到内蒙古,从内蒙古到陕西。
每次调动,他总是怀着一腔赤诚,不仅调离工作关系,还将户口和家人全部连根带走,他笃信“奉献乃生活的真正意义”,就这样抱着“这一辈子死在三线”的信念,继续着自己的航天事业。谁知道,这一次当他终于可以暂时放下工作为了家庭着想时,提交上去的调令却遭到了拒绝。不得已,俩人不得不继续着两地分居的生活,靠着书信传递思念。 那时候,张严平也养成了和杨南生一样的爱好——听音乐。虽然物质清贫,但杨南生的精神世界却极其丰富,他的小木橱里有摆放整齐的音乐磁带,他还整理了所有磁带音乐的目录,便于查找。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了他的晚年时期。杨南生的晚年时光,是在北京的航天大院里度过的。那时的条件并不算好,分给他们的房子建设时间早,总是漏水,修也修不好。房子也没有电梯,年岁渐大的杨南生出行十分不便。但即便如此,他也很少提条件,心甘情愿住在这个房子里,这个房子,也是他住过的最大的房子。哪怕退休之后很少有人前来看他,关照他的生活,即便他的组织关系不能调回北京,连看病都是个问题,他也从不抱怨。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继续着,杨南生也在一天天变老着。张严平回忆说,丈夫是在85岁那年突然变老的。先是上下楼梯不再方便,经常到二楼就要停下来歇一会。再是经常感冒,记忆力衰退,很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87岁那年冬夜里的一场急性胃溃疡,似乎加速了他的老去,尤其在之后,检查得知他得了腹主动脉瘤后,他变得更加虚弱了。紧急做完手术后,他虽然捡回来一条命,但身体却不复从前了,每次要去门诊时,都得依靠妻子搀扶着他才能走下楼梯。后来,他需要全天护理了,不得不住进了航天医院。再后来,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了,直到2013年,带着笑容溘然长逝。收拾他的遗物时,张严平打开了他曾经叮嘱过的一个黑色旧皮包,信中写着几句简短的话:一、在我病危之时,希望不要给我进行任何抢救。二、我死后希望不要举行任何“告别”或“追悼”仪式。三、我的遗体希望赠给医院利用,也可予以火化,而且不要保留骨灰。张严平不舍丈夫,便在杨南生上衣口袋里放了一张CD,那是他曾听过无数遍的《安魂曲》,想让他在黄泉路上有所陪伴。也遵从着丈夫的遗愿,将他的骨灰撒入大海,完成了这一场悲痛,却又带着宿命的送别。自那之后,她也陷入了漫长的治愈自己的时光,她所能想到的,是他的好,他的格局,他的淡然,和他这27年陪伴过程中的温情与浪漫。
那时候,张严平也养成了和杨南生一样的爱好——听音乐。虽然物质清贫,但杨南生的精神世界却极其丰富,他的小木橱里有摆放整齐的音乐磁带,他还整理了所有磁带音乐的目录,便于查找。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了他的晚年时期。杨南生的晚年时光,是在北京的航天大院里度过的。那时的条件并不算好,分给他们的房子建设时间早,总是漏水,修也修不好。房子也没有电梯,年岁渐大的杨南生出行十分不便。但即便如此,他也很少提条件,心甘情愿住在这个房子里,这个房子,也是他住过的最大的房子。哪怕退休之后很少有人前来看他,关照他的生活,即便他的组织关系不能调回北京,连看病都是个问题,他也从不抱怨。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继续着,杨南生也在一天天变老着。张严平回忆说,丈夫是在85岁那年突然变老的。先是上下楼梯不再方便,经常到二楼就要停下来歇一会。再是经常感冒,记忆力衰退,很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87岁那年冬夜里的一场急性胃溃疡,似乎加速了他的老去,尤其在之后,检查得知他得了腹主动脉瘤后,他变得更加虚弱了。紧急做完手术后,他虽然捡回来一条命,但身体却不复从前了,每次要去门诊时,都得依靠妻子搀扶着他才能走下楼梯。后来,他需要全天护理了,不得不住进了航天医院。再后来,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了,直到2013年,带着笑容溘然长逝。收拾他的遗物时,张严平打开了他曾经叮嘱过的一个黑色旧皮包,信中写着几句简短的话:一、在我病危之时,希望不要给我进行任何抢救。二、我死后希望不要举行任何“告别”或“追悼”仪式。三、我的遗体希望赠给医院利用,也可予以火化,而且不要保留骨灰。张严平不舍丈夫,便在杨南生上衣口袋里放了一张CD,那是他曾听过无数遍的《安魂曲》,想让他在黄泉路上有所陪伴。也遵从着丈夫的遗愿,将他的骨灰撒入大海,完成了这一场悲痛,却又带着宿命的送别。自那之后,她也陷入了漫长的治愈自己的时光,她所能想到的,是他的好,他的格局,他的淡然,和他这27年陪伴过程中的温情与浪漫。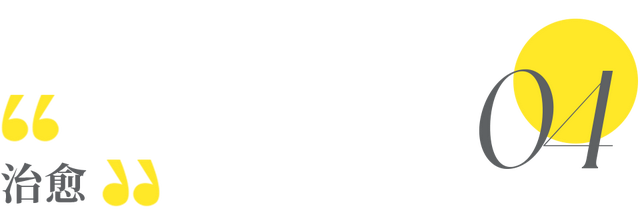 看过一句话:在这个世界上,会有千千万万的路通往一个终点,我们通常会选择最简单的,最有利益的,但总有些人,会选择最温情的那条。他们不会将一段关系变成谈判桌上需要加减筹码的存在,而是用真诚和关爱温暖着对方。在杨南生和张严平的婚姻生活中也是如此,他们彼此温暖,互相引领,相互治愈,学者和记者的爱情,虽然清贫,但清贫中总渗透着幸福。杨南生走后的日子,张严平一遍遍整理着他的过往,为他曾遭遇的痛苦感到痛心,为他日后没能安享的晚年生活感到不公。但看着看着,便释怀了。她明白了杨南生这一生所求的,并非功名利禄,而是内心安然,他虽然从不为自己争一句,但他优雅明亮,灿烂至死。他用尽一生为所追求的事业孜孜不倦,也用尽一生对所爱之人包容体谅。这又何尝不是那一辈科学家的情怀,是他们治愈与勉励人心的品格。如今,重读《君生我未生》这本书,我们感受的不仅是他们内心的丰盈,还有人格的高尚。原来,真的有人可以纯粹到这地步,他像是一盏明灯,点燃自己,照亮别人。他虽然物质清贫,却精神高尚。
看过一句话:在这个世界上,会有千千万万的路通往一个终点,我们通常会选择最简单的,最有利益的,但总有些人,会选择最温情的那条。他们不会将一段关系变成谈判桌上需要加减筹码的存在,而是用真诚和关爱温暖着对方。在杨南生和张严平的婚姻生活中也是如此,他们彼此温暖,互相引领,相互治愈,学者和记者的爱情,虽然清贫,但清贫中总渗透着幸福。杨南生走后的日子,张严平一遍遍整理着他的过往,为他曾遭遇的痛苦感到痛心,为他日后没能安享的晚年生活感到不公。但看着看着,便释怀了。她明白了杨南生这一生所求的,并非功名利禄,而是内心安然,他虽然从不为自己争一句,但他优雅明亮,灿烂至死。他用尽一生为所追求的事业孜孜不倦,也用尽一生对所爱之人包容体谅。这又何尝不是那一辈科学家的情怀,是他们治愈与勉励人心的品格。如今,重读《君生我未生》这本书,我们感受的不仅是他们内心的丰盈,还有人格的高尚。原来,真的有人可以纯粹到这地步,他像是一盏明灯,点燃自己,照亮别人。他虽然物质清贫,却精神高尚。在这个国庆,不妨为这些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们点个【在看】,他们高远的精神,终将影响我们到很久很久的以后。
作者 | 周美好,食一碗人间烟火,饮几杯人生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