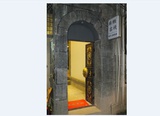东风解意,将三月的桃符换作四月的青笺。是谁在杨柳岸边系舟?系住了浮云游子的漂泊,又是谁在画桥西畔执伞?撑开了水墨江南的缱绻。雨丝斜,燕影翩,且看人间春宴正酣。
韶光温润,春潮漫过黛瓦白墙,檐角垂落的珠链叮咚成曲。我们踏着青石板上晕染的苔痕,把斑驳往事酿成杏花微雨。你折新柳作簪,我撷晨露为墨,在雾气氤氲的茶烟里,写就二十四番花信风的注脚。

细雨似琴弦,将光阴弹拨成连绵的平仄。你执伞立于藕花深处,素衣沾满草木清芬,恰似宣纸上晕开的淡墨。我们共读的旧书页里,夹着去年拾得的银杏,脉络里仍流淌着暮春的温度。竹影扫阶尘不动,茶烟透窗香愈幽,这般静好何须问今夕何年?
都说春色易老,我们却在藤蔓攀援的篱墙下,种下永不凋零的月光。当流萤点亮夜露,你以指尖轻叩陶埙,我应声拨动焦尾,宫商角徵羽里藏着整个盛唐的平仄。茶汤渐凉时,你用松针续火,火光映着眉间朱砂,恍若前世佛前未燃尽的灯芯。

世人都道春光短,我们偏要守着石臼捣花制香,看沉香屑与海棠瓣在时光里交融。你栽的忍冬藤已覆满东墙,我绣的并蒂莲正开在绢帕。待梅子黄时雨落满塘,便取坛中陈酿对酌,醉眼望去,满庭落花皆成双影。
此生何幸?能在春的褶皱里寻得相契的韵脚。不必羡瑶台仙侣,只消共守这方种满栀子的小院,任门外车马喧嚣,我们自在水绘的江南里,把朝云暮雨都读作聘书,将月落日升皆视为婚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