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楚把刚泡好的茶轻轻放在茶几上,茶水温热恰好,是她精心计算过的六十五度。这是褚永最喜欢的温度,不烫不凉,就像她曾经以为他们的婚姻会永远保持的温度。
"老公,喝茶。"她轻声说,声音里带着三个月来已经习惯的小心翼翼。
褚永头也不抬,手指在手机屏幕上快速滑动,仿佛那上面有什么比新婚妻子更重要的事情。茶在茶几上慢慢冷却,就像幼楚眼中微弱的光亮。
厨房里传来婆婆刻意压低的嗓音:"...当初就不该同意这门婚事,你看看现在..."公公的回应模糊不清,但那种不满的语气穿透墙壁,刺痛着幼楚的耳膜。
三个月前那场盛大婚礼上的欢笑仿佛还在耳边,四十桌宾客的祝福言犹在耳,谁能想到仅仅九十天后,这段婚姻就已经走到了悬崖边缘?

幼楚走进浴室,关上门,终于让忍了一整天的泪水无声滑落。镜子里的女人眼圈通红,曾经光彩照人的新娘如今憔悴得像朵枯萎的花。她恨恨地掐着自己的手臂,直到出现青紫的痕迹——都是她的错,全都是她的错。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幼楚一定会回到三年前的那个下午,当贺岩第一次笑着对她说"我们做好闺蜜吧"时,坚决地摇头拒绝。
贺岩是公司新来的设计师,阳光开朗,带着几分孩子气的顽皮。他们一见如故,从午餐搭档迅速升级为无话不谈的密友。公司同事都以为他们是一对,每次解释"我们只是朋友"时,幼楚心里都会泛起一丝微妙的得意——看,我有这么优秀的男性朋友,却只是纯粹友谊。
"你俩这样迟早出事。"闺蜜林悦曾警告过她,"男女之间哪有纯友谊?特别是他看你的眼神..."
幼楚当时不以为然地笑着打断:"你太老土了,现在什么年代了还这么想?"
后来她认识了褚永。与贺岩不同,褚永沉稳可靠,是理想的结婚对象。恋爱后,幼楚刻意减少了与贺岩的联系,却又不忍心完全断绝。她安慰自己:真正的友谊不该因为恋爱就结束,这说明她和贺岩的关系很纯粹。

那个周末的团建活动是噩梦的开始。二十多人去郊外农家乐,房间不够,幼楚主动让出床位睡在客厅沙发。半夜醒来时,贺岩的手已经伸进了她的睡衣。她惊慌地推开他,却因为怕吵醒别人而不敢大声斥责。第二天,贺岩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而她选择了沉默。
婚礼前夜,幼楚接到贺岩的电话。
"我明天可能不去了。"他的声音异常低沉。
"为什么?你是我最重要的朋友!"幼楚急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我怕我控制不住自己。"
幼楚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别闹了,你必须来。我让林悦看着你,不让你喝多。"
现在回想起来,那通电话分明是预警,而她愚蠢地忽视了。
婚礼当天,贺岩穿着一身不合时宜的黑色西装,在众多宾客中格外扎眼。幼楚忙着迎宾,只来得及对他匆匆一笑。当她挽着父亲的手臂走向褚永时,余光瞥见贺岩一杯接一杯地灌着白酒。
致辞环节,司仪刚宣布开始,贺岩就摇摇晃晃地冲上了台。幼楚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幼楚,"贺岩醉醺醺地对着话筒说,声音通过音响传遍整个宴会厅,"你老公知道咱俩睡过同一张沙发吗?"

时间仿佛凝固了。四百多人的宴会厅鸦雀无声,幼楚感到全身的血液都冲向了头部。她看见褚永的脸色由红变白,最后变成可怕的铁青。婆婆手中的酒杯啪地掉在地上,红酒像血一样溅开。
"不是那样的..."幼楚颤抖着嘴唇想解释,但巨大的耳鸣淹没了她自己的声音。贺岩被保安架走时还在大笑,那笑声像刀子一样剜着她的心。
婚宴勉强继续,但喜庆的气氛已经荡然无存。褚永整晚没再看她一眼,只在必要时刻露出机械的微笑。宾客们交头接耳,眼神中充满探究和八卦的兴奋。
"你和他到底怎么回事?"当晚,在新婚套房里,褚永终于爆发了,"全公司都知道你们的事,只有我被蒙在鼓里!"
幼楚哭着解释那只是一次意外,他们什么都没发生。但怀疑一旦生根,就像野草一样疯长。褚永查了她的手机,找到了那些她与贺岩的亲密合照——勾肩搭背的,头靠头的,每一张都像是情侣的合影。
"只是朋友会这样?"褚永把手机摔在床上,"你们女人总是说'只是朋友',却做着情侣才会做的事!"

回门那天,幼楚父母低声下气地向女婿道歉,保证女儿绝对清白。褚永勉强点头,但眼中的冰冷丝毫未减。回到自己家后,他直接搬到了客房。
"我们离婚吧。"晚饭时,褚永突然说。这是三个月来他第三次提出离婚。
幼楚的筷子掉在桌上,"为什么?我已经和贺岩断绝联系了,我什么都听你的..."
"不是贺岩的问题。"褚永疲惫地揉着太阳穴,"是我再也无法相信你了。每次看到你,我就会想起婚礼上所有人的眼神...我的父母,我的同事,他们都觉得我是个笑话。"
幼楚绝望地发现,无论她如何道歉、如何弥补,那天的耻辱已经深深刻在褚永心里。更可怕的是,她开始怀疑自己——如果当初能保持适当的距离,如果能早点意识到男女友谊的边界,如果能果断拒绝那次沙发事件...
浴室门外,婆婆故意提高声音:"离了就离了,反正还没孩子..."
幼楚打开水龙头,让水流声淹没一切。她看着镜中的自己,突然明白有些错误一旦犯下,就再也无法挽回。不是所有对不起都能换来没关系,有些裂痕,注定会伴随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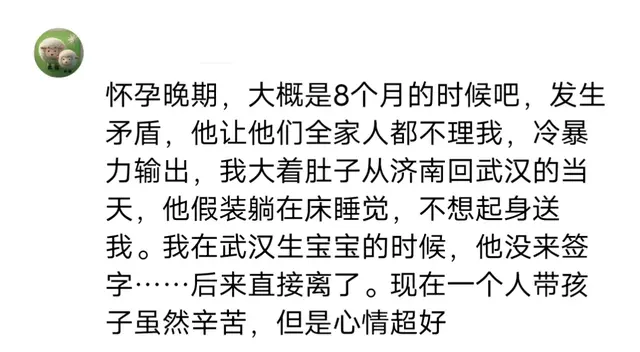

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