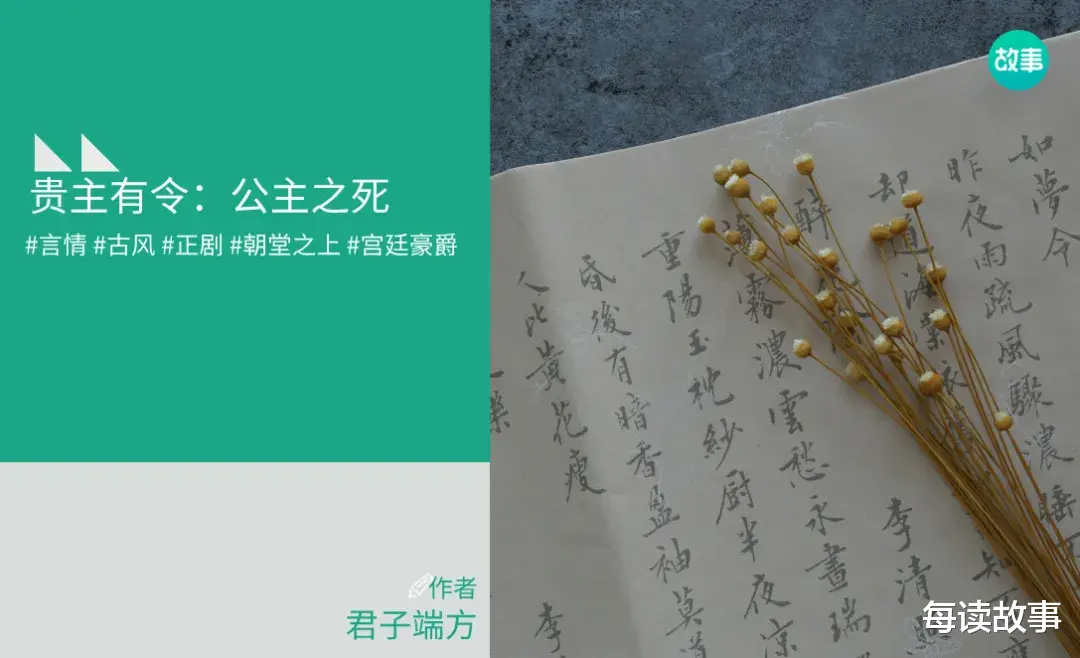
常人斗殴造成伤害,罚一百杖,而丈夫打伤妻子,只处罚八十大板。

冬日天气晴好,一只飞鸟停驻在昭阳殿的角脊上,怡然自得地梳理着羽毛。
风起时,檐下的九子金铃互相碰撞,发出清脆声响。
殿内,闻喜长公主正向沈贤妃哀哀哭求:“崔宣是个畜生!陛下再不准我和离,只怕我会被他折磨致死。阿姊,请你看在以往的情分上,再帮帮我吧。”
沈贤妃心疼落泪,只叹息道:“圣人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闻喜长公主还要再求,却见沈贤妃避开自己眼光,低低道:“我得了两幅雪庵仙人的画,已命人送去你府上。待你出宫后,可慢慢细赏。”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人家已在逐客了。
她不禁垂首,再抬头时满面泪痕,起身痴痴向外走去。
沈贤妃却又唤住她,“阿鸾——”
闻喜长公主回头,现出一张毫无血色的脸庞。
沈贤妃道:“你这样子如何见人?理妆后再走不迟。”
原来如此。
闻喜长公主逸出一抹苦笑,眸光里绝望之色更浓。
她好似并没有听到,适才沈贤妃说话时,白玉屏风后传来的小声惊呼。
等她离去,沈贤妃才又开口:“你们还不出来!”
窸窸窣窣声后,有两名宫装少女从屏风后徐徐走出。
前者一张端正的鹅蛋脸,皮肤明润,颊带绯色,为丹阳公主李令容。
后者凤眼波湛,鼻梁秀挺,观之气韵温和,乃临海公主李徽音。
沈贤妃先望向亲女,眉宇中略带不悦,“金枝玉叶,怎能有这种鬼祟做派。你一人淘气就罢了,怎么还带着你妹妹。”
丹阳公主撒娇道:“要不是皇妹的步摇簪勾住了我的头发,我才不会被您发现。”
她身后的临海公主闻言,抱愧似的一笑。
丹阳公主挨着母亲坐下,满不在乎道:“哪一次见闻喜姑姑,她都是满脸凄苦。天潢贵胄,做成她那样子真没出息。难怪父皇不喜欢她,若是喜欢,当初就不会为她选定如此凶狠的驸马。”
沈贤妃听着听着,眉尖便微微蹙起。
圣人心意岂是女儿能置喙的。
正欲开口训斥,临海公主含笑出声,“沈母妃,天色尚早,我还想出宫一趟,明日再来与你请安。”
沈贤妃自然准允。
待无外人时,沈贤妃拧一拧女儿面颊,叹道,“你说话这样冒失,可怎么是好。徽音比你年幼,为人处世是多么熨帖。”
丹阳公主下巴微扬,撒娇道:“她如何能与我相比,她没有娘亲依傍,又不得父皇宠爱。我却有您倚仗,还有舅舅与表兄。”
沈贤妃看一看神采奕奕的女儿,训斥的心思忽就熄了大半。
她轻抚女儿鬓发,“罢了。我还能留你多少日子。昨日圣人还问我,心中可有了中意的驸马人选。依我看,倒不如从你表兄里面择一个。知根知底,好过清河那样。”
提起清河公主,丹阳笑道:“二皇姐现在还躲在寺观里呢。大庭广众之下被人拒婚,什么脸面都没了,我要是她,也没有脸面再出来了。”
说话间,雕龙绘凤的公主步辇已停驻在含光门前,随侍的武婢向侍卫展示出宫玉牌。
尽管每半月,临海公主便会带着武婢从这里出宫,已成常例。
但,侍卫依然勘验过后才肯放人出宫。
一盏茶后,临海公主出现在醴泉坊。

绿釉莲花炉里静燃着天宝香。
陆载并不喜欢这种香气。
或许是因为此香于斋醮时常用,总能让他忆起母亲去世的场景。
不过,三日前嫁入陆氏的继母喜欢用这种香料。
他修养极好,即使站位离莲花炉颇近,但神色宁静如常。
继母杨氏手中拿着一个红彩玲珑球,正逗弄着膝上坐着的陆载小妹。
小妹倚在她怀里,犹豫了一下,才肯伸出手指去够,姿态怯怯。
如果父亲能看见这一幕,大概会对自己鸾胶再续的时间过晚而深以为憾。
妹妹的确需要一位得体的女眷进行教养。而继母杨氏门庭高贵,才学过人,更做过十五年的郢王正妃,在世家女眷中有着良好的经营。
辚辚车轮声从院内传来,打断他的思绪。
他看见继母杨氏的眼神一瞬霍然发亮,再顾不上小妹,起身向外走去。
陆载沿着杨氏动作看去,只见一个着联珠兽纹锦半臂、柿蒂绫长裙的年轻少女含笑立在门口,发上钗环明耀异常,与极盛容色相得益彰。
满屋人的视线纷纷汇于她身,她似浑然不觉,望向杨氏的眸光热烈,亲切道:“姨娘——”
杨氏眼底漾起柔色,将她上到主位,忙向众人引荐,原是圣人第四女,临海公主。
又按照行第一一介绍陆氏子弟。
陆载知道一些她的事。
这位公主的经历颇为曲折。她一出生便被抱至宫外,由郢王教养。直到郢王去世,郢王妃杨氏归于母家,圣人才拨下旨意,命沈贤妃抚养此女。
他没想到,临海公主与杨氏的感情竟然深厚到,杨氏再嫁以后,她依然会亲自探望。
轮到陆载小妹时,临海公主抚了抚她的额发,摘下一枝发饰为她戴上。钗首以金镶嵌玉片制成大蝴蝶,垂落四挂缀饰,蜂蝶金叶纷垂,精巧玲珑,十分可爱。
她神色温和,柔声道:“戴着玩吧。”
小妹下意识地看向自己兄长,临海公主的视线紧跟过来,二人目光相遇,陆载微微一笑。
眸如点漆,光彩熠熠。
公主并没有在正堂停留太久。
不多时,便与杨氏转入内室。
杨氏亲开妆奁,找出一条水晶珠串要替公主带上。
徽音摆手推却:“您留着吧。尚饰局并不曾短了我的供应,一枝簪子而已,难道我会吝啬?”
杨氏却不由分说,替她戴上,“你有是你的事,我偏要给你。”
珠串触及细腻肌肤,便是一阵微凉。
杨氏瞧着,忽然有些怔怔。
半晌才道:“我嫁给你伯父不到一月,就与他生了口角。他砸了暖砚,染了我一条绛紫长裙。我也没有输,泼了他一身热茶。这条珠串就是他给我的赔礼。”
十二岁以前,徽音一直生活在郢王府邸。郢王几乎是她父亲一样的角色,她坐正了身子,默默握住杨氏温热的手掌。
她们共同怀念着同一个人。
魂兮焉在,寂寞无音。
徽音在杨氏处待到日暮西沉,用罢晚膳,才欲启程归宫。
杨氏的心腹邓妈妈从外快步走入,向徽音匆匆一礼,俯身在杨氏耳边说些什么。
杨氏面色稍变,向徽音道:“闻喜长公主出事了。”

绣有瓜蔓叠叠纹样的帷帐内已空空如也。地上的脏污早被奴仆奋力擦拭干净。
门窗洞开,任冷风肆意灌入,血腥之气消失殆尽。
崔宣衣袍让风吹得紧紧贴在肥硕的身躯之上。
适才的画面走马灯一样在他眼前不断重演。
糊涂了,实在是糊涂了。他只是,只是喝了一点酒,醉醺醺回了公主府,看见那女人握着卷轴哭泣。
她哭泣时低着头,露出雪白的一段颈子。
他上前去,要同她亲热。她不肯,挣扎中天杆险些戳到自己眼睛。
他恼怒起来,便揪着她的头发给了她几拳。
她求饶了么,好像没有。而这更加激起了他的血性。
直到奴婢一声惊叫,他才发现,李鸢已躺在血泊之中。
后宫之内,椒风殿内红琉璃盘满盛夜光珠,照得光明如昼。太医鱼贯而入,沈贤妃亦带着丹阳、临海两位公主踏月而至。
椒风殿谢贵妃如今主理六宫。
她头戴凤凰金冠,冠顶正中立有一只展翅凤鸟,凤鸟双翅舒展,后尾上扬,口衔垂珠串。凤冠下是一张皮薄肉紧,笑时找不到一丝纹路的明艳脸庞。
自元贞皇后故去,便属谢贵妃与沈贤妃位份最高。
她看向来人,唇角略扬便算是笑了,“贤妃糊涂了。这种事情,怎好带未婚的小娘子来。”
沈贤妃着素衣,长发挽髻,只别了一只玉簪,自有一番温柔雅致。
她语气柔和,“到底是亲姑母,来看看也无妨。”
又含笑道:“听说清河还没有回来。未婚的小娘子,总在寺庙里待着,于名声恐怕有碍。妹妹,你说是不是?”
谢贵妃正欲还击,却见一盆血水端出,微蹙眉间。
丹阳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倒吸一口凉气,隔着衣袖,攥住了徽音的手腕。
不多时,擅长妇科的太医令来报,闻喜长公主小腹遭遇重击,落了两个月的孩子,此生恐难再孕。
殿内一时落针可闻。
谢贵妃命人禀报陛下,又看向沈贤妃,讥讽道:“我听说,长公主白日里去过昭阳殿?”
伴着她的发问,帷帐后传来女人隐忍而又绝望的哭声。
低低的,一声一声,抓在人的心上。

夜已深了,绮宴闪身进来。
她是昔年郢王为徽音挑选的武婢,即使提着沉重的食盒,走起路来依然轻巧无声。
绮宴动作极快,转眼间就从食盒里拿出一碟醋鱼、一碟雪藕、一碟酥油泡螺、一碟火腿干丝。还有蒸得黄澄澄的乳饼并一壶蜜饯梅汤。
她劝自家主子,“今晚您都没有用膳,好歹再吃些。”
徽音拣了一箸鱼肉,便又放下象牙小筷,向绮宴摇头,“我吃不下。”
胸口闷闷的。
白日在昭阳殿,她同丹阳藏在屏风后面,偷窥闻喜姑姑时就有这种感觉。
她看着殿内发生的一切,清晰听见自己心跳的响声,不忍浮上心头,又觉得这一幕异常可耻。
徽音垂眸,漆黑眼睫微颤,“我记得,闻喜姑姑曾送我一副棋具。”
绮宴比划了一下,帮她回忆,“是了,那年长公主同咱们郢王对弈,赢棋之后送给您的。裱锦围棋盘、缠枝莲纹的棋罐、青白二色的棋子。您不喜欢下棋,那套棋具咱们入宫时就没带来。”
“擅长下棋的人,会是愚笨之人么?你说,姑姑她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许是今夜值勤的宫婢偷了懒,不曾关窗,绮宴听完问话,只一瞬,便觉出了夜晚的寒凉。
她其实心中有答案,但,她不敢也不能直言。
徽音终于抬起脸来,用绮宴听惯了的平和语气说:“三皇姐说得没有错。如果父皇重视闻喜姑姑,崔宣不会这么对她。
“同样是长公主,闻喜姑姑的食邑不到修武姑姑的二分之一。腊日时,父皇赐遍百官与勋戚,闻喜姑姑的那份,在哪儿呢?”
听主子提起腊日赏赐一事,绮宴勉强一笑,安慰道:“贤妃娘娘不是说了么,内府办事不力,遗漏了也是有了。”
徽音摇头,“可是绮宴,只有我和闻喜姑姑没有得到赏赐。只有我们。”
她那双乌黑发亮的眼眸里,闪过一丝疑惧,“父皇也不喜欢我。如果他随便将我嫁给某个男人,像赏赐他一件礼物那样。闻喜姑姑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
绮宴心头一跳,这句话听来实在不吉。
她并不知道,自己侍奉的主子,已暗下某种决心。

有司以崔宣侍主无状为名,递上了一道参他的折子。
折子呈至思政殿的案桌,可陛下从未翻阅过。他召见大臣、批阅奏折、临幸嫔妃,甚至在清思院中打了一场马球,全然不将亲妹受辱的事放在心上。
在椒风殿里休养的长公主成了烫手山芋。
谢贵妃本就因女儿婚事不谐而愤愤不平,如今肝火更是旺盛,一时间,谢贵妃处的侍者人人自危,暗暗期盼着长公主能养好身体,早日回到自己的府邸。
长公主却始终缠绵病榻。
许多人都在心底想,何时才是了结。
直到冬至夜晚。
冬至夜是全年最长的一夜。徽音曾听杨氏说起,此夜做的梦最准,有预言之力。
在这个晚上,徽音梦见某处火光滔天,父皇站于烈火之外,神情冷漠,高声命令不许救火。
她跪在父皇身旁,死死拉住他的衣角,满脸是泪,不住哀求。
再醒来时,就听见了外间吵嚷声。她披衣下床,隔着窗棂隐隐见长廊外星火点点,心中升起不详预感。
尔后便听说了闻喜姑母的死讯。
她到底没能熬过这个冬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