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张隆溪教授出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书中第15章论及白话小说的发展,张教授说:Water Margin is also the first novel skillfully written in baihua or the vernacular spoken at the time rather than in wenyan or theical literary language, and in this regard, it marks the direction in which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especially the novel, was to develop and thus has a monumental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p.3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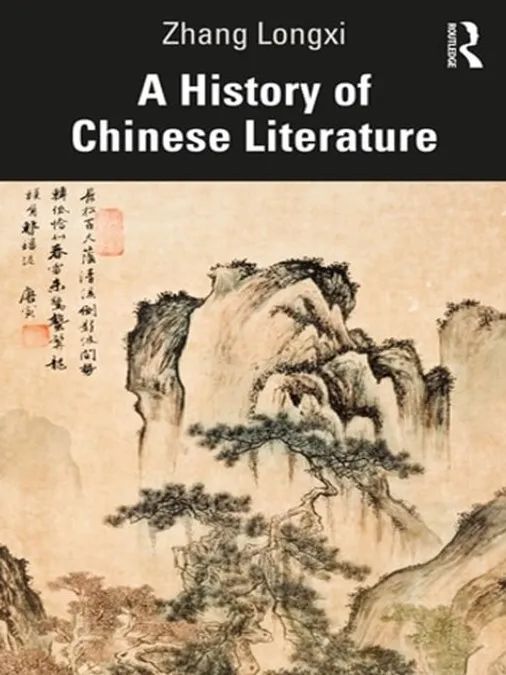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上面这引文中的Water Margin 指《水浒传》﹔baihua,就是“白话”;the first novel,意思是第一部小说;而it marks the direction……was to develop,意思是:用白话写成的杰作《水浒传》标志着中国通俗文学(小说)往后发展的方向。was to develop 说的是将来的事。
这个说法中的“第一”,表示《水浒传》之前还没有同类作品。值得特别注意的是the first novel skillfully written in baihua 之说和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所说大有出入。
本文讨论文、白问题和白话小说的语言特征,并检视《水浒传》在白话文学发展史上处于什么位置。

《京本忠义传》

按张教授的论断,《水浒传》得了个“第一”,在文学史上有monumental significance(里程碑式的重要性)。
《水浒传》有此重要性,关键是使用了the vernacular spoken写成的,足以垂范后世。按:vernacular是指the form of a language that a particular group of speakers use naturally, especially in informal situations,也就是不加文饰的口头话语。“vernacular”可以翻译为“白话”。
其实,在《水浒传》之前,白话文学已经有它自身的发展史。这方面,胡适(1891-1962)尤其关心(请看下一节)。
在张隆溪教授的书本中,the vernacular language始见于书中的Literature of the Yuan Dynasty(元代文学)部分,到第293页才首次出现。
然而,中国的白话文学,恐怕不是元朝才首次出现。
若论白话小说的滥殇,日本学者盐谷温(1878-1962)《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第六章第四节说明:宋代兴起的“诨词小说”用“俗语体”写成的,是真正意义的小说。(按: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大日本雄辩会,1919年,原为日文版;后来,书中内容被编译成《中国小说史略》。1949年,盐谷温将书中涉及小说的内容改名为《中国小说の研究》单独发刊。)

《中国文学概论讲话》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宋人“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之白话小说。
至于张教授声称《水浒传》是the first novel skillfully written in baihua, 这判断可以拿来和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说法相对照。
刘大杰指出:“(宋代小说的白话小说)白话文运用的技巧,已达到很成熟的阶段。”(《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二十二章,页353)。
刘大杰说宋代白话小说已经技巧成熟,而张隆溪教授认为元代才有第一本技巧高超(skillfully written)的长篇白话小说。
刘、张两家的说法,哪一种比较接近历史真相?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

提起“白话”,在中国文学史的编纂历史上有一本名著:《白话文学史》。
民国时期,胡适撰《白话文学史》(新月书店,1928年),此书追溯了中国历史上白话文学的发展轨迹。(附记:1927年出现胡适《国语文学史》一书。此书的底稿是胡适的授课讲义,未经胡适本人同意,被他人印成书。)
《白话文学史》之外,还有一本名气较逊的《新著国语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由凌独见编撰而成。

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
《新著国语文学史》的“国语”指什么?这本书的第二章说明:“历史教训我们文学要用白话做的才有生命,才有价值,才受世人的欢迎。社会上为什么爱看《水浒传》《红楼梦》呢?因为这两部小说是用白话来做的,……”(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页5)这种“用白话才有生命”的论调,和胡适之论十分相似。
胡适强调,白话文学是和古文文学、贵族文学相对的。他谈到汉代文学,说:“这(民间文学)里面写的环境,是和那庙堂文学不相宜的。这种环境里产生的文学自然是民间的白话文学。……从此以后,中国的文学便分出了两条路子:一条是那模仿的,沿袭的,没有生气的古文文学;一条是那自然的,活泼泼的,表现人生的白话文学。向来的文学史只认得那前一条路,不承认那后一条路。我们现在讲的是活文学史,是白话文学史,正是那后一条路。”(胡适《白话文学史》第二章)

《白话文学史》
这段话有两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自然是“白话”,其次则为“民间的”(实指平民),因为胡适认为平民多用白话来写作,他们的作品反映了真实的人生社会。
换言之,胡适声称,从汉朝开始,文学就分开了文、白两条路子。
后来,经顾颉刚研究,《诗经》被定性为“民间文学”的源头,而民间文学按胡适的“设定”,使用的大多是白话。因此,胡适所说的“从此以后”在年代方面可以向前挪到先秦。(《诗经》的作品中有多少是源自民歌、其口头性质如何,近人争议不休。参看陈致The Shaping of Book of Songs:From Ritualization to Secularization. Sankt Augustin, Germany: 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 2007.)
胡适整理出来的“两条路子”对后人有启发,以致于近人区分文、白两条线,分别写出了“白话小说史”、“文言小说史”方面的专书(例如:陈文新《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Judith T. Zeitlin, Historian of the Strange: Pu Songling and the Chinese Classical Tal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所谓the Chinese Classical Tale, 就是文言小说。

《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
在诗歌方面,也有古典诗史、白话诗话之别,例如:冯沅君、陆侃如撰《中国诗史》,不谈五四以后的新诗;云惟利撰《白话诗话》(香港山边社,1988年),只谈五四以后的新诗。
古典诗史中的本体(诗篇)到底有多文雅,不容易量度(文雅的程度难以精确检测并量化)。至于“白话诗”,一般专指五四提倡我手写我口以后所产生的散体诗(不拘平仄、长短),又称为“新诗”。
近百年“白话小说史”“白话诗”的观念,多少与胡适提倡白话文学有关连。

胡适《白话文学史》由第三章开始,多举白话文学作品为例,一直讨论到唐代的元稹、白居易而止。书中第六章、第七章分别举了文学史上很有名的作品为白话诗实例。

《国语文学史》
《白话文学史》第六章说:“《孔雀东南飞》在当日实在是一篇白话的长篇民歌……其时代自然在建安之后……”《白话文学史》第七章说:“北方的平民文学的最大杰作是《木兰辞》。”
不过,胡适认为现存的《木兰辞》也许不是原本的“平民”面目。他认为,《木兰辞》后来引起了文人的注意,不免有改削润色的地方。如中间“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便不像民间的作风,大概是文人改作的。
也许原文的中间有描写木兰的战功的一长段或几长段,文人嫌他拖沓,删去这一段,仅仅把“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两句总写木兰的跋涉;把“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两句总写他的战功;而文人手痒,忍不住又夹入这一联的词藻。
总之,“大概”、“也许”是胡适的推测之词,他的意思是:今存版本,可能经过文人动手修饰,将原本的平民文词加以文言化了。
胡适不排除“第一流文人”参与,因为白话只是工具,平民白话作者的思想实在不高明(陈国球等编《书写文学的过去:文学史的思考》麦田出版1997年,页63-64)。流传下来的作品“经后人修改,非本来面目”是文学史研究上的难题,美国学者Stephen Owen对此有颇多论析。

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
关于文士的角色,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指出,建安赋家以口语体作赋,应该是从民间语言吸收养分。程章灿列举了曹植《鹞雀赋》为典型例子。
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说:“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所以程章灿推测曹植从民间文学土壤中吸取营养是自觉的(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页52)。
总之,区分文、白“两条路子”,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不过,实况未必如胡适设想的那般文、白完全隔绝。这个问题,我们在下文讨论长篇小说时会再关注。
《白话文学史》第八章是“唐以前三百年中的文学趋势(300-600)”。胡适说:“他(陶潜)的言语却是民间的言语。在那诗体骈偶化的风气最盛的时代里竟会跳出一个白话诗人。”其实,陶潜也有《归去来兮辞》 、《闲情赋》等,根本不是用白话文写成(关于陶潜,请参看洪涛《陶渊明何时得遇知音?陶渊明如何成为“偏平人物”?(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五)》,载《古代小说网》2023年12月28日)。

陈岸峰《文学史的书写及其不满》
胡适又强行将唐朝李白、杜甫也收编为白话诗人。这就引来今世学者的质疑和严厉的批评(陈岸峰《文学史的书写及其不满》,香港中华书局2014年版,页52-53)。
胡适以白话文学为“活文学”,所以,唐代的律诗他是看不入眼的。他说:“唐朝的文学的真价值,真生命,不在苦心学阴铿、何逊,也不在什么师法苏李(苏武、李陵),力追建安,而在它能继续这五六百年的白话文学的趋势,充分承认乐府民歌的文学真价值,极力效法这五六百年的平民歌唱和这些平民歌唱所直接间接产生的活文学。"
简言之,白话和平民(民歌),是胡适这部《白话文学史》特别重视的作品。胡适相信白话文有助于社会改革。
近人看破胡适的手脚:先定目标,再四处搜罗合用的例证。文学史上一些不大合适的作品,也被他强行“收编”了(参看下文谈《三国演义》的部分)。

《二十世纪初中国白话文学研究及当代意义》

胡适对白话作品怎样开始崛兴,也有考研。《白话文学史》第九章和第十章是“佛教的翻译文学(上)(下)”。
《白话文学史》第九章强调佛经译文“不加藻饰,自有文学的意味,在那个文学僵化的时代里自然是新文学了。”胡适看到:六朝之后佛徒倾向使用“白话的讲说”。
胡适指出,三世纪晚期法护所译《修行地道经》中擎钵大臣的故事已经是用语不加藻饰(朱文华整理《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卷,页352)。

《胡适全集》
此外,大乘佛教《维摩诘经》“本是一部小说,富有文学趣味。”胡适认为鸠摩罗什在北方翻译《维摩诘经》所用的文体接近当日的白话(《胡适全集》第11卷,页356)。鸠摩罗什生于公元344年,逝于公元413年,活跃于东晋十六国时期。
在南方,佛驮跋陀罗(359-429)所译《华严经》的末篇占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华严经》中善财童子的经历被敷演成“一部长篇小说”(胡适的原话)。
《白话文学史》第十章主要讨论佛教俗歌对白话文学普及的影响。
胡适指出,五世纪以下,佛教徒倡行了三种宣传教旨的方法:(一)是经文的“转读”,(二)是“梵呗”的歌唱,(三)是“唱导”的制度。这三种宣传法门便是把佛教文学传到民间去的路子,也是产生民间佛教文学的来源。
简言之,佛教徒走的是通俗路线,多用白话来宣教。胡适说:“佛教中白话诗人的起来(梵志,寒山,拾得等)也许与佛教俗歌有关系。”(《白话文学史》,远流出版1986年版,页195)。

《五四复调:疑古思潮与白话文学史的建构》

白话文成为中国法定书面语的过程漫长。古代没有录音器,没有留下声音档案,所以现在我们只能从书面文字略窥古代口语的情况。
语言学家朱庆之(1956- )的研究揭示:初期(二世纪开始)佛经汉译本中的白话成份甚高。
唐朝禅宗大师的语录用白话载录,遂开出白话文学的新叶。笔者所撰《佛教跨文化传播的个案研究》(2020年),书中有一章讨论《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唐代的镇州在今日的河北。

洪涛著《佛教跨文化传播的个案研究》
《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简称为《临济录》,是唐代禅宗高僧临济义玄的言行记录,由临济义玄的弟子三圣慧然编集而成。这本《临济录》的“语录”,学者认为口语化的程度相当高(龚隽《禅史钩沉: 以问题为中心的思想史论述》三联书店,2006年,页304)。
例如临济禅师面对佛徒信众说:“道流!佛法无用功处,秖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着衣、吃饭、困来即卧……。”(《汉文大藏经》T47n1985_001_[0498a16])。
唐宋禅宗许多语录保存至今。《禅宗语录辑要》说明:“语录……用的都是当时、当地的方言口语,因而较为活泼自然。这种既口语化、又具抑扬顿挫节奏感形式的语录,后来被宋明理学家所沿用。”(《禅宗语录辑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这些语录固然不是文学作品,但是,接近口语的文字记录和小故事有赖佛徒佛寺保存了下来,我们得以略窥唐宋白话的使用状况。

《佛教汉语研究》
此外,美国学者梅维恒(Victor Mair)撰文讨论佛教与东亚白话文的兴起(收入朱庆之编《佛教汉语研究》,页358-409)。这篇论文原刊于1994年,名为“Buddhism and the Rise of the Written Vernacular in East Asia:the Making of National Languages,”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53 no.3)。
张隆溪教授的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也有佛经翻译一节,题为Early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Texts (p.48)。
可惜张教授没有申说佛经翻译怎样在语言上(白话)左右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因此,Early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Texts一节,给人孤零零的感觉(按:Early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Texts这一节主要谈支娄迦谶和安世高译经;汉明帝故事和白马寺译场之事。见p.48-49)。

《汉译佛典文体及其影响研究》

梅维恒认为白话是“未加修饰的话语”。他关注佛徒使用白话的情况,指出:“晚唐时期白话文兴起”(朱庆之编《佛教汉语研究》第376页,引梅祖麟说)。到了宋代,白话文已经在非主流社会阶层中得到认可(第364页),就连新儒学也使用通俗的口语化的语录来传播学说。
笔者手头上有一本宋朝黄士毅编《朱子语类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朱子语类》这本书用口语式的文体记述了朱熹师徒之间的对答,使朱熹精深细致的观点变得平易实用。学人在师徒一问一答之间,尽得朱子学说的精华。

黄士毅编《朱子语类汇校・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版。
据胡适《朱子语类的历史》一文,南宋后期人黎靖德在江西建昌刻的《朱子语类大全》成于1270年,比元朝建立(1271 年)还早一年。
梅维恒又说,慧皎用“国语”指称一个地区的语言。直至清末,“国语”常指非汉族群体的语言(例如拓跋文、鲜卑文。参看《隋书・经籍志》:“又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
梅维恒撰有专书讨论vernacular fiction的兴起:T'ang Transformation Texts:A Study of the Buddhist Contribution to the Rise of Vernacular Fiction and Drama i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1989. 二十多年后,这本书有中译本:《唐代变文: 佛教对中国白话小说及戏曲产生的贡献之研究》(2011年)。梅维恒显然认为佛教的宣讲有更多的“口头话语”因素,成了白说小说的先驱。

梅维恒主编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02年版。
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02年) 第一章就是“语言和文字”。由此可见,梅维恒编文学史首先就重视书写所用的文字,点出“言、文有别”的现象。此书指出,佛教入华之前,白话的使用甚少(p.30)。

佛教不是促进白话运用的唯一因素,蒙元统治的需要是另一种“外来因素”。
元朝的皇帝入主中土,为了有效统治,不得不重视自身的汉语和汉文化教育,尤其是元朝的统治者必须了解中土的儒家和历史故事。
可是,蒙古人的汉语言、汉文化水平一般而言都不甚高,因此,汉语文言写成的典籍显得艰深难懂,这语文障碍使蒙古人对汉文化难以快速掌握,因此,蒙古统治阶层很需要简要方便的汉文化知识读本,也需要易于理解的表述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元代出现了不少汉文经史典籍的节略本,以及附有蒙式汉语的白话本。

郑镇孙《直说通略》(影钞明成化刊本 )
郑镇孙《直说通略》以《资治通鉴》为基础,编写时尝试做到通俗浅易,在内容方面间有虚构发挥,例如,子婴投降刘邦一节:“子婴素车白马,颈上系着传国宝,出路傍投降。”这应该是依据《史记·高祖本纪》或者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九“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而改写。
《资治通鉴》的“组”是什么?一般人未必知道。
其实,“组”就是“印绶”,而“印绶”就是系在印环印鼻上的丝绳。郑镇孙弃“组”“印绶”不用,以白话“颈上系着传国宝”来传意,读者看了自然是比较容易明白。
关于白话小说,美国学者Patrick Hanan的著作《中国白话小说史》值得我们参考。《中国白话小说史》原为英语著作,名为The Chinese Vernacular Story(1981)。这本书讨论的是Story, 翻译成中文虽是“小说”,但是此书只涉及短篇小说,不讨论中国白话长篇小说。

美国学者Patrick Hanan(韩南)的英文版中国白话小说史
Hanan指出,现存早期白话短篇小说有三十四篇,其中十四篇为A组,“大多数可确定为元代”(页30)。换言之,在《水浒传》之前或形成期,有其他白话小说存在。
元代的《直说通略》(郑镇孙)、《经筵讲义》(吴澄)都是历史题材的书面白话著述。《直说通略》这本书,胡适也有提及,他在《国语文学史》(1927年)称《直说通略》是“白话的历史演义”、“历史小说”(《国语文学史》第三编,页199)。

文言、白话,是泾渭分明的?
——《三国演义》的半文半白
文言文学和白话文学是泾渭分明的吗?
梅维恒(Victor Mair)说:“文言文传统的作者和白话文传统的作者都很少真正使用这两种书面汉语的纯粹形式(例如曾经有过的话)。”梅维恒的意思是,有些作品大体上是以“半文半白”为特征,文白混杂,每篇的文言成分和白话成分所占比例各不相同。
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序》说:“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三国之盛衰治乱,人物之出处臧否,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矣。”这几句简评,主要是谈小说家所用的语言和人物形象。

上海古籍出版社版《三国志通俗演义》
在张教授的书中我们也能看到近似的说法:Heused aical language similar to the historical records,but integrated with elements of vernacular expressions,and thus created a language that is elegant,lively,vivid,concise,and effective,capable of portraying an impressive imageor creating an atmosphere in a few well-chosen words.(Zhang,p.307)张教授似乎判定:《三国演义》主要是用 aical language写成的。
张教授没有举实例,我们只好自行探讨。
《三国演义》第一回描写:时巨鹿郡有兄弟三人:一名张角,一名张宝,一名张梁。那张角本是个不第秀才。因入山采药,遇一老人,碧眼童颜,手执藜杖,唤角至一洞中,以天书三卷授之,曰:“此名太平要术。汝得之,当代天宣化,普救世人;若萌异心,必获恶报。”角拜问姓名。老人曰:“吾乃南华老仙也。”(罗贯中《三国演义》,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2017年版,页2)。

《醉耕堂刊毛宗岗评本三国演义》
碧眼老人如果说:“我就是南华老仙”,那就比较接近现在的口语体(白话)。书中的所载“吾乃……也”,还是带了文言色彩。
不过,同一回也有“蛇不见了”这样的大白话:“建宁二年四月望日,帝御温德殿。方升座,殿角狂风骤起,只见一条大青蛇,从梁上飞将下来,蟠于椅上。帝惊倒,左右急救入宫,百官俱奔避。须臾,蛇不见了。忽然大雷大雨,加以冰雹,落到半夜方止,坏却房屋无数。”(毛评本,见罗贯中《三国演义》,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1页)。
“蛇不见了”是白话。可是,这四字前面的“须臾”在当今的口语白话中极少使用。“须臾 + 蛇不见了”连用,益见其语体混杂。嘉靖本作“须臾不见”,没有语体混杂。
那么,像《三国演义》这样的小说,是白话小说吗?
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承认《三国演义》是用“浅近的文言”写成的(《新著国语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页240)。然而,他认为,《三国演义》这种古文和白话的过渡文字不妨收入国语文学史,当成白话文学的代表之一。
总之“过渡文字”也被凌独见纳入“国语文学”之中。

《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
谢旡量(1884—1964)《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认为《三国演义》不是贵族文学而是平民文学,而且以描写平民革命理想为旨归,人物形象鲜明,因此,不仅不应受到忽视和否定,相反应推尊其作者罗贯中为元朝小说界的大文豪(谢旡量《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商务印书馆,1923年,页13)。胡适这批人,将“平民”、“民间”和白话文学捆绑在一起。科考失败做不成达官贵人的平民,也读过四书五经,这样的平民就一定不会写古文吗?
胡适将《三国演义》当成是白话小说吗?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文学》一文中推许“言之无文,行之最远”的《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胡适《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页152)。
所谓“无文”,就是“不用文言”“少文饰”。可见《三国演义》也被胡适“收编”入他的白话文学之中,只是他不怎么谈《三国演义》的文句实例。
到了1922年5月,胡适还写了一篇《三国志演义・序》,将《三国志演义》也当成推广白话的“可用之兵”。
谢旡量说过“书中本是文言很多”(谢无量《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商务印书馆,1923年,页29),不过,他推重平民文学,这一点,谢旡量和胡适没有两样。

《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

这一节,我们尝试讨论张教授所说的the vernacular spoken,其中,spoken专指“口说”、“说话”。我们摘录小说中的对话来分析。
《三国演义》第九十三回“武乡侯骂死王朗”,孔明骂王朗:“吾以为汉朝大老元臣,必有高论,岂期出此鄙言! 吾有一言,诸军静听:昔桓、灵之世,汉统陵替,宦官酿祸;国乱岁凶,四方扰攘。黄巾之后,董卓、傕、汜等接踵而起,迁劫汉帝,残暴生灵。因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朝;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社稷丘墟,苍生涂炭。吾素知汝所行: 世居东海之滨,初举孝廉入仕。理合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期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天下之人,愿食汝肉!今幸天意不绝炎汉,昭烈皇帝继统西川。吾今奉嗣君之旨,兴师讨贼。汝既为谄谀之臣,只可潜身缩首,苟图衣食;安敢在行伍之前,妄称天数耶!皓首匹夫!苍髯老贼!汝即日将归于九泉之下,何面目见二十四帝乎!老贼速退!可叫反臣与吾共决胜负!”(周文业主编《三国志演义文史对照本‧下》,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页554。)

《三国志演义》文史对照本
这段武侯痛骂王朗的话(spoken by Zhuge Liang),颇有文言色彩:第一,用“吾”“汝”而不是白话中常见的“我”“你”。
第二,有骈文的特征,例如:“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朝;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理合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期反助逆贼,同谋篡位?”
第三,四字词特别多,一段话中“汉统陵替,宦官酿祸;国乱岁凶,四方扰攘 ”等四字词竟有二十多个,似是小说家在书斋中事先预备好的,不大像临阵时的即场发挥。
中央电视台1994年版电视剧《三国演义》中,小说原有的“吾”“汝”被改为“我”“你”(由唐国强饰演的诸葛亮说出),不过,诸葛亮的话中仍然保留了大部分骈俪句式和四字词。
到了2010年,安徽卫视出品《三国》,上引骂王朗的“台词”被大幅度简化,例如“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以致狼心狗行之辈汹汹当朝,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使社稷变为丘墟,苍生饱受涂炭之苦”被删汰。此外,陆毅饰演的诸葛亮说出“我”“你”:“你,王朗,世受大汉国恩,举孝廉入士,要是还有半点良心,就该匡君辅国,除贼兴汉,而你,却贪图官位,助贼篡逆,……你有何颜面大汉二十四先帝呀,老贼速退,杀你,污我刀耳。”

《三国演义》电视剧海报
总之,《三国演义》电视剧中的诸葛亮骂王朗的话,比小说中的原话浅白。安徽卫视的《三国》在这方面的改编(浅白化)尤其明显。也就是说,诸葛亮的话,语域上更加贴近现今的口语。
毛评本有凡例,其中一条说到:“俗本之乎者也等字,大半龃龉不通;又词语冗长,每多复沓处。今悉依古本改正。”所谓“之乎者也”,常见于文言文的语尾,用“之乎者也”是文言文的特征之一。毛宗岗将这些文言特征清除掉一些。
参照毛宗岗的说法,《三国演义》的“古本”是比较“文”的。毛本《三国演义》自然比较适合胡适、凌独见、谢旡量采用(也许是“挪用”/appropriation?)。

《三国演义诠释史研究》,郭素媛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上一节,我们讨论《三国演义》的“半文半白”。凌独见、谢无量、胡适却将《三国演义》拨归白话小说。
张隆溪教授认为《三国演义》用的是 aical language, 没有将它归入白话小说。胡适为了建立“新的传统”,需要多举“白话文学”的例证,尽力让白话之例压过文言之例,甚至将文言文学说成是死文学。胡适这样做,显然是过犹不及,所以被后来的学者抨击。
实际上,就以白话小说来说,不见得文、白是对峙的。相反,白话小说中也有文言的片段。张教授说 Water Margin is……written in baihua or the vernacular spoken, 没有举出实例。
我们试看《水浒传》开头怎样写。《水浒传》第一回 (《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页14),作者这样描写洪太尉揭开大青石板时,那锁魔地穴:

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本《水浒传》
天摧地塌,岳撼山崩。钱塘江上,潮头浪拥出海门来;泰华山头,巨灵神一劈山峰碎。共工奋怒,去盔撞倒了不周山;力士施威,飞锤击碎了始皇辇。
一风憾折千竿竹,十万军中半夜雷。
上面这段话,不但有骈偶句式,还使用了典故(共工撞不周山、刺秦王故事),这些都不合胡适“须是白话”的口味。
笔者再引一段口头语,和上例对照一下。
《水浒传》写鲁达在酒家和兄弟会面。酒保道:“官人要甚东西?吩咐买来。”鲁达道:“洒家要甚么?你也须认的洒家,却恁地教甚么人在间壁吱吱的哭,搅俺弟兄们吃酒。洒家须不曾少了你酒钱!”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全传》,四川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页49)。

上海人民出版社版《水浒全传》
鲁达所说的“俺”在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区口语中很常见,是第一人称代词。至于“洒家”,也指“我”,常见于北方方言和白话文。“恁地”,意思是这般、这样。
可见,《水浒传》虽是白话小说,但是书中有文有白。
《水浒传》第八十二回“梁山泊分金大买市 宋公明全伙受招安”记有道君皇帝的诏书:“朕自即位以来,用仁义以治天下,行礼乐以变海内,公赏罚以定干戈。求贤之心未尝少怠,爱民之心未尝少洽。博施济众,欲与天地均同;体道行仁,咸使黎民蒙庇。遐迩赤子,咸知朕心。切念宋江、卢俊义等,素怀忠义,不施暴虐。归顺之心已久,报效之志凛然。虽犯罪恶,各有所由。察其情恳,深可悯怜。朕今特差殿前太尉宿元景,赍捧诏书,亲到梁山水泊,将宋江等大小人员所犯罪恶尽行赦免。给降金牌三十六面,红锦三十六匹,赐与宋江等上头领;银牌七十二面,绿锦七十二匹,赐与宋江部下头目。赦书到日,莫负朕心,早早归降,必当重用。故兹诏敕,想宜悉知。”(《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123页)。
上引“博施济众,欲与天地均同;体道行仁,咸使黎民蒙庇”是四六言骈偶句;“故兹诏敕,想宜悉知”也不是白话。

《容与堂本水浒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可见白话小说的作者(可能是施耐庵、罗贯中)不像胡适所主张的那般只使用白话文。在一些严肃的语境,小说家就使用合适的文言,配合语域所需。
胡适如果按照自己的主张写白话小说,那么,宋朝小说中的角色势必人人说白话,难有语域的变化,结果是书中角色的谈吐缺乏变化、千人一面。
下面,我们再举另一本白话小说名著为例。
《红楼梦》第十八回,贾政对女儿元春(元妃)说:“臣,草芥寒门,鸠群鸦属之中,岂意得征凤鸾之瑞。今贵人上锡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远德钟于一人,幸及政夫妇。且今上启天地生物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旷恩,虽肝脑涂地,臣子岂能报效万一!惟朝干夕惕,忠于厥职外,愿吾君万寿千秋,乃天下苍生之同幸也。贵妃切勿以政夫妇残犁〔年〕为念,懑愤金怀,更祈自加珍爱,惟业业兢兢,勤慎肃恭以侍上殿,庶不负上体贴眷爱如此之隆恩也。”(《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页234)。
上面这段父亲(贾政)对女儿说的话甚是文雅,绝非平日会说的白话,而《红楼梦》却是白话小说。语境所迫,贾政说话不能显得太过俗白。这个案例也说明,白话小说的作者没有(像胡适主张那样)只用白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红楼梦》
贾政面对儿子贾宝玉时,也能说出“无知的畜生!你能知道几个古人,能记得几首旧诗?”这样的大白话。
同一个贾政,说话可文可白,这是因为小说家深谙小说之道,视乎语境,或文或白,不一而足。贾政与贾府清客们的对话中有较浓的文言色彩。
依笔者看,《红楼梦》不是普通的“平民”就能写得出来的。《白话文学史》的“白话”配“平民”之说,绝非无懈可击的。
胡适有时候不得不采用松散的定义,认为:适当地使用文言,多方融合之下,可成“国语的文学”。

本文无意否定《水浒传》在白话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笔者只想强调:《水浒传》之前的白话作品(尤其是唐代变文和宋代白话小说、《朱子语类》等)在白话撰述史上的角色也应该得到重视。
张隆溪教授说《水浒传》marks the direction in which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especially the novel, was to develop, 这句话给人的印象是:自从元末《水浒传》成书,小说的发展方向就定了下来。
然而,据Victor Mair的研究, 比《水浒传》更早二百年以上的唐代变文已经是中国白话小说及戏曲的滥觞。

梅维恒《唐代变文:佛教对中国白话小说及戏曲产生的贡献之研究》
胡适《白话文学史》比Victor Mair更加努力证明白话文学古已有之。胡适将白话作品说成是活的,文言作品被打成“死文学”。胡适的目的是:白话作品应该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
白话文学是文学的主流还是旁支,我们渐且不争辩,无论如何,《白话文学史》为我提供了若干实例,证明:白话文学,古已有之,不必等到元末的《水浒传》。
如果单论白话小说的发展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指出:宋代白话小说的技巧已经成熟。不必等到元末的《水浒传》。
笔者认为,胡适在他编纂的文学史中营造“文”“白”对峙的局面,心中先存有他一己的目的。他为了推广白话的运用,多多少少有“编造历史”的嫌疑,以“新撰的历史”来树立新的民族传统。白话文学在胡适书里,有较强的“工具色彩”:他心中有更大的目的,就是文学革命、改造社会。
文白对峙,大概是胡适心中的“必要的对峙”。他站在白话一方,为白话文学争“正统”。胡适谈的是白话文学,不是专论白话小说(当然他实际上很倚重白话小说来推广白话,例如为多本亚东版的排印本小说作序)。

张中行《文言和白话》,中华书局2012年版。
然而,民国以前的白话小说作家,没有“文言是死文学”的观念。“死文学”是胡适抹黑敌对面(文言文学)的标签。
白话小说,在语体方面不是铁板一块。在应当使用文雅话语的语境,白话小说的作者会使用文言文。《三国演义》毛评本的内文比起嘉靖本(或古本)更接近口语白话,如果毛宗岗是据嘉靖本而改用白话,那么毛氏的改动也是一种广义的翻译。
此外,社会上有各阶层,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教育程度不一,不会只有一个语域,其间必有雅语、俗语之分。关于这点,请读者参看笔者的文章The Language Register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David Hawkes’s The Story of the Stone and their Relation with English Literary Conventions,载《广译:语言、文学、与文化翻译》第13期2016年9月(这篇英文文章有中文题目:《霍译本红楼梦的语域变幅、社群分野与英语文学成规》)。读者也可以参看洪涛《女体和国族: 从红楼梦翻译看跨文化移殖与学术知识障》(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

洪涛《女体和国族:从红楼梦翻译看跨文化移殖与学术知识障》
文言和白话,宛如同一光谱的两端,其中间地带不容易截然切分(张中行《文言和白话》,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十四章)。胡适“用白话”的主张,在他的年代大概是很有意义的,问题是胡适有时候为了“扶持”白话而在所撰文学史中强行收编之事,这现象已经引起今人严厉的抨击。
到了二十一世纪,用白话来和文言文学分庭抗礼的历史意义已经减少(二十一世纪初反而兴起“国学热”,人们要回归传统文化)。现今,写白话诗的人很多,而旧体诗词的生命力仍然不弱。
胡适编纂白话文学史书是为了推广白话,他的做法有可议之处,但是撇开其“编史”的瑕疵,《白话文学史》反映了一个事实:白话作品例如民歌之类,各朝代都出现过。
在《水浒传》诞生之前,白话文学早已存在,这点是没法否定的。

胡适反对文言文学之外,也反对现代人用典(胡适《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然而,1952年12月26日,胡适回到永福国小故居,在故居前种下一棵小榕树苗,并写下“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墨宝送给学校珍藏(胡明《胡适传论・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87﹔李敖《胡适研究》,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年版,页204)。

《胡适传论》
“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出自《诗经·小雅·小弁》,不是口头白话。“维”是句首语气词,引出主语。“止”是句末语气词。“维”“止”这样用,和白话没有关系。
胡适自己为什么不用白话题写呢?大概也是因为这场合如果使用白话显得他不学无文。
题“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和白话小说中出现文言文,有很大差别吗?没有。可见,将运用白话绝对化,实行起来往往是有困难的。
附记一: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
胡适《白话文学史》 (1928年) 只写到唐代为止(其末章第十六章是“元稹 白居易”),始终没有完成文学史下卷。
郑振铎1938 年出版的《中国俗文学史》直接以“俗文学”为中心,从先秦歌谣讲到清代民歌。

《中国俗文学史》
附记二: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提及胡适对白话文学的看法(页5)。《新著国语文学史》的出版早过胡适的《国语文学史》和《白话文学史》。这年代先后的问题令笔者略感惊讶。
后来,笔者在戴燕教授的著作中了解到事情的来龙去脉。据说,凌独见上过1921年胡适在教育部所授“国语文学史”的课(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页59)。
《文学史的权力》第六章还讨论国语的基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值得一读。

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附记三:Bo vs Bai: 读音转为笔录 (关于Li Bo)Li Bo 见于张隆溪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就是汉语世界中的“李白”。然而,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一般使用汉语拼音来拼写汉语世界中的人物姓名。“白”拼音为Bai。
书本上出现Li Bo,是失校之例吗?
这Li Bo,在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出现165次。它在张教授书中不是罕见的人名。
2024年12月,笔者偶然看到张隆溪用普通话主讲“2021人文讲座(一):经典与经典的稳定性”的录影片段, 注意到 1:41:14张教授说: Du Fu Li Bo。
张教授将“李白”念成Li Bo,其故安在?

《李白研究论著目录》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书面纸本上的Li Bo, 看来不是源于编者的疏失, 而是教授将自己的Li Bo读音(白话)转为笔录而成。书中“白话”“白朴”“白先勇”的“白”则拼写为“Bai”。
笔者揣测,张隆溪教授将“李白”念成Li Bo, 也许是有理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