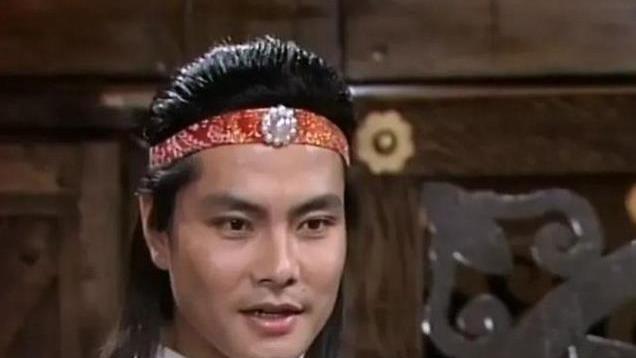当我们提到六和寺的时候,就必然会联想到两个人,一个是在那里坐化的花和尚鲁智深,另一个则是在那里终老的行者武松。要知道,这鲁智深和武松可不是虚构出来的人物哦,在宋朝的史料当中,他们可都是确确实实存在过的呢。

您知道吗?在《水浒传》这部名著里,鲁智深和武松这两位梁山好汉,可是把六和寺当作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一站呢,这里面其实是有着很深的用意的哦。话说后来,明末有一位既搞史学研究又擅长文学创作的张岱,他特意跑到六和寺去做了一番实地考察呢。这一考察可就发现了个有意思的事儿,按照实际情况来看,鲁智深根本就不太可能是在这六和寺里坐化的,武松同样也不太可能真的就在这儿一直终老下去。那他们后来到底怎么着了呢?很有可能,这两人是一块儿偷偷溜掉啦。
史学家蔡东藩先生在其所著的《宋史通俗演义》里,提到了自己以一个当地人的身份,去拜谒武松、时迁以及张顺相关遗迹的经历。蔡东藩先生生长在古越这片地方,这里距离杭州还不到一百里地呢。由于距离比较近,他就时常会到杭州去走动。而每到杭州,他便会去寻访当地的一些古迹。这一寻访可就有了不少发现。在杭州城内呢,真真切切地存在着一座张顺祠,据说张顺还曾被封作涌金门内的土地神呢。再看城外,那里有着一座时迁庙。还有哦,在美丽的西子湖边,还能看到武松墓呢。蔡东藩先生由此觉得,这些遗迹既然存在于此,想必是有其依据的,应该不会是毫无根据的空传之事。
大家知道吗,杭州有个武松墓哦,它可不是在人们可能以为的六和寺那里呢,而是在西泠桥边哟。有意思的是,在距离武松墓大概五十米的地方,埋葬着的是南北朝时期南齐的一位名媛,她就是苏小小呢。
在西泠桥边这块地方,有个挺有意思的情况呢,义士武松和名女苏小小居然是比邻而居的状态,这事儿乍一听,还真能算得上是一段挺特别的佳话啦。可谁能想到,就在2014年的时候,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武松的墓碑还有苏小小的墓碑,竟然在半夜里被一个人给涂上了红油漆呢。后来,这个人被抓住了,经过审讯呢,发现一个挺让人意外的情况,这人似乎也不姓西门。

先暂且不去说为什么会有人在武松的墓碑上做出喷漆泄愤这样的事情,现在呢,咱们还是把话题转回来,聊一聊鲁智深以及武松他们二人最后的归宿情况吧。
在《水浒》原著里面,鲁智深最终“坐化”这件事呢,那可真是疑团重重。仔细琢磨琢磨,就会发现很有可能这背后是有着一番精心谋划的呢。很让人怀疑,这说不定就是武松精心设计出来的一个计划,而且呢,这个计划还得到了宋江的点头认可哦。然后呢,大家就这么联合起来,共同上演了这么一出类似金蝉脱壳般的大戏。
话说鲁智深随着梁山好汉一同去征讨方腊,待到凯旋归来之时,鲁智深心里其实早就有了一番盘算,他料到自己这一回京城啊,恐怕是没什么好下场的。为啥这么说呢?原来啊,那太尉高俅有个堂弟,高俅呢,把这堂弟收养过来当成自己的儿子了,为的就是能延续自家的香火,让家族有个后啊。可谁能想到呢,后来鲁智深和一帮泼皮在相国寺的时候,闹了那么一出事儿,生生就把高俅堂弟传宗接代的念想给断了。你想啊,这等断人后嗣的大仇,那高俅怎么可能就这么算了呢,肯定得找机会报复鲁智深。所以鲁智深心里明白着呢,这一回京,怕是要面临高俅的刁难喽。
鲁智深心里头啊,压根就不乐意招安这事儿。可你知道吗,当初跟他一起在二龙山落草为寇的那些弟兄们,除了武松是个例外,其他人好像对当官都挺感兴趣的。就说那青面兽杨志吧,还有金眼彪施恩,这俩家伙对那官帽可是稀罕得很呐。鲁智深呢,他虽然自己不情愿,可也不能就这么扫了弟兄们的兴,而且他跟这些弟兄们感情深厚,哪舍得就这么和他们分开呢?所以没办法,就只能硬着头皮陪着弟兄们再接着走这招安的路喽,就当是再陪他们走一程吧。

在经历了与辽国的战事,以及平定田虎、王庆、方腊这一系列的重大战役之后啊,曾经二龙山的那七位好兄弟,到最后就只剩下鲁智深和武松两人了。这几场战役下来,那可真是无比惨烈,身边的兄弟们一个个离去,他们俩心里别提多不是滋味儿了。也许是见惯了战场上的生死离别,又或许是对这世间的纷争感到厌倦了吧,鲁智深和武松此刻都觉得自己已经没什么可牵挂的了。而且啊,经历了这么多,他们的心也变得如同死灰一般,对那些功名利禄再也提不起什么兴趣。所以呢,当朝廷提出让他们进京接受封赏的时候,鲁智深和武松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们不想再卷入那些官场的是是非非当中,只想着能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过往后的日子。
武松之所以拒绝受封,那是有一定缘由的。他说道:“小弟我如今已经落下了残疾,实在是不愿意再前往京城去朝见天子啦。我打算把身边所有的金银赏赐,全部都捐纳给这六和寺,作为陪堂公用的费用。我就安安心心地在这儿当个清闲道人,这样的日子对我来说就已经非常好了。哥哥啊,您在造册登记的时候,可千万别把小弟我写进要进京的名单里。”
在武松对宋江说出某些话之前,鲁智深其实就已经“坐化”了。而在鲁智深坐化之前呢,他还曾和宋江有过一场十分推心置腹的交谈。鲁智深当时是这么说的:“我这心里啊,早就如同死灰一般了,压根就不想去当官儿,就只盼着能找到一个清净的地方,好让自己能安安稳稳地生活下去,这对我来说就足够啦。(哪怕宋江都许诺了让他去当住持、僧首呢)可这些我统统都不想要啊,要那么多也没什么用处。到最后能落得个完整的尸首,那就算是很不错的了。”

宋江这么做,很明显是在帮鲁智深把真相给遮掩起来呢。为啥这么说呢?你想啊,童贯回去以后那是会跟高俅说这事儿的。而那些僧众呢,他们得了钱财之后,自然也就不会到处去多嘴多舌说些什么了。这么一来,那个龛子里到底装的是谁,可就只有为数不多的那么几个人才知道啦。
半壶老酒始终持有这样一种看法,那就是鲁智深的坐化之事并非真实发生的情况。甚至鲁智深临终时所留下的那些“遗言”,在半壶老酒看来,极有可能是别人事先就已经写好的。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大家可以想想啊,鲁智深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得呢。就像当初他打死镇关西之后出逃,走到十字街头,那里贴着通缉他的榜文,当时的情况是“鲁达却不识字,只听得众人读道”,从这就可以明显看出他是不识字的。既然如此,他又怎么可能写出那种充满高深意味的偈语呢?这实在是让人觉得不太可能。
在水浒原著当中啊,有一处描写特别有意思呢。你瞧啊,宋公明也就是宋江啦,他接到了相关的禀报之后呢,就赶忙带着众多的头领匆匆赶过去查看情况。等他们到了地方一看,只见鲁智深已经自己安安静静地坐在那禅椅之上了,而且一动也不动的,就好像定格在那个画面里似的呢。
大家知道唐僧吧,他有个本事呢,就是能打坐,而且据说厉害得很,能够连着好几天都不吃东西,身体也一动不动的。再说说鲁智深,他这人呢,向来是不怎么喜欢打坐这种事儿的。不过呢,要是到了特别紧要的关头,让他强忍着不动,坚持个一两个时辰,那也还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哦。

鲁智深并非是毫无动静、如同死寂一般的状态,而是处于一种相对静止但实际仍有其存在意义的情形。当时那个在径山大肆点火的大惠禅师,或许心里也明白,那龛子里所装着的并非真正意义上已经消逝的鲁智深呢。毕竟禅师后来还说出了这样的话语:“忽地随潮归去,果然无处跟寻。”意思大概就是鲁智深仿佛一下子随着潮水消逝而去了,可真到要去寻找其踪迹的时候,却又哪里都找寻不到。这也从侧面让人感觉,禅师对于鲁智深的那种特殊状态,似乎有着别样的认知呢。
大惠禅师心里清楚得很呐,鲁智深压根就没在那龛子里呢。而宋江随后所做的一系列安排,张叔夜和童贯那可都是瞧不见的哦。当时是这么个情况,鲁智深随身带着的那些多余的衣钵,还有金银财物啥的,另外再加上各位官员所布施的东西呢,全部都给收纳到六和寺里头去啦,这些财物就都作为六和寺常住的公用之物啦。
鲁智深平日里所用的那些常用物品,就这么都留在六和寺啦,就连他那杆水磨浑铁禅杖也没带走呢。也搞不清楚这些东西最后是会给谁拿去“常住公用”,反正就都搁在那儿了。
话说鲁智深坐化之后,武松就也不打算走了,据说他俩都留在了六和寺呢。这里可就有个关键问题啦。施耐庵写《水浒传》的时候,按理对方腊和宋江的那些事迹得是比较了解的。而且呢,更应该清楚这么个情况,那就是在当时,实际上所谓的六和寺是不存在的哦。这可是经过张岱考察之后得出来的结果呢。在宋朝的时候,就只有六和塔,根本就没有六和寺。那六和塔还被方腊给烧成了一片白地啦,啥都没剩下。所以呢,说鲁智深是在六和寺坐化的,这事儿压根就是虚构的,根本就没这回事儿,完全是子虚乌有嘛。
张岱在其作品《西湖残梦》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在宋开宝三年的时候,智觉禅师主持修建了一座塔,修建这座塔的目的是为了镇住江潮。这座塔有九级,高度达到了五十余丈,它高高地耸立着,直插云霄,显得十分突兀,横跨在陆地与河流之上。当时那些正在江面上行驶的海船,都是把这座塔上的灯光当作前行的向导呢。不过呢,到了宣和年间,这座塔在方腊之乱中遭到了毁坏。后来到了绍兴二十三年,有一位名叫智昙的僧人对它进行了改造,改造之后变成了七级。

这么来讲吧,当梁山军成功征讨方腊胜利归来的时候,那六和塔早就已经消失得干干净净了,既然六和塔都没了,那与之相关的六和寺自然也是还没有修建起来的哦。大家看施耐庵在作品里所描写的情节,他写鲁智深是在这个根本就不存在的六和寺里坐化的呢。这其实就是在暗暗地给读者透露一个信息,那就是鲁智深的坐化很可能是假的哦。说不定鲁大侠早就想好了办法,来了个金蝉脱壳之计呢,然后就和武松一道,自由自在地在江湖上逍遥快活啦。您想啊,连六和塔都已经不存在了,那谁又能在那个地方找到鲁智深和武松的踪迹,可不就任由他们在江湖逍遥去咯。
后来,有一座是以塔来命名而修建的六和寺。到了明末的时候呢,在这六和寺还留存着一首诗,这首诗是万历年间考中进士、担任过四川参议的李流芳所写的哦。而张岱呢,还特意把这首诗收录到了《西湖残梦》这本书里面呢。这首诗是这样写的:“人生能有多少时光,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江山依旧还是原来的模样呢。再次来到这里,还能和友人相互携手同游,这种快乐简直都没法用言语来形容啦。就好像把自己置身在一幅美丽的画图之中,在这样的情境下,哪里还会想着要回去呢。接下来应该是要去寻找云栖这个地方了,只是云栖它又在那渺茫遥远的什么地方。”
李流芳所写的这首诗,难道不恰恰就是鲁智深、武松那逍遥自在归宿的真实呈现吗?可以说,从这首诗里,仿佛能看到鲁智深、武松他们那种最终寻得逍遥去处的情景被生动地描绘了出来,它可不就是对鲁智深和武松逍遥归宿最为贴切的一种真实写照嘛。
要知道,明末史学家所做的那些考察结果,子就写出了那种含义高深的偈语来,这是不是有点奇怪?还有那在江湖上叱咤风云、向来风风火火的武松呢,却忽然就静下了心来,这转变也挺让人琢磨的呢。再看宋江,他把装着鲁智深遗体的龛子一下子就给烧掉了,可却把鲁智深的那些东西都给留下来了。这么多让人觉得可疑的地方,它们是不是都在隐隐地暗示着我们,鲁智深其实并没有真的坐化呢?这可真值得大家好好去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