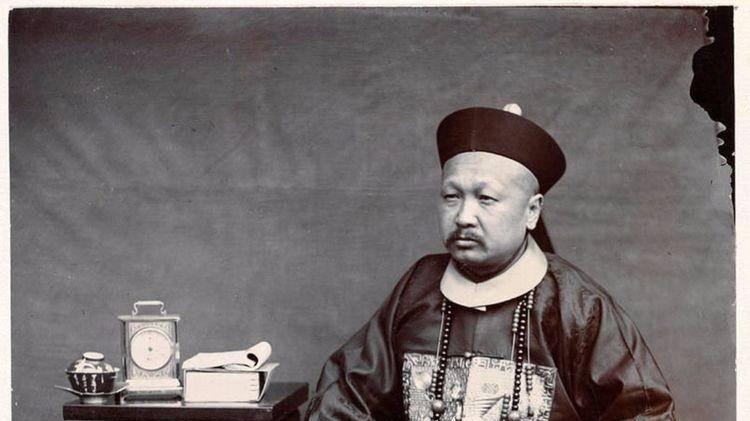嘉庆十一年九月,依循旧例,吏部文选司开展月选。此次月选,重点为知县职位的选拔,共计三个空缺,分别为江苏震泽县知县、浙江德清县知县及云南永善县知县。

在此次月选之中,经严格筛查,符合候补知县条件者共计七十九人。令人诧异的是,在这众多候选者里,竟有七十八人不约而同地将震泽与德清二县列为首选。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仅有欧阳儁一人,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永善县。
这一情形犹如在高考志愿填报时,志愿一经确定便无法更改。在此背景下,于此次月选之中,七十八位候补官员里,七十六人注定会遭淘汰。究其缘由,乃是名额有限且选择既定难以变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永善县仅有欧阳儁一人报名,如此一来,从逻辑和实际情况推断,欧阳儁无疑会被授予实缺。
嘉庆帝获悉此情形后,龙颜震怒。在他看来,一众出身进士的候补官员,于职位选择上竟存趋利避害之举,遂降旨予以严词斥责。与此同时,嘉庆帝召见欧阳儁,明言若其于永善任内政绩斐然,三年期满,必将擢升其官职。
为何部分人员宁愿落选,也拒绝前往永善任职?究其根源,永善县地理位置偏远,经济发展滞后,治理难度颇大。此前数任知县,皆因无法足额征收赋税,而遭受革职或降级之惩处。

该年岁末十月之际,欧阳儁动身前往履职之地。彼时,一众同年纷纷前来送行。在众人看来,欧阳儁此举实乃行事莽撞、决策失当,其仕途之路恐将因之而戛然而止。
欧阳儁对其中的艰难并非浑然不觉。然而,究竟是何种缘由致使他采取与常规相悖的举动?这一问题的根源,需追溯至清代的官缺制度。
【知县缺之肥瘦】
在清代,全国县域数量达一千三百有余。彼时,朝廷基于多元因素考量,将众多县份划分为四类,即最要缺、要缺、中缺与简缺。各类县缺在官员任命方面,皆有其独特的条件与标准。
欧阳儁初涉仕途,依制仅能于中缺与简缺官职中遴选。江苏震泽、浙江德清及云南永善皆位列中缺范畴。就“缺分”理论而言,此三县在这一方面并无实质性差异。
然而,云南作为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的省份,其下辖的永善县更是以贫困著称。该地不仅交通条件极为落后,且当地民风呈现出粗犷不羁之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震泽与德清两县,虽在行政区划中同属中缺等级,却地处江苏与浙江区域,乃久负盛名的富庶之地。

故而,即便同属简缺、中缺范畴,亦存在细致的层级划分。古人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仕途之中,官员们普遍期望前往经济富庶之地任职。毕竟,在此类地区,即便仕途晋升之路受阻,却也能在经济收益层面获得一定保障。
因知县职位所涉利益与发展空间存在差异,朝中具人脉资源、家族具备相应条件的进士群体,对偏远地区的知县任职机会往往持有轻视态度。他们更倾向于耗费一两年乃至数年时间耐心等待,以谋求一个契合自身期望的任职地域。
此情形易衍生一弊端,即资源丰沛之地各方竞相逐利,而资源匮乏之处则乏人问津。鉴于此,朝廷旋即推出另一举措,将全国知县职位依地域特性,细分为腹缺、边缺、苗疆缺、沿海缺、沿江缺等类别。
为激励众多候补官员前往边陲偏远省份履职,朝廷颁行相应奖励举措。其明确规定,于中原腹心等内地省份,知县的任职期限设定为五年;而在地处偏远之省份,知县的任期则缩短为三年。

以震泽县为实例,依据吏部所颁明确政令,知县任职需满三年方可进行职位“转调”,满五年方具备“升迁”资格。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永善县知县仅需三年即可获得升迁机会。然而,无论职位的转调抑或升迁,均以通过吏部严格考核为必要前提。
即便如此,仍有诸多人士对前往边疆省份履职心存抵触。究其实质,乃是难以承受边疆地区艰苦的工作与生活条件。
【欧阳儁的情况比较特殊】
欧阳儁,于清嘉庆七年荣登三甲进士之列。其出身寒门,家境清寒。直至四十一岁时,方获实授永善知县之职。彼时,以世俗标准观之,作为高龄进士,他尚无房产、座驾与积蓄。
在京处于候补状态的数年间,他的境遇颇为窘迫,经济上深陷债务泥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多数同年,不仅年龄较他为轻,且家境更为优渥。这些同年于京城官场中积极运作,通过各种钻营打点手段,不少人已谋得实职。

欧阳儁处境颇为窘迫,于朝堂之上并无深厚人脉根基,且囊中羞涩,实无财力用以打点疏通。若贸然参与震泽、德清知县之职位角逐,如同他人一般,其落选结局殆无悬念。如此一来,他必将继续于吏部闲置,在漫长岁月中无奈等待,恐需历经数年之久。
功夫不负苦心人,欧阳儁所择之路经时间验证颇为正确。于永善县履职期满三载,凭借自身能力与积累的政绩,他获擢升为知州。此后,欧阳儁持续进取,凭借出色的治理才能,仕途更进一步,升任知府。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与他同时获选担任震泽、德清知县的两位官员,在其仕途中,自始至终未获擢升,于知县之位上徘徊辗转。
实际上,就晋升层面而言,地处偏远省份的知县具备显著优势。
官员能否获得晋升,与吏部所实施的考核机制紧密相连。以知县这一官职为例,若于大计考核中获评“卓异”等级,通常便具备了升迁的契机。

然而,卓异这一评定的获取颇具难度,具体而言,每省获此评定的名额不足十人。相较之下,在多数情形下,知县职位的晋升,往往需依据“循资历序”的原则,以此判定其是否具备升迁资格。
在无法详尽洞悉官员才能及政绩的情形下,论资排辈不失为一种极为简捷且行之有效的方式。对于吏部而言,凭借资历,官员状况即可清晰呈现,无需再进行繁杂的考察评估。
从历史层面审视,于清代,多数知县在政绩建树方面能力有限,且缺乏足够资源用以对上级进行疏通运作。故而,他们往往安于本职,在职位上以熬资历的方式延续任期。
在论资排辈的晋升体系下,地处边疆省份的知县在资历积累方面独具优势。相较于其他地区,其任职期限显著更短,部分地区仅需两年,多数也仅需三年,便具备了升迁资格。
在吏部的晋升考量体系中,若两位知县同时被列入晋升名录,且在出身背景、任职资历以及施政业绩等方面呈现出相近态势时,地处偏远区域的知县将被赋予优先晋升权。此举措体现了朝廷对身处艰苦地域履职官员的政策倾斜,旨在通过这种方式,激励官员投身于条件欠佳地区的治理工作。否则,此类地区恐将面临无人赴任的困境。

欧阳儁的仕途晋升堪称此类典型案例。其获擢升为知州,得益于在永善县的任职履历。之后,欧阳儁又升任知府,彼时,他展现出颇为自得之态。据闻,其同年对此评价,称其似有“憨人得福”之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