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林硕(国家博物馆)
首发湖南政协《文史博览》
作为晚清重臣,曾国藩赖以成名的支柱是其亲手缔造的湘军。极盛之时,清政府半数督抚尽属湘军中人,可谓权倾朝野。
湘军最初脱胎于湘乡士绅成立的地方团练武装——湘勇,仅仅是当时湖南众多团练之一,与浏阳的“浏勇”、宝庆的“宝勇”、新宁的“楚勇”相比亦无过人之处。
不过,善于把握时机的曾国藩却巧妙地通过援赣之役、移驻衡阳、创立水师三个步骤,成功让湘勇摆脱了内无财政专项拨款,外无离境征战之权的旧时团练模式,将其锻造为晚清烜赫一时的军事集团——湘军。

一、墨絰从戎,组建团练
作为湘军领袖的曾国藩出任过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成为当之无愧的疆臣之首,可他早年却是不折不扣的京官。
早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屡试不第的曾国藩终于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入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历任翰林院检讨、翰林院待讲、日讲起居注官、文渊阁直阁事、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等职。因其克己奉公,十年十迁。

至咸丰二年(1852年)已经坐到了署理吏部左侍郎的位置上,成为名副其实的二品大员。从曾国藩在京期间的履历簿上看,无疑是标准的文官。那么,缘何他会投笔从戎,到地方去督办团练呢?
事情还得从咸丰二年六月谈起。彼时,刚刚履新半年的曾侍郎奉旨前往江西主持乡试,岂料途中传来母亲亡故的噩耗,转往桑梓奔丧。按照清代礼制:在职官员无论身居何种职位,如遇父母辞世都要离任返乡,守孝三年。在此期间,在籍官员不得干预地方事务。
然而,是年十二月,咸丰皇帝一道“帮办团练”的上谕,打破了曾国藩的赋闲生活。此时的湘省已是狼烟四起。早在咸丰元年(1851年),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领导了举世震惊的“金田起义”。次年,起义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离桂入湘,进围长沙。

为增强军力守备省城,朝廷下令启用守丧在籍的曾国藩为“帮办团练大臣”。墨絰从戎的曾侍郎,集合兄弟国华、国荃、国葆,发动同乡罗泽南、王錱、李续宾等人的力量,组建起湘乡勇(简称湘勇)。
从严格意义上说:此时的“湘勇”还是在省内打转,不允许跨省作战,也没有固定的给养来源,尚未摆脱团练武装的范畴,与后来的“湘军”不可同日而语。
乾隆、嘉庆时期,清政府为了镇压五省白莲教大起义,也大力推行团练,结堡自守。待到太平天国起义之时,咸丰皇帝又搬出祖宗的老办法。不过,朝廷在利用汉族乡绅组建武装的同时,又对其甚为防备,在诸多方面加以限制。

一方面,严格划定作战任务及区域。通常情况下,团练的活动范围都是在各自州、县守备,无朝廷允许“不得远近征调”;除非出现太平军围攻长沙这类危机的情况,才会让乡勇汇聚省城协防。
另一方面,财政方面,不食于官。筹办团练的经费主要依靠乡绅捐输银钱、百姓按亩摊派,以及在各地设卡向过往行商征收厘金(商业税)等手段。
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基本上不会给予团练任何经济支持。因为在他们眼中,团练即“民团”,不隶属于政府,与正规军存在很大差距。
二、出师援赣 跨省作战
眼见自己辛苦组建的武装力量被视为不入流的“杂牌军”,曾国藩犹如芒刺在背。如何能将湘乡勇打造成一支可以实现自己“匡时救世”之梦的武装,成为他亟待解决的难题。

咸丰三年(1853),一封求援信给曾国藩带来了新的契机。修书之人是曾国藩的老战友——楚勇创办者江忠源。江氏兴办团练比曾国藩、罗泽南早很多: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他就创建地方武装,镇压了雷再浩领导的“新宁青莲教起义”。
曾国藩之所以对江忠源的历史耳熟能详,除了二人是旧相识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咸丰元年,江忠源兄弟组建的楚勇被朝廷赋予了“跨省作战”之权,出湘入桂,在广州副都统索佳·乌兰泰麾下作战;这让曾侍郎艳羡不已。
如今,江忠源被困南昌,倒是给曾国藩送来了机会。既然朝廷可以在危急之时派遣楚勇离湘赴桂,湘勇同样可以如法炮制,以援赣为由,突破团练守土作战的限制。

于是,成竹在胸的曾侍郎提笔上书:事急从权,恳请皇上参照“楚勇援桂”的前例,准许湘勇出省作战,以解南昌之围。不久,咸丰皇帝准其所请。
接获讯息,曾国藩不禁大喜过望:既然官方允许了自己的援赣作战计划,等于默认湘勇超越了普通的地方团练,迈出了向“从湘勇到湘军”的第一步,性质开始发生变化。
鉴于湖南境内仍有小股太平军活动,曾国藩决定坐镇省内,只派遣罗泽南、李续宾、郭嵩焘等人率一千湘勇东征驰援,同行的还有江忠源四弟姜忠淑麾下的两千楚勇。

初次离省作战的湘勇在太平军水、陆合攻之下损兵折将,而两千楚勇更是全军覆没。侥幸突入南昌城的郭嵩焘目睹太平军水师的威力,痛定思痛,建议江忠源考虑筹建水师。江氏一方面上表朝廷,请求各省广设船厂,筹备水师;另一方面,也将郭的“水师之议”分享给其他统兵将领,这其中就包括曾国藩。
三、移驻衡阳 一石三鸟
对于曾侍郎而言,“水师之议”虽好,却一时无暇兼顾。他正在进行从湘勇到湘军的第二部——移驻衡阳。
很多人认为:曾国藩离开长沙,是由于他与时任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南提督鲍起豹不合所致,实则不然。

如果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曾国藩留馆授职翰林院检讨步入仕途算起,到咸丰三年之时,他已经历了长达十四年的宦海沉浮,分别任职于礼、兵、工、刑、吏五部。对于如何与同僚相处的为官之道,曾侍郎自是烂熟于胸,游刃有余。否则,他根本不可能十年十迁,从一介七品小官擢升至当朝二品。
有鉴于此,即使曾国藩与湖南官场的某些官员之间产生过些许不愉快,也断不会有坊间流传的那样严重。既然如此,那么“兵围又一村事件”有事怎么发生的呢?

其实,事件起因比较简单。自太平军围困长沙起,驻防各地的绿营、团练纷纷云集省城协防;其中最彪悍者,当属来自湘西凤凰的镇筸兵。
咸丰三年八月,镇筸兵自恃“绿营精锐”的身份,与团丁发生冲突。曾国藩力挺自己人,导致镇筸兵围其驻地“又一村”,双方发生冲突。然而,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巡抚骆秉章和提督鲍起豹是幕后黑手。
这次兵祸虽属偶然,但事后曾国藩将驻地移往衡阳确系事实。坊间传言:曾氏以在籍侍郎的身份督办团练,没有摆正自身的位置,受到湘省官场排挤,难以在长沙立足,故南下避之。
诚然,曾国藩确实带领着湘勇离开了省城,但“兵围又一村事件”仅仅是偶发事件。他的离开完全是顺水推舟,因势利导,籍此为由离开长沙。
驻扎衡阳实则是曾国藩“一石三鸟”之计。

首先,借兵祸之事,在朝野上下营造出自己和湘勇备受欺压、排挤的假象,以便咸丰皇帝能够同意他脱离地方官员的监视。
其次,趁机来至湘南,彻底摆脱了盘踞省城的各种力量对湘勇进行的掣肘与刁难。曾国藩和未来的湘军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大本营。
最后,有利于可以改变世人心中湘勇依附八旗、绿营的附属形象。虽然三者分属不同的管理系统,但在不明就里的百姓眼中,与正规军同城驻扎的湘勇,不过是前者的附庸而已。
四、筹建水师 初历战阵
尽管在曾侍郎的运筹帷幄之下,湘勇拥有了跨省作战之权,拥有了自己的大本营衡阳,但粮饷始终是高悬在曾国藩头顶的紧箍咒。

早在咸丰二年,曾国藩就试图借增援长沙之机,奏请改团丁为“官勇”,以便“粮饷取诸公家”,实际是向朝廷索要钱粮。虽然咸丰诏准,可三湘大地绝非“湘勇”一家之天下,各地团练都希望从省府财政中分取杯羹,故湘勇军饷仍旧捉襟见肘。
恰在曾国藩一筹莫展之际,长江战局发生了新的变化。咸丰三年九月,太平军的西征部队水陆并发,兵临武昌城下。

清政府调湘勇武装北上救援。然而,接到谕旨的曾国藩却按兵不动,而是提笔写下了《暂缓赴鄂并请筹备战船折》和《请截留粤饷筹备炮船片》。
他在奏折中陈情:太平军水师“以舟楫为剿穴,以掳掠为生涯。千舸百艘,游弈往来,长江千里,任其横行”,清军无可奈何,此皆“舟师未备”之故。是故,朝廷欲在湖广、江南等河湖水网密集之地击败太平军,必须拨款大力组建水师,以改变两湖地方“无一舟可为战舰,无一卒习于水师”的窘境。因此欲救援湖北,恳请先筹建水师。

朝廷很快准其所请:从湘省财政支出三万两经费建造战船、招募水勇。考虑到湖南藩库所拨相较于筹备炮船之费,“实属不敷供支”。事急从权,咸丰皇帝还同意曾国藩可以截留“粤饷”(由广东运往江南大营的军费)四万两,甚至还赋予他动用“漕米”之权。
资财虽已齐备,可欲筹备水师,靠塔齐布、李续宾等陆战悍将实难成事。究竟谁可担此重任呢?
恰在此时,有人向曾国藩举荐:如今衡阳就有一位人才,姓彭名玉麟,字雪琴,军旅世家出身,深谙《公瑾水战法》,足堪此任。只是他现为母亲守孝在籍,且对官场心灰意冷,抱定了“平生最薄封侯愿,愿与梅花过一生”的心态。
常言道:“千金易得,一将难求”。为了请动彭玉麟,曾国藩亲自登门造访,用自己墨絰从戎的事例现身说法,又以“乡里藉藉,父子且不相保,能长守丘墓乎”之语点拨,始劝得彭玉麟出山,承担起湘创建军水师的任务。
至此,曾国藩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将湘勇从普通的地方团练改造成一支水陆齐备、粮饷具足的国家武装——湘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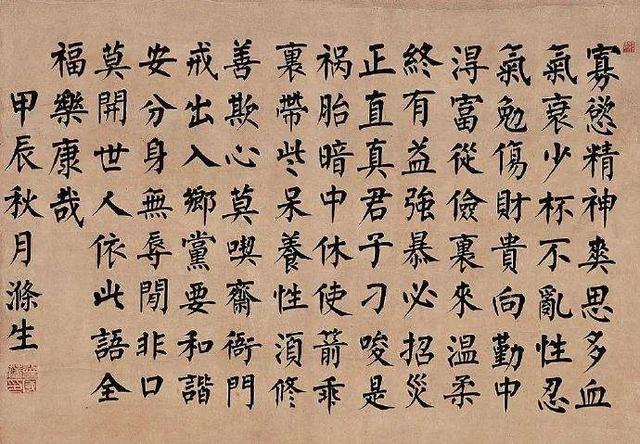
咸丰四年(1854)二月,曾国藩统领这支一万七千人的水、陆大军离开衡阳,出师北上,在湘潭、靖港两地与太平军交锋。
初历战阵的湘军先胜于湘潭,后溃于靖港。陆军损失不大,但水师折损了三分之一左右。痛定思痛的曾国藩彻底领悟到:从湘勇到湘军是一个长远的过程,绝不是靠跨省征战之权、财政拨款之利就可以轻易实现。
欢迎关注文史宴
专业之中最通俗,通俗之中最专业
熟悉历史陌生化,陌生历史普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