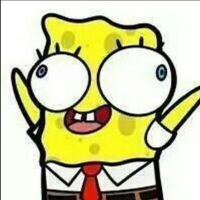1959年的秋天,阴云低垂,北京机场跑道上的风夹着微微寒意。
一架从远方飞来的飞机缓缓降落,舷梯终于放下,舱门打开,一位身着厚重藏族传统服饰的年轻女子出现在舷梯前端。
她不过17岁,却眉目间透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冷峻和深沉。
望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国土,她突然双膝跪地,俯身匍匐,将额头贴在那片冰冷的地面上。
她是谁?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为何会从数千公里外的印度孤身来到这里?

1942年藏历二月初八,这一天在桑顶寺历史上被视为无比重要的吉日。
清晨,太阳还未完全升起,整个寺庙便已被前来观礼的人潮围得水泄不通。
寺庙内外,挂上了五彩的经幡,随风猎猎作响。
僧俗百姓聚集在桑顶寺外,人们身着盛装,有的带着风尘仆仆的疲惫,有的捧着供奉的酥油和哈达。

庄重的礼仪由寺庙的大殿开始。年幼的德钦曲珍穿着红色和黄色相间的仪式服饰,她被护送至一张精美雕刻的木制坐床上,寺庙大殿内的高僧活佛围坐在她身旁,齐声诵念佛经。
金刚铃和法鼓相继响起,空气中充盈着佛教仪轨的神圣氛围。
当活佛德钦曲珍被正式加冕为第十二世多吉帕姆活佛时,大殿中的气氛达到了顶点。

作为“产生诸佛的大佛母”化身,德钦曲珍的加冕无疑是藏传佛教的重要时刻。
无论对宗教界还是对信徒,她的降世被视为一种不可思议的福报。
与此同时,她也成为在中国历史上唯一被尊封为“大呼图克图”的女活佛。

坐床典礼的热闹消散后,桑顶寺的生活回归了它原本的安静,而年幼的德钦曲珍也正式开始了她的修行之路。
清晨,当东边的日光洒向寺庙的白塔时,小活佛便已经披上袈裟开始一天的礼佛。
桑顶寺的大殿宽阔而幽静,墙上布满了绘制精美的唐卡,讲述着佛教的故事。
在这些传统绘画的注视下,幼小的德钦曲珍学会了长时间的静坐与经文诵读。

每年,她总会前往古城江孜或者春丕山进行修法。
出行时,她的身份总会招来不小的动荡,每一次旅途都引发沿途信徒的大规模围观。
僧俗官员的护驾队伍穿过牧区、山谷,沿途的村民们都会精心准备酥油茶、糌粑等供奉食物,在道路的上空悬挂经幡,为她祈求加持。她的短暂停留,无形中成为当地群众生活中的重要事件。

随着时间进入20世纪40年代末,整个西藏地区因政治局势的转变而逐渐陷入动荡之中。
1949年,这一切发生了彻底的转折。

1949年3月,西藏的天空沉重而晦暗,隐隐传来的枪声打破了山间的寂静。
西藏地方政府发动的武装叛乱,将整个地区推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动荡之中。
寺庙盟墙之内,诵经的声音开始夹杂着僧众低声的不安议论,面对外界的纷乱,十二世多吉帕姆·德钦曲珍和她的近侍试图维持寺内的秩序,但局势迅速恶化。

很快,叛军以武力强行闯入寺庙。为了补充武器和粮草,他们多次逼迫寺院交出寺中积存的物资。
他们的目光甚至锁定了德钦曲珍这位年轻的活佛,试图利用她的影响力为叛乱筹集支持。
面对这一切,寺中僧众与活佛一起商讨对策。眼见叛军的行为愈发过分,最终徒留在桑顶寺意味着危险日益逼近,甚至可能引发一场血雨腥风。

在西藏青翠山峦之间,有着羊卓雍措,这片宁静的高原圣湖倒映着雪山的身影,湖水碧绿如玉,被普遍认为是藏地的圣地之一。
而德钦曲珍和几位近侍决定将其作为隐秘庇护所,他们匆匆出发,逃离了桑顶寺。一路上,他们不得不昼伏夜出,穿越人迹罕至的群山,以避开叛军的眼线。

湖心岛是羊卓雍措中间最为隐秘的地方,他们渡湖躲藏于此。
三面环水,一面以茂密的树丛掩护,这里仿佛天造地设、与世隔绝。
看似平静的藏身之地并未能成为他们的长久庇护所。
躲避了数日后,他们还是被叛军追踪到了这个隐蔽的避难点。
一群荷枪实弹的叛军冲破树丛,漠然地面对这位手无寸铁的年轻女活佛及其随从。

她被迫接受叛军的安排,开始了一段飘零无依的逃亡生涯。
德钦曲珍首先被挟持至不丹,这个毗邻西藏的小王国虽并非另一个世界,却已经足够让这位年幼活佛与自己的家园渐行渐远。

在异国他乡的日子里,德钦曲珍并没有放弃回归家园的希望。
1949年8月,在中国驻噶伦堡商务代理处的协助下,17岁的德钦曲珍迎来了转机。
在复杂的国际交涉中,这位被困国外的女活佛终于得以脱离叛军的控制。

从印度的起点,她辗转穿越巴基斯坦,途中面临着紧张的国际氛围带来的关卡检查与不安定性。
之后,她又绕道阿富汗,哪怕是在这样多山的陌生国度,德钦曲珍仍需默默忍受对家乡的思念。

跨越了前苏联与蒙古的漫长路途后,她终于在1949年9月底到达北京。
几乎是终点的北京,对于德钦曲珍来说却分外的亲切。
当那一天来到,她终于站在中国的土地上,周围一切都仿佛染上了故乡的气息。
当她下飞机时,那种激动溢于言表。

身着厚重的藏族传统服饰,她慢慢踏下舷梯,而舷梯下是接送她归来的中国官员和藏民代表。
就在那一刻,她突然跪倒在地,长时间匍匐,双手紧贴怀念已久的大地,额头触碰至泥土,她几乎哽咽得无法言语。
面对围观的人群,她终于用一口熟稔的藏语低声说道:“如果没有祖国,恐怕我永远无法再返回自己的家乡。”
她的每一个字都带着一种深沉的感情,深深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1957年,十二世多吉帕姆·德钦曲珍从印度返回西藏,告别了海外漂泊的日子,她被政府安排在拉萨居住,生活模式也随之改变。
从那时起,她的修行从寺庙内的群体活动转为更加个人化的“在家修行”。

1966年,十年动荡的大幕在中国开启,这股浪潮最终也卷到了这位女活佛的生活之中。
被视为宗教中心的桑顶寺未能幸免劫难。这座承载了她整个童年时光与信仰寄托的古老寺庙,被夷为平地,昔日的大殿和佛堂灰飞烟灭。

她的修行生活也在这一年陡然停滞,不仅她的个人修行被迫终断,寺中用于传承的经卷、法器和宗教仪轨也一同被摧毁。
记忆中清晨回荡的诵经声变成了寂静无声的废墟,信仰的根基遭到无情动摇。而她的弟子、僧侣及周围的信徒在这场浩劫中四散,纷纷远离寺庙。

她被迫与信仰世界保持距离,转向隐忍低调的生活。
从前习惯于与僧众共同修行、朝圣和主持寺院事务的日常,被迫变成一种孤独而形式化的个人修行。
那段岁月中,德钦曲珍多次陷入矛盾与无助,但她依然坚守某种微弱的信念,期待未来总有转机。而这种等待,持续了十余年。

1980年代,政府对宗教政策有所调整,修复的希望终于重新点燃。
1984年,桑顶寺终于得以重建。重建的过程中,有老工匠用记忆中的寺庙结构一点点复原,有来自乡村的信徒奔赴辛勤劳作,为的是再现昔日的辉煌。
见证了寺庙涅槃重生的德钦曲珍双眼噙泪,曾经被迫搁置的宗教传统终于得以继续,她再次拾起活佛的职责,开始主持重要的宗教仪轨,每年的“岗甲萨”大法会也成为她生命中的重要活动之一。

1994年,一场充满神圣色彩的宗教活动在桑顶寺展开,那是藏传佛教中被奉为至高仪式之一的“花露药丸炼丹”大典。
炼丹在藏传佛教中有着悠久而神秘的历史,它以复杂繁多的仪规与耗时耗神的准备工作而著称。
炼制的药丸并非普通的药物,而是被视为结合了天地宇宙能量与活佛修行力量的神圣化身。它们通常用于重大法会期间的供养或疾病治疗。

在为期半个月的参与中,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德钦曲珍全身心投入。
炼制的第一步便是从自然中采集上百种稀有的藏药材,每一种药材都必须经过严苛的挑选与净化仪式。
在那一刻,人们目睹的是德钦曲珍如何以专注的眼神审视山间采摘来的每一片草叶和每一颗种子。

随着大典的进行,从四面八方向桑顶寺汇聚的信徒人数逐渐攀升。
据统计,最终的祈福人数达到了上万人,他们带着自家供养带来的药材与哈达,希望能参与到这场史无前例的盛典之中。
在药丸即将炼成的时刻,整个寺院上空直冲天际的香火四溢,仿佛连接着尘世与神界。
那些药丸在佛前被供奉加持后,再由德钦曲珍一颗一颗地分发出去。接受药丸的信徒们无不激动涕泪,他们将其视作庇佑未来的至宝。
参考资料:[1]旺堆.女活佛桑顶·多吉帕姆在1959[J].中国藏学,1999(1):118-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