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克定
故事起源于一包蚕豆。
1915年的北京城还算平静,袁世凯虽然天天做着那当皇帝的梦,政事倒是照常施行。
至少平常人家准备逃难的包袱一时半会儿还用不上。
好日子谁不想过?但是正值乱世,“乱”也得有“乱”的活法。
大街小巷里,四处都是小贩们的吆喝声,左边打仗,右边游行,老百姓的生意不好做。
一间卖果脯小食的杂货店里,进来了个丫鬟打扮的小姑娘,直言要买黑皮的五香酥蚕豆,价钱不是问题。
只见这姑娘虽然打扮朴素,但一打眼就能看出来是大户人家出来的,想必定是为哪个小姐姨娘买的解腻零嘴。

民国时期北京城里走街串巷的小贩
慧眼如炬的老板听着喜笑颜开,忙不迭抽出一张干净的报纸,是时下最权威的《顺天时报》,刚刚打印出来不久,还留有淡淡的墨香味。
不过很快,那一丝墨味就被咸香扑鼻的熟蚕豆味盖住,一大包新鲜出炉的蚕豆被丫鬟拎在手中,直奔“新华宫”而去。
那是曾经的天潢贵胄、皇亲国戚才能住的地方,如今,是袁世凯一家人的“行宫”。
只见这个小姑娘轻车熟路的进了旁人只能远观不可亵玩的地界,目标明确的冲着一间装饰华美的屋子走去。
正等着吃蚕豆的大家闺秀望眼欲穿,见到侍女手里的包裹,顿时喜笑颜开。

民国摩登女郎合照
这姑娘不是旁人,正是袁世凯的三女儿——袁静雪。
自己最喜欢的零嘴就在眼前,袁静雪忙打开报纸,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顺便瞟两眼报纸上的最新消息。
可看着看着,她发现不对了。
此时的袁静雪年纪还小,正是孩童心性,可这并不意味着她看不懂包裹蚕豆的报纸有问题。
《顺天时报》虽是日方注资开办,但是当时社会混乱,许多纸媒纷纷倒闭,这个外资的报纸也就逐渐成为了民众接受消息的最大来源。
掌握了流量就控制了发言权,一百年前的民国也不例外。
《顺天时报》的繁盛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民意”。

《顺天时报》
而作为明面上国家的最高领导者,又处在复辟的关键阶段,袁世凯自然对此报的“民意”甚为重视。
闲暇之时,这位身居高位的总统大人总会抽出一段时间细细品读当天的时政新闻、社会观点。
当他看到报纸上对其如今功绩大加赞扬之时,总是颇感欣慰,认为自己做皇帝乃是“顺安天命”。
大家长对《顺天时报》尚且如此推崇,那袁家人或多或少也对其多点关注也是情有可原。
或许是天意,发现不对的,正是颇受袁世凯宠爱的袁静雪。

袁世凯
包着蚕豆的报纸同样是当天的《顺天时报》,为何与她今日看的不同?
深思熟虑、两相对比之下,她得出了一个惊骇的结论:
有一份报纸是假的!
她知道,这份报纸和大哥袁克定脱不了关系。
实际上,家里孩子与大哥的关系都不好,于是袁静雪选择问风流儒雅的二哥——袁克文。

袁克文
袁克文却只和她说了一句话:
“我在外边早已看见和府里不同的《顺天时报》了,只是不敢对父亲说明”,袁克文道:“你敢不敢说?”
“我敢!”
后续的事情很难得知细节,女孩年纪还小,不知道这是何等严重的大事,告知真相时,父亲袁世凯的沉默却让她心惊胆战。
她只知道,第二天起床之时,全家人都在讨论大哥被父亲用鞭子狠狠抽了一顿的事。
那年的袁克定,37岁。
一张报纸,为何能让袁世凯对向来看重的儿子痛下狠手?甚至骂其“欺父误国”呢?

袁静雪
袁克定,字云台,别号慧能居士,可他做的事,却称不上一个“慧”字。
1912年,喜爱驰骋于马场的袁克定终日打雁,终被雁啄了眼,摔下马,直接将腿摔到了不能站立的程度。
加入政场十几年,袁克定与袁世凯的关系远非“父子”可轻易定论,武昌起义、南北和谈、外交事务,袁克定均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
袁世凯是个相当重视嫡庶亲疏的传统人物,他将袁克定视为接班人,几十年来亲手培养,哪见得儿子落得如此地步。
听说德国医疗事业发达,他迅速派人将大儿子送到了德国最好的医院救治。
若是袁老先生预知了日后诸多乱事,皆因此念而起,不知道会不会悔青了肠子。

袁克定
毕竟是一国元首的亲生儿子加得力助手,袁克定一到德国,就受到了极大的优待,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甚至特意为其举办了欢迎宴会。
灯红酒绿,鬓影香风,推杯换盏间,被晃花了眼的,不止袁克定一人。
或许威廉二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与袁克定客气了许久,他终是带着些许诱惑的口吻无意道:
“中国不适合共和制,只有君主立宪制,才是大势所趋。”
“君主立宪”?昏昏沉沉中,袁克定听到了这四个字。
乱世出英雄,人是中国人,国是中国人的国,除却真正卖国求荣的汉奸之流外,不同阶级、不同政党、不同阵营的政治家们,都只有一个目的——“救国”。
而袁克定心中或许有这个心思,不过瞬间膨胀起来的虚荣心让他暂时无暇他顾。

威廉二世
所以,我们不能说袁克定被猪油蒙了心,他只是不会预知而已。
他不能预知一战、二战,德国既是发起国,也是战败国;
他不能预知其父的皇帝之位只坐了83天;
他同样不能预知,中国早已不是“君主”可以控制的国家。
袁大公子只看到了德国的兵强马壮、国富民强。
他看不见专制让人民苦不堪言,看不见战争让国民流离失所,甚至看不见威廉二世眼中,那被掩盖在善意之下的贪婪和野心。
世界是个圈,想稳坐霸主之位,东亚国家的加盟必不可少,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而处于亚洲漩涡的中国,必须要以重宝徐徐图之,拉拢结盟。
当然,这份拉拢和宝物究竟几分真心,几分利用,或许只有德国的政客们自己心中清楚。
而袁克定此时以为自己发现了什么常人难以得到的宝藏,迫不及待地拖着一条病腿回国邀功。

中袁世凯
君主立宪制?中国不就有现成的吗。
袁世凯想做皇帝这个念头究竟是何时兴起的?古今中外诸多学者专家讨论了许久也没个准确答案,可有一条是大家纷纷赞同的。
他想集权。
而众所周知,皇帝才是中央高度集权制的最大受益者。
民国初立的前两年,各类民间党派层出不穷,军权、政权,被分流进各个军阀高官手中,袁世凯这个总统看上去风光无限,实际上处处受人掣肘。
袁克定从德国带来了“君主立宪制”的消息,让曾经不会在意的袁世凯第一次认真考虑起了西方的政治制度。
从那一刻起,“复辟”就板上钉钉了。
而若说此举是袁世凯为了将权利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行动,那袁克定的想法就简单多了。
父亲若是能当皇帝,他就是“皇太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曾亲眼看见皇权破碎的夕阳之景,自然也了解万民供养一人的盛世华景。
此时的袁克定,或许已经选择性地忘记了,曾经的他,也是一个坚定的革命斗士。

袁世凯与各国使臣合影
相较不受父亲喜爱的生母于氏,袁克定在袁家“金贵”多了。
虽说袁世凯是庶子出身,但是并不妨碍他将嫡子看得最重。
袁世凯与于氏的婚姻热度只维持了短短两年,或许这门亲事唯一的意义,就是生下了对袁家来说十分重要的嫡长子。
袁世凯并不迂腐,但是他相当重视嫡庶,从小到大,他从未想过让袁克定以外的人继承他的衣钵。
作为袁家二公子的袁克文比袁克定小11岁,与袁克定不同,虽同样深受宠爱,但是并没有作为接班人培养,于是从小千恩万宠长大的他一直是个浪荡公子,并不醉心政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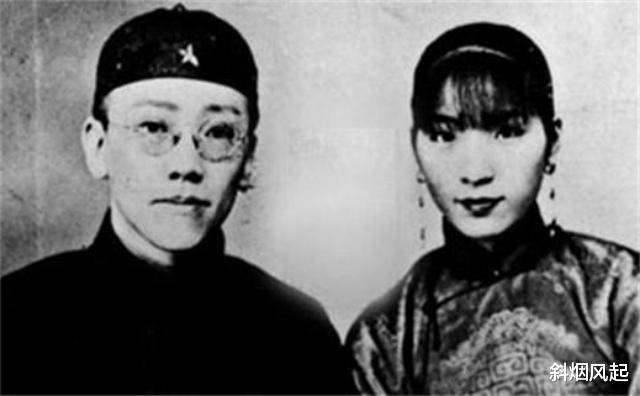
袁克文与妻子刘梅真合照
让袁克文一直苦恼的是,袁克定一直将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比如在立太子这件事上,后者甚至曾直言:
“如果大爷(袁世凯)要立二弟,我就把二弟杀了!”
虽然听起来是气话,但是也足以说明袁克定对“皇太子”之位的垂涎欲滴。
自从袁世凯决定复辟之时,袁克定就已经以太子自居,为人极其倨傲,甚至不把父亲手下的老臣放在眼中。
1913年新年伊始,段祺瑞与冯国璋按旧礼给袁世凯拜年,袁世凯身居高位,在二位老臣行跪拜大礼时,连连摆手,称“不敢”。
而作为晚辈的袁克定面对两位老者的大礼,却端坐在首,安心受了几拜。
人情世故是个不明言说的默契,袁克定此举,称得上狂妄。

段祺瑞
可惜,假《顺天时报》暴露之后,袁克定在袁世凯心中的地位急速下降,“欺父误国”的标签直到袁世凯悲愤逝世之时,还扣在他信任一生的大儿子头上。
可这时的袁克定显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袁世凯因复辟失败忧愤离世后,家中的长辈只剩下当家主母——于氏坐镇。
虽说于氏只是个不通文墨的小脚女人,但是长辈不亡家不散,豪奢一时的袁家撑不起袁世凯逝世后的门面,也只能看似安稳的照旧生活。

袁世凯妻妾女儿合照
3年后,于氏去世,袁家正式分家。
作为家中长子兼封建大家长的角色,袁克定分得的家产是大头。
据传,除去古董字画、不动房产、珠宝店面之外,他还拿到了40万的现金大洋。
而其他庶出兄弟们,只分得了12万元,还比不上袁克定的半数之资。
根据袁克定的侄子袁家宾所说,袁世凯在世时,曾存于法国银行200万法郎,而这些钱,最终都归到了袁克定手中,家中兄弟还曾因此闹过一阵。
尽管已没有了“袁家天下”的供奉华景,但是不得不说,如此厚重的家产和资金,也足以供得起一个富贵之家。
可最终,袁克定为何落到了吃破菜叶子的地步?

袁世凯与子女合照
北伐战争胜利后,时局变了。
国民政府执政时期,是袁克定生活水平的急速下滑期,虎落平阳被犬欺,不再从政的他人人都能来踩一脚。
袁克定本身是傲气颇重的。
他曾因家中弟妹不听从自己建议,随意婚嫁,大庭广众之下下人面子。
也曾因不能接受宪兵警察的搜身之举,一怒之下再未去过天津。
而最为知名的,则是他于华夏存亡之际,坚决不为三斗米折腰的故事。
1928年前后,国民政府曾对袁克定名下的财产进行了没收和封禁,这导致其生活水平本就每况愈下。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狼子野心妄图吞并中华大地,没正式露出凶狠面孔时,四处招揽收纳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物。
袁克定,就是其中一位。

汪伪政府高官合照
彼时日本在中国的权利相当之大,一系列不公平的条约让各大港口门户大开,即便在政治场上,他们渗透的也相当充分。
华北的汪伪政府正在日本人的控制下四处“招兵买马”,时任华北伪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朱深,“替”袁克定签订了一份条约——《拥护东亚新秩序》。
袁克定的缺点不少,干的错事也不少,但是骨子里对于叛国的事情还是有着些原则和分寸的。
听闻此事,袁克定大为不满,迅速找寻报社,想做出澄清,可此时北平的报社皆害怕大势力报复,皆不敢发声。
重重困难之下,他找遍关系,托遍熟人,终于在一张报纸的小小角落登出一则澄清声明:
“未经本人同意,署名不予承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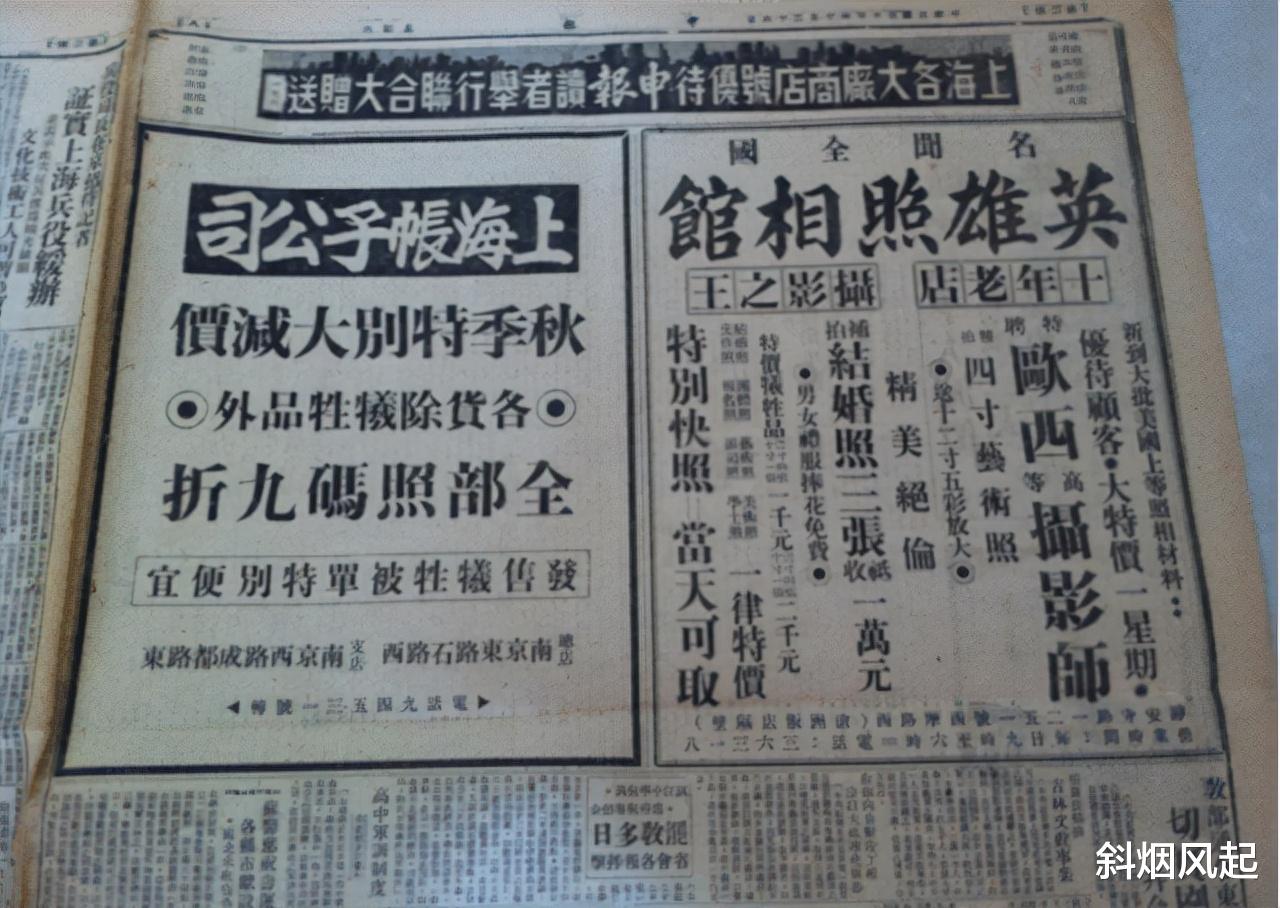
民国报纸
事实上,在当时的大背景之下,袁克定费尽功夫做出的澄清对其来说可谓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而他毅然的与另一方割席,这成为了袁克定日后十分说得出去的一件得意事,但是并不能缓解其生活的窘况。
19世纪40年代,袁克定的生活早已难以为继,家中不再请得起佣人家丁,一位老仆人却依旧忠心耿耿。
最难的时候,已经须发皆白的老人家常常佝偻着身子,去菜市场捡一些别人不要的蔬果青菜,更多的时候是白菜,因为易于储存。
炒菜、熬汤、做腌菜,袁克定就靠着这位老仆人“化缘”而来的食物聊以度日。

民国街边卖食物的小贩
可偏偏这时的他依旧端着那让外人不明所以的“优雅”,每次进餐必定净手端坐,戴起餐巾,拿起刀叉,切割着曾经不屑的窝窝头和咸菜。
按理说,能在政场上挥斥方琼的袁大公子绝对不是个蠢人,但是除却当权政府对其刻意的为难之外,如此困境与他自己所作所为也脱不了关系。
他有极其相信“自己人”的坏毛病。
年轻时被女人欺骗过感情,于是爱上了男色。
他信任自己的下属仆人,结果被人骗光了房产。
因为不曾怀疑过儿子供养其晚年的决心,他被儿子骗走了全部的股份和资金。
这确实让人有些哭笑不得。
最终,还是袁克定的表弟——张伯驹,供养了其晚年生活。
或许经历了太多的恩怨是非,解放之后的袁克定生活逐渐平淡安稳,甚至懂得了感恩回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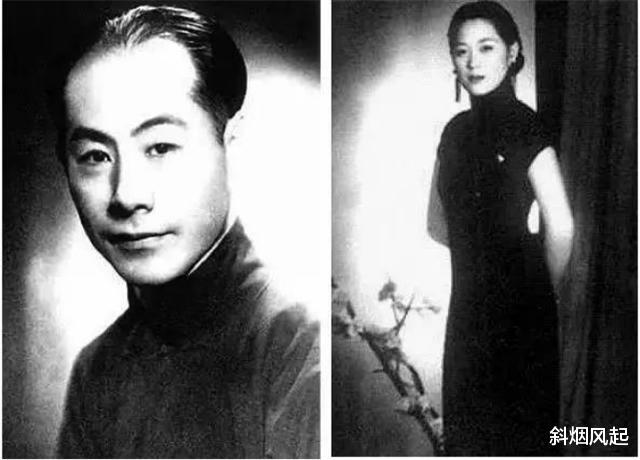
张伯驹与爱妻
他会将自己全部的工资收入交给张家媳妇,不参与张伯驹的社交会友,每日除了在文史馆中做好本职工作,就是在四方的小院子里安稳待着。
而他晚年的故事,竟然是由张伯驹的女儿——张传彩,口述给后人的。
忙忙碌碌了一生,不知道究竟该评他诸事圆满七彩人生,还是感叹一句:
曾经种种,竟然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