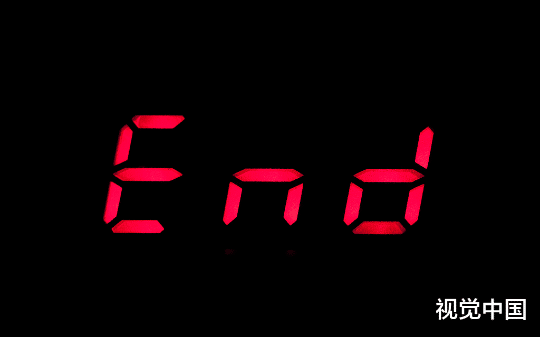一年前,我和丈夫随科考队攀登珠峰。
但在进入雪线后不久,我们就遭遇了暴风雪。
队里的小白花为了活下去,抢走了我们这一队人的所有物资,害得所有的队友被活活冻死。
更是将我一刀刀捅死后,一脚踹进万丈冰壑。
却对赶来的救援队颠倒黑白,说是我害死了所有人后畏罪潜逃。
丈夫亲自写了报导刊登,将我从地质考察队除名。
儿子更是想到我就大骂:“我不要这种贱女人当我的妈妈!我巴不得她永远别回来了!”
我成了被全国人民唾弃的存在。
只有外婆坚信我的清白。
一年后,冰川消融,有人在河流里发现了我面目全非的尸体。
01
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心情面对我的尸体。
全身上下都有被野生动物啃食过的痕迹,脸部身体无数道深深的刀疤被水泡到卷曲,显得愈发狰狞吓人。
饶是许天河这样经验丰富的地质考察员都有些看不下去,偏过了头。
“每年因为攀登出事故的遇难者都不在少数,即便是考察队员也不例外。”
许天河细心地发现了我尸体衣服上的地质考察队logo,手指顿了一下。
这也是验尸官请他来做身份辨认的原因。
“是一位放牧的藏民在河流里发现了这具尸体,应该是伴随冰川消融从雪山上流下来的。”
“尸体存在大量被伤害过的痕迹,脸都被划烂了,携带的通讯设备与身份证件也都被人拿走,看样子是不想让我们知道死者的身份。”
验尸官颇为不忍地咋舌:“这得多大仇啊……许队长,您有什么头绪吗?”
我死死地盯着眼前这个男人。
期待他的口中能说出我的名字。
我被丢弃珠峰的万丈冰壑之下整整一年,从未想过还能重见天日,我想,这一切都是天意。
可是许天河的眉紧蹙了很久,最终冷冰冰地吐出两个字:
“没有。”
验尸官有些失望,却也在意料之中。
许天河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问道:“这件事除了我还有谁知道?”
验尸官摇摇头:“您是科考队的负责人,除了您我没有通知过别人来认尸。”
许天河一贯冷峻的面容终于流露出一丝笑意。
“那就好,这种小事没必要打扰到别人。何况欣欣有抑郁症,我担心她知道了,又会吓到做噩梦。”
验尸官闻声也笑了,显然对他们十分看好:“瞧您说的,谁不知道您跟欣姐快结婚了,我们怎么会去触霉头呢。”
我怔愣地望向许天河。
没有了我的存在,他最终还是奔向了那多柔弱的小白花。
可我才死了一年呀。
验尸官边和他打趣,边又止不住地看向我的尸体,忽然“咦”了一声。
“许队,您觉不觉得这个人有点儿眼熟?”
“像不像一年前失踪的何蔚蓝?”
许天河一瞬间脸色变得极为阴沉。
“不要在我面前提她!”
一字一句都像是从牙缝中挤出来,透着无与伦比的恨意:“那种害死队友来保全自己的小人,还提她做什么?”
02
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许天河有些疲惫地捏了捏眉心:“这人去世大概多久了?我回头问问同事有没有印象。”
验尸官却没有回答,反而问道:“许队,何蔚蓝叛逃多久了?”
“一年。”话音刚落,许天河的表情变得怪异了起来。
我知道,他是想起了一年前的那桩雪山事故。
我带领的考察小队遭遇暴风雪,全队仅有朱欣欣一人生还,其余所有人等到救援队赶到的时候,早已冻成了冰雕。
但正是因为这桩惨案,考察队已经一年没再涉足珠峰了。
许天河斩钉截铁:“不可能是她。”
因为,正是那活下来的朱欣欣告诉他:是我为了活下去,抢走了队里所有的物资,才害所有人被冻死。
而我正好音信全无,他信了,回所里后立刻写报告呈交上级,甚至公然发布到网上。
用最犀利刻薄的口吻抨击我,说我是他见过的最无耻的贱人。
我的心在滴血。
他居然听信了朱欣欣的一面之词而这么诋毁我。
尸体的身份始终无法明确,只能送去验DNA。
刚出门没多久,许天河就接到了朱欣欣的电话:
“天河,小川被人打了!我好害怕,你快过来……”
许川是我和许天河的儿子,今年都七岁了。
闻言许天河脸色骤变:“你别急,先把定位发给我,我马上过来!”
我的灵魂被迫跟着许天河而动。
想到儿子,我的心里既感到雀跃,又有些隐隐地不安。
小川他现在,还讨厌我这个妈妈吗?
03
许天河赶到的时候,就看到打扮清纯的朱欣欣站在一个馄饨摊前,哭得梨花带雨。
只见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奶奶正把一个七岁的男孩架在双腿上,一下又一下地用力拍打他的屁股:
“我叫你小小年纪满嘴喷粪!”
“我叫你不尊重你妈妈!”
许川痛得惨叫连连,却仍梗着脖子不认错:“老东西快放开我,否则等我爸爸来了,看他怎么收拾你!”
这位老人正是我的外婆。
闻言,她冷笑一声:
“好啊,别以为把你爸爸搬出来了,我这把老骨头就会害怕!我还没去问他,把我外孙女藏到哪里去了!”
许天河一把抢走许川,厉声喝道:“够了。”
朱欣欣缩在许天河怀里,哭成了泪人:“都怪我嘴馋,忽然想吃馄饨,小川便好心地建议我来这里,说他曾外婆做的馄饨最好吃,没成想人家根本不欢迎我!”
说罢,她掀起袖子,被热汤烫过的部位鲜红而触目惊心。
许天河面带薄怒:“你!”
“是我干的怎么了!”外婆用铁勺把大锅敲得砰砰响,“我的馄饨不欢迎小三食用!这个坏女人把小川带坏成什么样啦?连亲妈妈都不要!”
许川跳出来嚷嚷:“我就是不要她!”
“爸爸说了,那个贱女人害死了好多无辜的叔叔阿姨,她是坏人!这种人怎么配当我的妈妈!我巴不得她死在外边儿,永远别回来了!”
听到许川这么骂我,许天河反而露出了欣慰,再看向外婆,语气都多了几分高高在上:“说起来,我确实有事找您……”
“何蔚蓝现在就躲在您这里吧。”
04
外婆愣住了。
我也一愣。
以为外婆没听清,许天河又重复一遍:“您从小就溺爱她,纵容得她无法无天,她犯下这么大的事,想来也只有你还愿意藏着她了。”
外婆气得手直哆嗦,差点一口气没提上来。
“我家蓝蓝不是叛徒!”她大声喊道,眼眶里逐渐蓄上了泪水,“她是被冤枉的!我也不知道她这一年去了哪里,连通电话都没给我打过。”
许天河脸色一沉:“外婆,我和欣欣要结婚了,她只要让出许夫人的位置,过去的事我就可以既往不咎。”
“你快让她跟我去民政局把离婚协议办了,不然欣欣怎么做人?”
在他看不见的地方,朱欣欣唇角微勾。
以为外婆会暴怒,可这次外婆没有。
只见外婆沉默了一会儿,转身继续煮馄饨:“我比你更想知道她的下落,可是蓝蓝真的不在我这里。”
许天河不信,看向外婆身后小破屋,像是明悟了什么。
径直闯进那个他与我从小玩到大的民房,翻了个底朝天,连卫生间都不放过。
却始终没有发现发现我的踪迹。
他终于大发雷霆,一巴掌拍倒了一张折叠桌:
“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帮着何蔚蓝胡闹?”
“既然您铁了心要包庇她,那我就上报城管,把你这没有营业执照的小破摊子收了!”
“我只给何蔚蓝一周的时间,叫她赶紧滚出来见我!”
我震惊地望着许天河,忽然像是才认清了他一样。
他在说什么啊,明明跟我一样都是吃着外婆的馄饨长大的,明明知道馄饨摊是这个小老太太的唯一收入来源。
他居然为了朱欣欣,用这个来威胁她。
说完这句话,许天河就带着朱欣欣和许川扬长而去。
我看着外婆沉默煮着馄饨的佝偻背影,泪水止不住地掉。
却只能无声息地消散在半空中,一如我这个灵魂一般。
这世上唯一还坚信我是清白的人,就只有我的外婆。
05
许天河说到做到。
一周后,没见到我人,他果真带领一帮人围了外婆的馄饨小摊。
这帮人大多是地质考察所的同事,以及部分遇难者的家属。
“老人家,我们不为难您。”
为首的人眼含泪水,竭力让自己保持冷静:“我们只需要何蔚蓝出来,给我们所有人一个交代!”
许天河脸色阴沉,言语中满是讥讽:“我说吧,何蔚蓝就是个冷血的家伙。”
“您这么多年真是养错人了,我再给最后一次机会,她人现在在哪儿?”
朱欣欣见火药味十足,立刻娇软地扶住了他的肩膀:“老公,别动气,姐姐可能是害怕,毕竟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不敢出来见人。”
朱欣欣的谎言堪称天衣无缝,毕竟死人永远没办法开口。
但我突然有些好奇,假如许天河知道了我真正的死因,他和许川会有什么反应。
他们……会难过吗?
随即我又为自己这个想法感到可笑,全天下最巴不得我去死的就是他们父子了,怎么会为我难过。
外婆面无表情地往煤炉里添了块蜂窝煤:“你们的戏真多,同样的话还要老婆子说几遍。”
人群后突然爆发一声凄厉的怒喝。
那是一位队友的遗孀,自从丈夫遇难后,她的精神就有些疯疯癫癫了。只听她大吼一声,掀翻了离她最近的一张桌子:
“我要给我的老公报仇!”
情绪就像是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人心潘多拉的魔盒。
人们开始疯狂地打砸一切目光所及之处,有外婆用了十几年都不舍得丢的折叠桌椅,刚烧开的大锅连同煤炉重重砸在地上,热水所经之处,蒸汽蔓延,将外婆苍老的面容也变得晦涩不清。
眸光闪烁,又似早已麻木。
我的事情闹得举国皆知,时不时前来打砸、将正义感宣泄在老人身上的,又何止他们一个?
那些人打红了眼,大吼着冲向外婆的小民房:“还有这里!”
家里当即被砸得一片狼藉。
我曾经出生入死的队员,每一个人都参与了这场暴行。
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拼命想去阻止,却只能徒劳地穿过每个人的身体。
有人看见了我上锁的房门,怒吼一声砸掉了门把上的锁:“这一定是那个贱人的房间!我倒要看看她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外婆的脸上终于有了慌乱,颤颤巍巍地跑了过去:“别动那里,别动那里……”
可没人会听她的。
06
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小房间终究是毁了。
几个壮小伙子抡起棍棒就要砸掉我挂满整面墙的奖状和荣誉证书。
外婆为了护住我的荣耀,不顾一切地上去阻拦。
人群后的许川眼中忽然闪过一丝精光。
他冷不丁地用力推了外婆一把,只听外婆“哎呦”一声,苍老臃肿的身形毫无防备地向前倒去。
额角重重地磕在了木制床头柜的边角上。
当场鲜血染红她身下的水泥地,外婆地四肢轻微地抽搐了一下,彻底不动了。
“外婆!”我嘶吼着扑到她的身上,这一刻我多么痛恨我是个死人!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我们做错了什么!
有人见到鲜血,终于清醒了过来,继而惊恐地大叫:
“出事了!”
见状,许天河淡漠的脸色微微一变。
他一把将许川藏到了身后,确定没人发现是他做的后,小声地呵斥道:“你知道你刚刚做了什么吗?”
许川吐了吐舌头:“谁叫这个老东西上次打我,我许川有仇必报!”
许天河不赞同地弹了他的脑门:“调皮,对何蔚蓝一家老小这么做也就罢了,对别人可不能这么没礼貌,知道吗?”
话音刚落下,许天河的口袋里便传出了手机的震动。
一声声,如同剧烈敲击的擂鼓。
许天河诧异地按下接听,紧接着那头传来了验尸官的声音。
“许队,化验的结果出来了。”
那个人声音颤抖到几乎不成完整,仿佛世上最恐怖的事情正发生在他眼前。
“那具尸体的身份是……何蔚蓝!”
“一年前我们都以为她失踪了的何队!”
我看到许天河如遭雷击一般,过了好久好久才找回了自己的声音,语气里都是不可置信:
“……你说什么?”
那个人直接哭了出来:“就是你的妻子啊许队!我们好像都错怪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