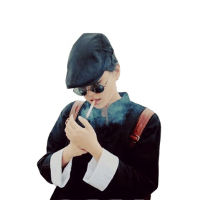1930年,中国各大报纸纷纷登载了一条爆炸性的消息: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伙同其女婿、该院秘书长李宗侗监守自盗,携卷故宫大量国宝逃匿无踪。此消息一出,便如石破天惊,引起社会各界议论纷纷,顿时轰动全国。
那么,故宫盗宝案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辛亥革命后,清帝退位,但清王室仍然留居故宫,直到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民国政府才将故宫收归国家,由政府出面管理。

故宫博物院的主事人虽几经变迁,但自北京大学教授李石曾起,经庄、江、王三任院长至易培基,都对宫内宝物注意保管,严令院内职员按规章办事,不准监守自盗,也没有人敢私自出入储藏宝物的房室。可以说,当时为防范故宫宝物被盗而采取的措施是非常严密而又严格的。
既然故宫防范宝物被盗的制度如此严密,那么又因何会发生故宫盗宝案这一咄咄怪事呢?难道易培基真有偷天换日的本领,学会了孙悟空的七十二种变化?事实当然并非如此。
导致易培基大走霉运的最初原因,却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了。易培基接任院长之初,便依照旧官署的惯例,对职员重新加以委任或添用。其中,秘书长由他的女婿李宗侗出任,国民党元老张继则出任古物馆的副馆长,馆长则由易培基自兼,马衡与张继同列副馆长之职。
盗宝案的发生,就是由李宗侗与张继的老婆崔振华发生口角而起的。

故宫博物院宝物展览的地点分东、中、西三路轮流开放。有一天,恰值中路开放日期,又逢李宗侗率职员在东边厢房整理皮货。当天张继的老婆崔振华来看皮货,她一进神武门就转弯向东走。值岗警察并不认识她,把她当成了参观中路却错向东行的游客,于是叫她往南走,进御花园浏览。不料,一向专横的崔振华根本不听警察指挥,而且也不说明来意,执意要向东走。警察认为指挥游客是自己的职责,坚决不放她过去。由此二人发生争执,以致吵闹起来。恰在此时,一位认识崔振华的职员经过此地,告知警察说:“她是张继副馆长的太太,可以放她向东去。”
崔振华被放行后,大步走到整理皮货处的门口,正好遇到李宗侗工作完毕出来,余怒未息的她,顿时气冲牛斗地责怪李宗侗。李宗侗本是大少爷出身,脾气也不小,平白无故遭到崔振华一阵抢白,当然不高兴。尽管崔振华是他的长辈,但他也觉得咽不下这口气。他不仅不肯低头向崔振华赔小心,反而直接顶撞她。
最后,两人大吵起来。崔振华挟怒回家,一进门便叫丈夫张继向易培基告状,企图由易来惩处李宗侗,以解心头之恨。然而,易培基素知崔振华的秉性,认为她是个疯婆子,也知道张继是一个有惧内癖的懦夫,因而听说此事后便置之不理。他一不处分李宗侗,二不敷衍、照顾崔振华的面子。如此一来,崔振华不禁大为光火。于是,她开始暗中向故宫博物院职员搜集有关易、李二人“不轨”的材料,伺机报复。张继身为司法院副院长,本来就可以指使法官为所欲为,更何况检察署署长郑烈是他一手提拔的人,一向对他俯首帖耳,惟命是从,这使他更能够运用司法权力来得心应手地惩治易、李。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将故宫宝物南迁,分批装运至上海租界内贮存。在装运中,一次风声紧急,正进行加速抢运,该院职员萧襄沛要把一个凤冠装在箱内,箱小冠大,不能封盖。于是萧将冠上的珠子摘下,当场装入箱内,连同其他古物装满一箱,然后封钉。萧襄沛的这一做法,只是没有保存原冠的小错误,最多只能给以告诫或记过的行政处分。但郑烈却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件小事不放,借此给萧襄沛扣上了“破坏古物以伪换真”的大罪名,并指使检察院提起诉讼。
结果,萧襄沛被判处有期徒刑数年,并成为所谓易培基故宫盗宝案的替罪羊。张继、崔振华、郑烈借机在报上大吹特吹,说易培基指使萧襄沛盗宝,人赃俱获,已由苏州法院判罪,企图以此掩盖天下人耳目,遮盖捏造盗宝新闻的虚假。
善良的人们也许会问:面对张继、崔振华、郑烈等人的一再诬陷栽赃,易培基、李宗侗为什么不出面投案辩诉,通过法律途径揭露他们的罪行呢?因为李宗侗坚决反对这样做。其理由有两点:第一,他认为张继、崔振华、郑烈的目的在于打倒易培基和他自己,只要易培基辞去院长一职,他们的目的即已达到,由此便可安然无事。何必自投虎口,枉做囚犯?第二,他认为堂堂司法院副院长和检察署长狼狈为奸,栽赃枉法,这是政治问题。非到国民政府改革政治时,不可能肃清这股恶势力,使案情获得公正解决。投案反诉,没什么用处。
易培基听从了李宗侗的意见,辞去院长一职。但结果并没有像他们所想的那样,反而使张、崔、郑等人更加变本加厉,欲将他们二人置之死地而后快。不过,易培基也曾一再表示:再等几年,政局稍微好转,只要自己一息尚存,就必报此仇。但是,他的这一想法却直到临终前也未能实现。1937年10月,易培基因肺病加剧,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在上海的私人公寓中与世长辞。
据说,易培基在病重期间,甚至直到死之时,除了忧愤国难、心系民族安危外,另一件念念不忘的事情便是自己投案反诉,报仇伸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