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人娘亲被巧取豪夺后》
作者:未眠灯

简介:
黛黎万万没想到,只是一次普通的上学罢了,竟让她失去了相依为命的儿子。她整理好一切,来到校巴失事的江边,投入江中打算和家里的小朋友相聚。
本以为是结束,但再睁眼却来到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
周围古色古香,脂粉飘飘,莺燕低语,她仿佛身在待客的后院,一切都恍惚如梦中。
黛黎顺从预感往外逃,途中遇到一个似来此地做客的霸道男人,她使计摆脱了对方,未曾想那人竟直接向宅子的主人讨人。
后来黛黎才知道,她偶遇的男人居然是北地的无冕之皇,朝廷唯一一个凭军功跻身君侯之列的武将。
天下已乱,群雄并起,她来到了一个乱世。
*
九岁,是州州人生的第一条分界线。
九岁以前,他是妈妈的乖宝,是蜜罐里的糖豆,是红旗下的接班人。九岁以后,他是路边谁都能踩一脚的野草,是必须与恶狗争食才能活下来的贱骨头,更是别人手里一把指哪砍哪的血刀。
孤身在外,漂泊无依,他曾无数次回忆过母亲的笑靥和温暖,却没想过有朝一日他竟还能和母亲重逢!
只是……
看着母亲身边那揽着她腰的男人,他陷入沉默。
事情似乎变得相当复杂了。
精彩节选:
夜已深,许多屋舍早已熄了灯,房舍主人也早早梦周公去了,但某座阁院却是例外。
屋中很静,明明只余两道呼吸声,黛黎却好似听到隆隆作响的雷声,哦不,那不是春雷,是她几近从嗓子眼跳出来的心脏在呐喊。
男人倾压过来,黛黎下意识抬手抵在他胸膛上:“并非编应付之辞,是那事说来话长,妾方才想着如何长话短说。”
秦邵宗没顺势退开,但也没继续往前,他维持着俯视的姿态凝视着身下的女人。
黛黎没指望他能接话,努力挤眼泪开始半真半假地编故事:“妾有一幼子,前些日子被歹人拐了去。经查,他现今似乎身在这府中,故而妾才想了法子溜入府中寻子,中途碰见尊驾实乃意外。”
秦邵宗倒不意外她有孩子。
女子十五及笄,可出阁嫁人。今朝为促进人口增长,颁发了鼓励生育和减轻赋税等法令,其中有一则便是: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五算,即要交五倍的人头税钱。
因此,普通人家的女儿基本早婚。而受大环境影响,贵女哪怕再拖,也不过是晚一两年成婚。
“妾知尊驾贵不可言,也感激尊驾对妾的赏识,不过锦衣玉食虽令人眼热心动,但妾为人母,犬子于妾而言是心头肉。自决定生下他时,便想着爱护他长大,如何舍得他在外漂泊受苦?今日妾寻子心切,这才斗胆扯了虎皮当大旗。至于后续闹得阖府风雨,乃妾始料未及之事。妾心惊胆战,也自知愧对尊驾抬爱,所以无颜再回来。”
黛黎最初想装有苦衷是真,但说着说着,她想起死不见尸的儿子,忍不住红了眼眶也是真。
“至于尊驾说的负隅顽抗,此言差矣。”黛黎当然不肯承认:“当时妾疲惫至极,半昏半睡,又兼之夜黑风高,故而妾初醒时未能认出尊驾,只以为是梦里那个拐完犬子后、又想来拐妾的歹人,还望尊驾恕罪。”
顿了下,黛黎给他戴高帽:“尊驾能不计前嫌,仍高看妾一眼,妾高兴都来不及,又怎会将您往外推,毕竟尊驾光看一身气度便是天潢贵胄级别的人物。”
这番说辞,直接将他先前那句“是你自行出来,还是我抓你出来”归为她睡迷糊了,没听见;至于后面的挣扎,一口咬定是她看不清人,才未认出他。
总之刚刚是刚刚,现在是现在,现在她有眼识泰山了,刚刚那些事不做数。
话毕,黛黎听他哼笑了声,也不知他是信还是没信。她暗自抿了下唇,决心下一剂猛药。
黛黎面上早已不似初时慌张了,她红唇微微翘起,撑在男人胸膛上的手擦着黑袍往下,指尖划出一道并不激烈、但绝对能引起微痒的弧度:“妾不懂时政,不知尊驾具体身份,但听闻连蒋府君都唯尔马首是瞻,您定然是顶顶贵重的人物,想来命人寻一小童不过是信手捏来,不知尊驾能否帮妾这个小忙?”
白皙修长的手指勾上男人腰封,摸到了其上的首面形带钩,正欲将其拿下时,一只粗粝的大掌陡然将她握住。
他强势挤入她掌中,反包住她的手,将那柔软的掌心肆意揉搓着,从带着淡粉的指尖到手舟骨上端,每一寸都没放过,甚至连指缝都来回摸了个遍。
秦邵宗笑道:“寻一小儿有何难?待明日金乌露头后,我叫人去办。”
似乎有把火沿着手臂烧过来,叫黛黎后背颤栗,她忍下抽回右手的冲动,抬起左手轻轻勾住男人的颈脖:“犬子名叫秦宴州,五尺七高,半个月前妾曾受一道士指点给犬子剪了短发,他应该很好认。”
秦邵宗眼里划过一缕深思,“姓秦?”
黛黎心里打了个突。
“秦”这个姓氏算不上特别,毕竟在百家姓里。但她是知晓的,在某些时代,某姓氏有可能成为大姓,从而将某地牢牢占据。比如,江左孙氏,一门三雄;洛阳吕氏,三世四人等等……
“秦”姓,该不会那么巧是如今某地的大姓吧?
“你丈夫是何人?”他忽然转了话题。
黛黎心道“秦”果然是大姓,这一瞬,无数个念头浮现,但又迅速像被戳穿的气泡消失。
不行,根本编造不了。
她现今既不知身在地域与年号,也不知周边大环境,完全两眼一抹黑,无中生有的名门望族和水中月没区别,一探就散了。
黛黎像是心虚般移开目光,“他、他不过是无名白丁罢了,就算妾说了,尊驾也不识得。春宵一刻值千金,不如你我快快安寝吧,也好令妾明日早些见到犬子。”
她勾在秦邵宗颈上的左手用了些力,给了他个下压的信号。
秦邵宗神色难辨,叫人看不出他在想什么,忽而他轻笑了声,“好一句‘春宵一刻值千金’,那就如夫人所言,我们早些渡春宵。”
他原先箍在她腰侧的长臂收回,转而从她上衣与长裙间探了进去。
绕是之前做好心理准备,但这一刻黛黎还是忍不住僵了下。她感觉碰上她皮肤的并不是手,而是被烧得滚烫的砂纸,粗糙间带着难以忽视的热度,只是稍微滑动,就仿佛要烫掉人一块皮.肉。
这把烈火贴合着她的腰线、如蛇蜿蜒般迅速往上烧,黛黎眼睫不住微颤,薄薄的眼皮浮现出一层浅红,雪映桃花似的。
悬于上的黑影终于倾轧了下来,宛若雄伟的山岳将她完全覆盖。中间的距离彻底湮灭,对方如何的箭在弦上,大抵没有旁人比此刻的她更清晰了。
黛黎呼吸微滞,她仿佛闻到了硝烟与风沙糅合而成的味道,滚烫的气流穿过她的耳膜,落在她的耳尖、耳垂,带出少许醒目的红痕和激颤后,慢慢往下移。
不过……
“嗯?”秦邵宗撑起身。他对刚刚碰到的、质感类似铁的小东西很在意。
房中的烛芒熠熠,榻上女人腰带松散,直裾深衣外衫散开,露出里面同样松松垮垮的中衣,而在中衣底下,则是一片晃人眼的丰润。
白雪皑皑,峭壁高耸,钟灵毓秀得惊人。
和寻常的女郎不同,她没有穿帕腹。
不,不是没有穿。
秦邵宗看到了她中衣下隐隐露出来的一个烟紫色小角。
在他发出那声语气上扬的疑惑时,黛黎怔了下,最初没明白是哪里出问题扰乱了她的计划,直到秦邵宗将她翻过去。
本就松散的直裾深衣和中衣被男人更拉开了些,墨发如水淌在女郎洁白的背上,绮态婵娟,自生风流。
秦邵宗拨开她柔顺的长发,入目是一件样式有些奇特的小衣。
现今女郎的帕腹后方都有绑带,以一道或两道绳结固定在后背和后腰。但这件帕腹并无绑带,它流畅地贴合在女人的后背上,宛若一段未剪裁过的衣料,不过仔细看能瞧见这小衣中段内藏玄机。
黛黎趴于榻上,清晰地感受着那只大掌的移动,从肌肤相贴到被内衣隔开,紧接着是“啪”的一声微响。
她的内衣扣开了。
那时在西苑换衣裳,黛黎曾想过要不要从内到外全部换干净,后来到底没那么干。
一来是内衣不像裙子和深衣,不显山不露水的,哪会有人看见;二来是她不习惯、也不想穿别人穿过的贴身内衣。
结果计划赶不上变化,没想到对方竟搜府寻她,更没想到自己没能躲过去。
现代内衣排扣以铁制,铁随便用,废铁只值一两块钱一斤。但在冷兵器时代里,铁器等同兵器,是颠覆政权最不可或缺的力量。拿冶铁技术有大飞跃的汉朝来说,铁器依旧金贵得很,寻常百姓家有铁犁和铁锄等农具,却不见得会有铁锅。
而现在,这值钱玩意儿出现在了一个女人的贴身小衣里。
黛黎记得排扣和她的内衣同色,外表应该看不出是铁,她祈祷他认不出来。
“铁做的?“秦邵宗上手按了按。
黛黎:“……”
“夫人何处买的帕腹?”他问。
黛黎抱胸翻了个身,慢吞吞道:“在一个西域来的商人处,那行商说这小衣特别,还拍着胸口说唯有他那处有得卖,定不会和旁的女郎撞款,我听着新奇,便买了一件。”
说着,她又去勾他脖子,“尊驾莫要理会那些了,现今及时行乐才是正事,妾无比希望明日能早些见到犬子。”
秦邵宗没阻止她翻身,也像是瞬间忘了那个镶了铁的排扣,他顺着她的力道俯首,“安心,只要令郎在府中,哪怕他被藏在主人家的私库里,我都能将人带回。”
“我自是相信尊驾能力的。”黛黎柔声道,两人不再脸对着脸,她终于可以不再收敛脸上的异色。
熟悉的滚烫气流再次袭来,从颈侧往下,黛黎心里默数着时间的同时,手也向下探。她的指尖先碰到了他的腰,男人黑袍未除,而哪怕隔着外袍等物,她依旧能感觉到衣袍之下的肌理结实精壮,带着勃发的热度。
黛黎顿了顿,而后去解他的鞶带。
这个时代的鞶带和现代的腰带挺相似,有带钩有圆环。而在他的鞶带将将解开时,黛黎见差不多了,于是狠狠转了下左脚腕。
“尊驾,妾不大舒服,好像是……癸水要来了。”黛黎的手重新抵回他胸膛上,将人往外推。
秦邵宗的脸刷地黑了,他目露怀疑地打量身下女人,却见她咬着红唇,面色苍白,额上似隐隐还有冷汗。
表情可以伪装,但身体给出的反应没办法骗人。
黛黎带着忍痛的神情怯生生地问:“您明日还会派人帮妾寻子吗?”
榻上女人除了胸前一件歪斜的小衣,上身几近衣裳褪尽,她枕在如瀑的青丝上,带着旖旎粉调的雪肤有零星的红痕,仿佛是熟透的蜜桃沁出了水色。
秦邵宗太阳穴跳了跳,扣着她腰的手臂青筋毕现,像在极力忍耐着什么,他深吸一口气又重重吐出,最终直起身扣好自己被解了大半的鞶带,“我言出必行。”
留下这句,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间萦绕着幽香的厢房。
直至那道高大的身影彻底消失不见,黛黎才听见了心头大石落下的声音。
她成功了!
果然,古时的男人皆认为癸水是不洁之物,对此多有避忌,所以才出现了古时经期女性不得出入寺庙、不得碰祭品等事情。
和她想的一样,这种位高权重的强势男人非常傲气。哪怕他再急色,也不屑于去验她癸水的真假。
她用癸水避他几日,同时借他的手将这座府邸再搜一遍,随后寻个机会离开这里……
“君侯?”
莫延云被先前秦邵宗掳人那一幕冲击得有些厉害,兼之见月亮好不容易出来,他一时间无了睡意,干脆在院中赏月。
结果月没赏多久,他竟看到上峰从主屋出来了。
莫延云震惊难掩,又有点不为外人道也的担忧。
将那么一个活色生香的大美人从头吃到尾,再砸吧砸吧骨髓里的滋味,能干的事情太多了,要花的时间也绝对不少。然而现在一盏茶的功夫都不到,君侯居然出来了,难不成……
秦邵宗闻声望来,不知是不是他的错觉,莫延云觉得他上峰那双眼冒着绿光,和之前在北地草原看到的狩猎失败的饿狼一个样。
他下意识将目光往下移,飞快地瞄了眼。同为男人,他一眼便看出对方饱腹与否。
哦,原来刚刚不是他的错觉,君侯是真的没吃饱,算算时间,甚至可能没吃上嘴。
莫延云久经欢场,排除种种可能后,猜测“逢春”多半来癸水了,因此无法伺候。他深知此时男人都会极不舒爽,府中舞姬甚多,既然她难以为继,寻旁的美人伺候也行,何苦让君侯受那等委屈,于是道:“要不我去给您挑个美貌舞姬过来?”
秦邵宗:“可。”
莫延云领命去办,但才走开三四步,却又听见上峰改口——
“罢了。”
莫延云惊讶转身:“您这是为何?”
秦邵宗的声音暗哑非常,但语气平静了许多,“我有一计可让此行事半功倍,其中需要她参与,此时不宜有旁的女郎掺进来。”
“君侯,她可信吗?”莫延云对此十分怀疑。
以他对秦邵宗的了解,既然对方能说需要她参与,那“逢春”到时绝不止是一个存在感很低的镶边角色。临时找来的人不知根底,且此前她甚至还耍了君侯一把,当真能相信吗?
“她与蒋府无任何瓜葛。”秦邵宗淡淡道:“她有一幼子,名叫秦宴州,短发,五尺七高,可能在府中,你明日带人暗中去寻。另外,去查一查北地秦氏是否走失了个小孩,再查秦氏各家贵妇的动向。”
莫延云被这番话冲击得不轻,他脱口而出:“君侯,您怀疑‘逢春’是贵妇?这、这如何可能?”
妻凭夫贵。所谓贵妇,那必须是夫家显赫,甚至丈夫本人颇有建树,是英杰才俊。当然,这样的豪族向来强强联盟,妻子的母族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一言蔽之,贵妇出阁前是个千金,出阁后运道也好,夫家乃至丈夫本人都很争气。
秦邵宗斜睨了他一眼,不打算和他详细解释,“问天问地问那么多作甚?你是想着以后都尉干不了了,好去茶馆做百晓生赚银子?”
莫延云讷讷摇头说不是。
秦邵宗回首看身后的屋舍,眼中沉淀着深意。
寻常人家的妇人要干农活或洗衣做饭,时间久了,一双手定然会生茧。舞姬之流说白了也是为奴为婢,在无需伺候尊客时,也要自行干活。唯有那些被奴仆服侍着、被夫家好吃好喝供着的贵妇,才能十指不沾阳春水。
她的一双手除了右手中指内侧略有薄茧,其余柔软无比,身上肌肤细腻润滑,还带着某种似乎是花香的香气,是真正被精心娇养出来的。
再加上牛皮鞋,和那件带了零星小铁块的帕腹,她的夫家必然不俗。
“逢春”这个名字是假的,“菘蓝”也是假的,但秦邵宗莫名觉得她的寻子心切是真,所以“秦宴州”大概率不是假名。
她的夫家是秦氏,秦氏在北地是大族。但在他印象里,秦家的旁支里好像没有以惊人美貌闻名的贵妇。
难道她并非正室?
似乎不无可能。
若是正室,身旁怎能没有护卫与奴仆供其差遣。且旁支嫡子被掳,这等事他不可能没听到风声,而当家主母也不至于落魄到亲自到外头寻人……
思及此,秦邵宗添了一条吩咐:“除了贵妇外,育有子、甚得丈夫宠爱的宠姬也查一查。”
“唯。”
*
月落日升,东方既白,新的一日如约而至。武将晨练是基本,无人睡懒觉。
秦邵宗晨练回来,刚好见燕三从主屋里走出,后者见了他,解释道:“君侯,方才‘逢春’说不慎扭了脚,想讨瓶药油,我便给她送过去。”
秦邵宗“嗯”地应了声,说起其他:“你收收拾拾搬去和莫延云同住,将偏房空出来,午后去寻两个女婢过来。”
昨日还拒了蒋崇海的奴仆,今儿又主动索要,算得上朝令夕改了。但燕三没问为何,只是拱手领命。
昨晚秦邵宗离开后,黛黎自然不敢睡在主屋,她赶紧挪了个位,到旁边连着主屋、供伺候奴仆休憩的小偏房去。
偏房小是小了点,床窄是窄了些,但架不住安全,也比露天环境好多了,黛黎算是睡了个好觉。
心里记着事,翌日她也醒得早。睡醒后并不出去,而在房中静听,等到隔壁男人离开,她才向他下属讨了瓶药酒。
没想到才刚上药,他就回来了。
这是最好的待客阁院,屋舍座向和其内陈设皆是顶好的,连带着相连的小偏房也没有普通小偏房昏暗。
日光从窗牗照进来,落在他的身形上,勾出山体般雄峻的轮廓,哪怕现今是白日,那令人心惊的压迫感仅比夜间少些,并未消失。
黛黎刚调整好表情,就听他问:“崴脚了?何时的事?”
扭伤一事必不能发生在她暴露前,否则难保他能猜到昨夜她之所以难受,根本不是癸水作祟。
“昨夜尊驾离开后,妾心里忐忑,忧心不已,回偏房时不慎岔了神,一个没注意被门槛绊了下。”黛黎说着早就编好的借口。
秦邵宗目光往下移,她此时微盘着腿坐在榻上,鞋袜尽除,宽大的裙摆花瓣似的铺开,一只脚被裙摆完全盖住,正在上药的左脚露出小腿中段以下的部分,在这日光算不上非常亮堂的屋内,泛着羊脂玉似的白腻光泽,她抹了药油的脚腕处微微肿起,确实是伤了脚。
他的目光和主人一样侵略感十足,黛黎只觉小腿像被火烫了下,她下意识想将腿上卷起的裙摆放下来。
不过动作刚起,黛黎忽然想起什么,硬生生止住。
一个会主动勾着权贵,想与之共覆云雨的女人,绝对不会不喜这等目光。
“尊驾来寻妾,是否是犬子有消息了?”黛黎面露激动。
药酒开了盖,浓烈的味道萦绕满房,像一头不知饥饱的巨兽将女人身上的雅香吞没。作为一个沙场里打滚的武将,秦邵宗对各类药酒无比熟悉,却是第一回觉得今日这药味颇为碍事。
秦邵宗:“令郎暂无消息。”
黛黎垂下眼,面上失落难掩。
“时间尚早,晚些再看看。”用于安置奴仆的小房里物件少,唯有一桌一柜一椅罢了。受胡风文化入侵影响,椅是小胡椅,秦邵宗单手抄过胡椅置于榻前,大马金刀坐于其上,和榻上的黛黎面对面。
“夫人芳名?”他忽然问。
黛黎正要说话,又听他语气难辨地道:“什么逢春菘蓝之类的假名,夫人就不必说了。”
“……黛黎。远山黛的黛,黎明的黎。”黛黎这次本就没打算说谎,她还需在这里待几日,要是旁人叫她假名时她没反应过来,因此露了馅反倒不美。
秦邵宗定定看了她两息,才“嗯”了声作回应:“秦夫人……”
“妾不冠夫姓。”黛黎打断他。
秦邵宗眼中有幽光划过。
不冠夫姓的女郎有两种,其一是母族地位远远高于夫家,这类妇人比起夫家的姓氏,更喜欢旁人称呼她的本姓;其二是能随意转手赠与他人的姬妾和舞姬之流。前者是不屑,后者是不够格,有云泥之别。
黛氏,北地与中原都未有“黛”家的大族。
秦邵宗:“夫人似乎不是南康郡人士。”
黛黎笑叹道:“尊驾好眼力,妾的确不是本地人,来南康郡不过是因机缘巧合。”
他继续问:“夫人故乡何处?”
黛黎暗道不好,和许多电视剧演的不一样,她是直接从现代过来的,在这里无任何痕迹,相当于黑户。
不说,他定不肯罢休,说不准还会打破如今她好不容易维持的平衡。说么,但又该如何说……
万般思绪像被猫咪弄乱的毛线球,黛黎眼皮跳了两下,忽然福如心至:“交州,妾是南边交州的苍梧郡人士。”
古时的交通不发达,从南至北可不像现代那样只要短短几个小时。就算他决心刨根寻底,但一来一回至少几个月,等消息回来,她早不在南康郡了。
“交州苍梧郡?”秦邵宗长眉微扬:“交州距离此地少说也有三四千里,夫人何故背井离乡?”
黛黎拿出一套封建说辞:“自然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这人点头,显然对她这话很是赞同,但他的问话并不止于此:“夫人为何独自寻子,你丈夫呢?”
黛黎露出黯然伤神的神情:“不知尊驾问的是妾的哪一任丈夫?”
秦邵宗一顿,“你有几任丈夫?”
“妾前后有过五任夫君,刚好一只手能数得过来。”
黛黎似惆怅地叹了一声:“妾命途多舛,否则也不会因此从交州逐渐北上。其实昨夜妾欺瞒了尊驾,犬子的生父并非白丁,妾观他言行举止,多半是大宗族出身,不过他的具体身份妾也不知晓,只知他叫秦懿,字化鲤。他神出鬼没,归期不定,并不会经常待在妾和犬子身边。”
这是她昨晚辗转反侧好一番,才想出来的新说辞。
没办法,谁让她刚说完丈夫是白丁,转头就被他发现她内衣里有小铁块。寻常百姓的铁皆用在刀刃处,哪会这般奢侈。
丈夫是白丁这条路行不通,那就编个神秘权贵出来。古时男人虽能纳妾,但并非肆无忌惮,妾室数量会受到一定限制。
比如《独断》中有记载:天子一取十二女,象十二月,三夫人九嫔。诸侯一取九女,象九州岛,一妻八妾。卿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
说白了,明面上只能这么多,贪心不足如何是好?
那就养在外面,也因此有了外室。
黛黎思来想去,决定给自己换个身份,一个哪怕查也不那么好查,且明面上逻辑勉强能自洽的身份。
毕竟换夫婿都换习惯了,现任丈夫又时常不在身边,她对他无深厚感情可言,自然当新的高枝出现时,她会毫不犹豫地攀上去,更别说对方还答应为她寻子。
秦邵宗转了转扳指。
秦懿,秦化鲤。
秦家嫡支与旁支杰出的子弟中并无此人,是这个秦懿不够出众因此不被他得知,还是给的是假名?
假设是后者,那到底是“秦懿”自持身份,不愿走露风声,还是……
秦邵宗一瞬不瞬地看着面前女人,他棕色的眼在日光渐盈的室内更显得瞳色浅淡,像一把铮亮的、能划破一切假象的刀。
黛黎心慌难止,到底没忍住垂下眼睫避开他的目光。
他问:“你家住何处?”
黛黎听见了自己心跳加速的声音:“妾的夫婿甚是不喜妾抛头露面,也不喜妾与外人接触,故而寒舍在南康郡西边十余里、一处不显眼的山林里。对了,妾先前听闻府中人称呼尊驾为君侯,不知尊驾是何地的君侯?”
最后一句问得天真,却很符合一个对时政完全不了解的妇人的眼界。
太守是官称,前缀有地名,连在一起就是某地太守,管辖该地域。君侯听着也是官称,那前面应该也有个地名吧。
秦邵宗失笑说:“朝廷并无将管辖地与列候官职一并赐我。”
这话刚说完,就见她微不可见地拧了下细眉,好像有点担心,又好像有点懊悔。至于担心什么,自然是忧心做了赔本买卖,后悔轻易跟了他。
刚刚秦邵宗还笑她天真,现在嘴边弧度敛了:“我为夫人寻子,夫人是否该投桃报李?”
黛黎不知他怎的将话题拐到这上面来,难道是她方才演过了,激得他想在其他地方把威风找回来?
她顿时有些头皮发麻:“那是当然。犬子是妾的命,救命之恩没齿难忘,倘若君侯有用得着妾的地方,妾定不推辞,只是……”
说到这里,她抿了下唇,似难为情,“只是癸水不能行房,您能否等妾几日?”
这一刻的黛黎一颗心提到嗓子眼,生怕他来一句“无妨,不做到最后依旧有许多乐趣”,但或许他没那么不讲究,也或许他还念着她是个伤患,事情没黛黎想的那般糟糕。
秦邵宗:“并非行房。昨夜我在蒋府寻人,打的是寻找走失爱姬的旗号,蒋府君听闻后对此事颇为关心,后续可能会让他的妻室与你闲谈,夫人可知到时该如何应对?”
他虽问的是“到时”,但黛黎听出的可不仅仅是应付那位府君夫人,她闻琴弦而知雅意:“君侯放心,妾知晓该如何做,只是为防露馅,还请您给妾一些信息。”
“我领了三千玄骁骑从蔚州来,欲前往赢郡剿一李姓大盐枭,此番来南康郡不过是途径此地。”秦邵宗顺带给她讲了下盐枭李瓒的大概信息。她待在他身边多少会耳濡目染些,不可能对这李姓盐枭全然不知。
黛黎眼皮子跳了跳。
士兵在古代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电视剧和小说里动不动就是某某拥军百万,其实并不合理,又或者说水分惊人,因为哪怕是鼎盛的大唐,全国军队加起来都没那个数。
拿东汉初来说,举国军队不过是三十万左右,若能拥军十万,哪怕中间用老弱病残掺水掺了一半,都能算是一方大枭雄了。君不见,当初董卓只带了三千人马就镇住了中央军。
玄骁骑,这听着应该是骑兵。
古代的骑兵是国之重器,他居然带了三千在身旁,那没带出来的又有多少?
黛黎暗自抽了口凉气,她忽然无比清晰地认识到“君侯”这个称呼在他身上没任何水分,他绝对是从列候进阶来,用实打实的军功上位。
秦邵宗:“我姓秦,秦邵宗,字长庚,祖籍幽州渔阳。一个月前有人献美于上,遂你我相遇。你与伺候你的女婢在来程路上皆染了疾,她体弱没撑过去,你勉强过了险关,但因精神不佳,身体不适,故而昨日入府时待在马车中没露面。”
他上下打量她,眼里带了些笑意:“你头脑简单,性格善妒且骄纵,路上时常因餐食不精与我闹脾气,昨夜我被你闹得心烦,故意向蒋崇海讨要一个不存在的舞姬,并让属下将消息泄露给你,意在让你收敛些。但没想到适得其反,你勃然大怒后偷偷离了阁院,我为顾全自己的面子,只对外称爱姬在府中走失,同时紧锣密鼓地寻人。至于寻到你后,我如何服软,那便是你我关起门后的房中事了。”
黛黎心道原来他想让她配合演一出戏,她若有所思,“您想借妾之口,将这‘真正’的原因,和我们独处时的态度说给府君夫人听?”
秦邵宗笑道:“你倒不是个笨的。”
黛黎再次问他,“妾性格骄纵,骄纵到什么程度,您能否给个范围?”
“恃宠而骄,自然是越骄纵越好,上房揭瓦不在话下。”他如此说。
黛黎听他用似笑非笑的语气说着这种话,只觉后背起了一片鸡皮疙瘩。这一刻她好像身在丛林里,周围枝繁叶茂,而她身旁有一头以皮毛为保护色融入环境中、正对外面虎视眈眈的恶虎。
直到这时,黛黎终于想起昨夜偶遇两个女婢,有一人分明认出她,最后却视而不见的违和感在何处。
他和那蒋府君根本是面和心不和,双方都对对方提防有加,因此他那时要找她,府中奴仆很可能受上命而阳奉阴违。
黛黎沉思片刻,而后试探着说:“君侯,整个框架就按您说的,一些小细节妾能否自由发挥?”
秦邵宗同意了。
黛黎见他这时候好像挺好说话,于是继续道:“君侯和妾于一个月前相遇,那君侯帮妾寻子之事……”
“自然会在暗中进行。”秦邵宗见她失落垂眸,又加了句:“倘若蒋府中找不到人,便到外面找,只要令郎还在南康郡,哪怕藏在犄角里也能将他翻出来。”
“做戏做全套,不如您命人重新给妾做个新的传,到时妾将其在府君夫人面前显摆,好叫她深信不疑。”黛黎小声提议。
传,是百姓的身份证,上面有姓名和籍贯等信息。它既是非奴隶流民者之象征,也是凭证,可以说无传难行远路。
身为君侯的掌上珠,如何肯让自己继续沦为无传的姬妾奴婢之流。
秦邵宗:“可。”
黛黎不住露出笑容,刚要谢他,就听他来了句:“得了新传就这般开心?”
黛黎心头狂跳,当然不肯认:“君侯此言差矣,妾之所以高兴是因为彻底与您达成共识,寻回犬子也指日可待。您放心,一旦走出这个阁院,妾便是那个恃宠而骄的宠姬,绝不叫他们起半分怀疑。”
“不是自走出此地起,而是从今日午后开始,午后我让人寻两个蒋府的女婢来伺候你。”秦邵宗从胡椅上起身。
黛黎以为他说完要离开,正想口上送他两句,却见他并非转身,而是往前走了一步。
那张胡椅本就放在榻边一步之遥的位置,如今随着他这一迈步,两人近在咫尺,近到黛黎只需稍稍抬手,就能碰到他的黑袍。
男人俯身弯腰,一手圈过黛黎的腰,另一手从她膝盖下抄过,轻而易举将人抱起来。
黛黎心下一惊,本能将他鞶带上那一块衣裳揪得皱巴巴的。这人似乎天生火力旺盛得厉害,她侧挨着他胸膛的肩胛和被他抄手圈过的腿弯,都变得热烘烘的:“……君侯?”
“我已让他们腾出一间偏房,你住到那边去。”秦邵宗抱着人出了小房间。
黛黎垂眸,这倒也能理解,谁家被宠得无法无天的宠姬会住这等奴仆才住的小间。
他们出来时,恰好遇到将行囊移到隔壁屋的燕三,以及从外面回来的莫延云,两人见状皆是一愣。
“去寻个府医来。”秦邵宗留下一句后抱着人进了燕三先前的屋子。
莫延云看向燕三,“昨夜君侯与我说他有一计可事半功倍,还说其中需‘逢春’参与,难道计划已开始了?否则君侯何时这般纡尊降贵过。”
燕三一言不发地转身往外走。
“嗳,你作甚去?我和你说话呢。”莫延云不满。
燕三头也不回:“寻府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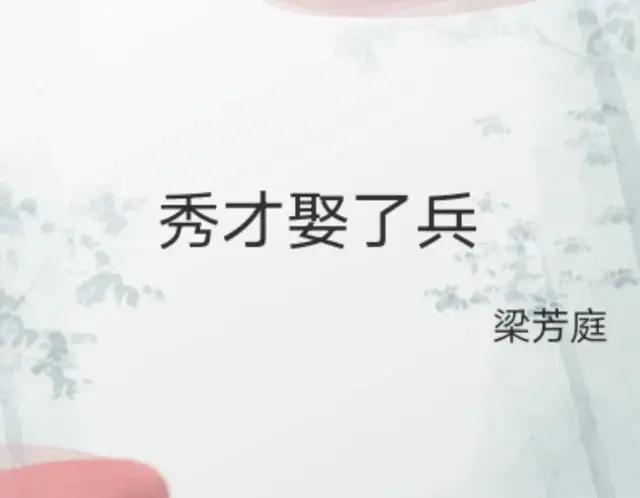






码,和看过之前的以前一篇母女穿越的文非常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