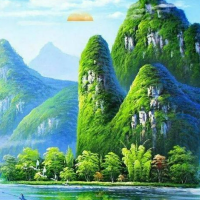在苏联期间,李敏曾多次向贺子珍表达,希望能有机会见到她的父亲毛泽东。然而,当她们抵达北京,真正面对毛主席时,李敏却显得有些拘谨,那声“爸爸”竟难以启齿。
贺子珍离世多年后,李敏在一次媒体访谈中回忆起童年的温馨片段。她提及:“周伯伯引领我见到父亲,他示意我称呼父亲,我起初难以启齿,不过最终还是叫出了那个称呼。”

【真是一个小娇娇】
新生儿最初识别的个体是谁?
是母亲打来的电话。
谁是世界上对女儿最为疼爱之人?
是母亲打来的电话。
在光明照耀的安宁地域,孩子们承载着国家的希望,如同国家的新芽,然而对娇娇而言,这些显得尤为难得。娇娇身处的环境,与那片充满希望的土地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那里,孩子们的笑容如同阳光般灿烂,他们是国家未来的基石,被寄予厚望,被细心呵护,如同精心培育的花朵。但对娇娇来说,这样的生活似乎遥不可及,仿佛是一种奢侈的幻想。尽管周围的世界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但对娇娇而言,那些关于未来、关于希望的描绘,都显得那么不真实。她所处的现实,与那片充满阳光与和平的土地有着天壤之别。在这里,每一份快乐、每一份希望,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去争取。
1936年冬季,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后不久,娇娇迎来了她的诞生。
在长征启程之前,贺子珍已经怀孕。在长征途中,她生下了一个女儿,但由于形势紧迫,她未能仔细端详孩子,便将其托付给他人。
当前,这个婴儿诞生于寒冷的土窑之中,且因贺子珍身体状况欠佳,孩子自诞生起就显得格外纤弱。邓颖超接过这幼小的生命,心疼地言道:“真是名副其实的娇弱宝贝。”
当毛主席听闻这个名字时,他果断决定:“就叫她小娇吧。”

贺子珍健康状况欠佳,乳汁分泌不足,因此为女儿娇娇找了一位乳母。自娇娇诞生以来,她多数时间在乳母家中度过,期间还不时由多位邻里乡亲轮流照看。这也使得娇娇日后常常提及,自己是在众人的关怀与抚养下成长的。
据她后来所知,周围的长辈们提及,在她刚度过满月不久,母亲便将她交由奶妈抚养,而自己则前往抗大求学。由于学业繁重,母亲每周仅能抽空回家探望她一次。
一年后,贺子珍心中始终挂念着要移除体内长征时遗留的弹片。然而,她身体状况不佳,难以自行完成此事。她多次向毛主席表达了这个愿望,但毛主席考虑到当前局势动荡,认为不是合适的时机,便告诉她需等待环境平稳后再作打算。
当年,贺子珍毅然决定告别延安,远赴莫斯科。
毛泽东主席因公务繁重,每日需处理众多事务,决定将女儿娇娇送往保育院,让她与保育院中的其他孩子共同成长。娇娇在保育院度过了数年的时光。

当她逐渐明白事理时,依稀能够回忆起,在托儿所的日子里,不仅有保育员负责她的日常起居,还有众多的小伙伴陪伴左右。每日夕阳西下之际,众多家长会陆续前来,将各自的孩子领回家中。
娇娇没有被任何人接走,但她表现得十分勇敢。与其他会哭着喊“我要爸爸”或“我要妈妈”的小朋友不同,她没有这样做。
娇娇自幼便听话且知理,个性较为文静内敛。
保育所位于延安周边,地处窑洞之中。步出窑洞,视野中展现的是连绵的山峦。每当其他孩子被家人接走后,娇娇便会独自坐在门边,凝视着西方天际的红霞,那景象宛如身着彩衣的鸟儿,让她感到十分有趣。
抗战时期,红军实行统一供给制度,毛泽东主席明确提出,娇娇应当与其他孩子一视同仁,不得享受任何特殊待遇。

毛主席通常在周末或工作较为轻松的时段探访娇娇。据延安时期的一些老同事后来回忆,由于毛主席公务缠身,难以抽身照料女儿,时常处于忙碌状态。
直至1940年,毛泽东得知贺子珍在苏联所生的孩子不幸去世后,决定派遣娇娇前往苏联,以陪伴并安慰贺子珍。
那些情况,娇娇并不了解,后来是由毛岸英向她叙述的。
自1927年与父亲分别后,毛岸英与毛岸青便未曾相见。母亲过世,兄弟俩在上海经历了一段漂泊的日子,直至1936年,他们被相关组织寻获,并立即被送往苏联。

抵达苏联后,贺子珍受到了毛岸英与毛岸青的热烈欢迎,他们频繁探望,并亲切地称呼她为“贺阿姨”。在那段日子里,贺子珍与这两个孩子之间逐渐建立起牢固的情感纽带。
《贺子珍在苏联的岁月》一文提及了她在苏联的一些经历,这些内容也散见于相关资料中。书中详细叙述了贺子珍在苏联的日子,讲述了她在异国他乡的生活片段。这些故事不仅展现了她的坚韧与毅力,也让人们窥见了她在那段特殊时期的心路历程。通过文字,我们仿佛能够穿越时光,感受到她在苏联的点点滴滴。贺子珍在苏联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但她始终保持着乐观与坚强。她面对困难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及她对生活的热爱与执着,都在这些故事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这些经历不仅塑造了她的个性,也让她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
据书记载,贺子珍于苏联产下婴儿后,召唤了毛岸英与毛岸青至其身旁,吩咐他们为这新降临的小兄弟取一个合适的名字。
毛岸青首先提议:“要不我们给他取个带有‘斯基’的名字,像是‘科瓦斯基’怎么样?”毛岸英摇了摇头,反驳道:“这不太合适,难道我们希望他将来成为一名司机吗?你看他长得多像父亲,将来应当从军,去对抗邪恶势力才对。”
毛岸英继承其父毛泽东的学识广博与口才出众,而毛岸青则在一旁腼腆地向贺子珍发问:“贺妈妈,您觉得,应该如何称呼才好?”
贺子珍在一旁听着他们的对话,忍俊不禁。经过一番思考,她决定让毛岸英来给孩子起名。毛岸英思考片刻后,提出了“廖瓦”这个名字。贺子珍听后,觉得十分合适。

【缺失父爱的童年】
娇娇前往苏联时,年龄约莫四岁,或许已不太记得国内的亲友,因此在苏联入读小学期间,当有同学询问她父亲身在何处时,她无法给出明确的回答。
一次交谈中,贺子珍对娇娇提及:“现今苏联的女孩已不同于我们过去,她们广泛涉猎各类素养的学习。你对学习钢琴感兴趣吗?”
娇娇出于一种探索的心态,答应了下来,但她真正的兴趣所在仍是绘画。某一时刻,贺子珍请求娇娇创作一幅画作,于是娇娇描绘了两位男孩,而在他们之间,站着一位扎有小辫子的小女孩。
毛岸青见状评论道:“在这三个人里,你年纪最小,为何把中间的人画得最大?”娇娇不服气地回应:“可实际上,我还是比你们小。”这时,贺子珍也忍不住露出了笑容。

直至某个时刻,毛岸英瞧见了娇娇手中的一张照片,照片中的人正是毛主席。他于是询问娇娇:“你可认识这张照片上的人?”娇娇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当然认识,老师曾向我们介绍过,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名叫毛泽东。”
毛岸英再次提及:“他仍旧是我们的父亲吗?”
娇娇难以接受这个事实,毕竟他是一位领袖人物,而自己仅仅是一名小学生,她难以想象他会是自己的父亲。
为了确认兄长所述的真实性,娇娇特地去找贺子珍求证。贺子珍从珍藏之处取出已久的《矛盾论》等著作,向娇娇说明,你的父亲其实是毛泽东,这些文章都是出自他之手。
小小的娇娇心中充满疑惑,为何与父亲相隔如此遥远?为了解开这些谜团,她回国的念头变得异常坚定。

1947年间,国内正经历着激烈的解放战争,贺子珍携女儿娇娇归国,并在尔滨安顿下来。东北局的成员特意前往迎接,其中林彪、李富春等人,重逢昔日的“贺同志”,心中充满了亲切之情。
娇娇回国后首要之事便是给毛主席寄去一封信,信中她用俄文,字迹略显稚嫩地写道:尊敬的毛主席,我有一个疑问,您是否是我的父亲?为何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从未有机会与您相见?
当毛主席接收到那封信时,心中充满了喜悦,随即指示秘书立即回复:娇娇,我是你的父亲,而你则是我的女儿,我十分挂念你,期盼你能早日归来团聚。
在告别之际,他特意补充了一句说明:“贺怡阿姨将会去接你。”

1949年春季,警卫员将娇娇护送至位于北京香山的双清别墅。初见毛主席时,她呆立了许久。周恩来在一旁,改用俄文向娇娇介绍:“这便是你的父亲,毛主席,快唤他父亲。”
见到娇娇嘴唇微动却难以发声的模样,毛泽东心生忧虑。周恩来开口道:“娇娇的中文水平尚待提高,但她一直在刻苦学习。”
娇娇酝酿许久后,终于喊出了那个称呼:“爹。”毛主席立刻将娇娇紧紧抱在怀里,愉快地对周恩来说:“原来我还有个会说外语的孩子。”
毛泽东主席给娇娇赋予了一个新称谓“李敏”。关于她为何随母姓李而非父姓毛,原因在于毛泽东在陕北活动期间曾使用化名李德胜。至于“敏”字的由来,推测是援引自《论语》中的理念“君子应当言语谨慎而行事敏捷”,这一命名思路似乎与李讷的名字灵感同源,均出自该句。

多年后,李敏回想起初次与父亲相识的场景,记忆依旧清晰。那时,她与父亲的初次相遇仿佛就在昨日。尽管时光流转,但那一刻的情景在她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她记得,与父亲相识的那一刻,心中的感觉异常鲜明,即便多年过去,那份初次相识的印象依然未曾淡去。
李敏回忆道,恰逢即将用餐之际,父亲提议一同外出就餐。席间,她注意到一道未曾见过的菜肴,便询问父亲这道菜的名字。父亲告诉她,那是田鸡。她接着追问田鸡为何物,父亲解释,田鸡指的是生活在田间的蛙类。
毛泽东的一个玩笑让娇娇展露了笑颜,娇娇未曾料到,父亲竟是如此平易近人,多年未曾感受到的父爱,在那一刻似乎全部涌现。

【受苦受难的母亲】
入学小学初期,李敏与李讷每逢周末便结伴归家,周一又一同返校。大部分时间,她们都在共同的居所中度过。按常理,年龄相仿的她们应当关系紧密,但由于是同父异母,初期相处并不顺畅。
毛主席在处理这件事时采取了妥善的方式。他告诉李讷,作为妹妹,应当听从姐姐的指导。同时,他也对李敏说,身为姐姐,需要有包容妹妹的气度。
可能正是因为受到了毛主席那样恰当的教育方式,李敏逐渐变得成熟起来,她开始领悟为何母亲长期居住在南方。

李敏心中总是牵挂着母亲,每逢寒暑假期,她都会乘坐交通工具前往南方探望贺子珍。而贺子珍也同样殷切地期待着李敏的每一次到访。
一位资深的精神病学专家指出,贺子珍或许患有忧郁性神经失调,其症状起始于她儿子不幸去世后,情绪持续低落。此外,她还表现出日益加重的猜疑倾向,心理状态难以承受接连的挫折。
李敏向父亲转述了所有情况,毛泽东听后平静地说:“我对你母亲的病情有所了解。”
因此,李敏渐渐理解了,为何每当父亲带去一封书信及些许食物时,贺子珍总是满心欢喜,心情格外愉悦。在那段时间里,贺子珍的状态颇为不错,她主动提出,希望能够前往江西居住。
贺子珍的出生地位于江西,从南昌前往永新,有便捷的铁路连接,行程仅需一天时间。
计算一下时间,自1928年告别永新起,至今已有31载。她最后一次返回永新,大约是在红军第三次攻下永新城之后。那时,贺子珍留在永新,协助县委开展工作,不久便随红四军前往赣南,以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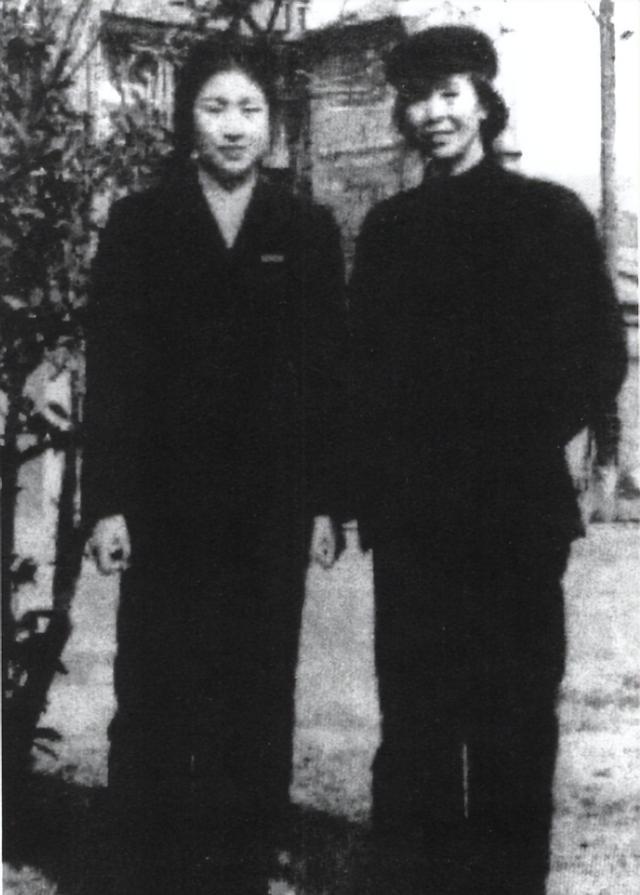
1959年夏季,于庐山举行的会议上,毛泽东偶然获悉贺子珍身处南昌的消息,随即作出部署,私下里与贺子珍进行了一次会面。
贺子珍在登山之际未曾预料到即将发生的情景,也未做任何心理准备。这次意外的重逢,几乎让她泪如雨下。事后她提及:“我当时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不停地掉眼泪。”
你为何当初选择离开?
错误在于我,是我缺乏理解。
我女儿即将步入婚姻殿堂,你是否曾见过她的未婚夫?
对于女儿的婚姻大事,你持赞成态度,我同样也表示支持。
这次偶遇成为了他们生命中的诀别,贺子珍自庐山归家后,精神状态似乎又遭受了新的波动。

庐山会议结束后,李敏在北京的中南海举办了婚礼仪式。与此同时,江西传来贺子珍病重的消息。李敏与丈夫的新婚蜜月不得不暂时搁置,她立刻赶往南昌,去照料病重的贺子珍。
那次,李敏在南昌陪伴了贺子珍一个多月时间,直至她身体状况有所改善,才返回北京。在告别之际,贺子珍对李敏说:“要照顾好你的父亲,还有小孔。”
李敏踏上火车后,凝视着窗外延展的风景,内心感受复杂。
之后,李敏有了两个孩子,毛主席吩咐将孩子们送到贺子珍处,以陪伴他们的外祖母。
贺子珍晚年时光,大部分是与两位孙子相伴度过,她享受着与孙子们相处的天伦之乐,生活颇为安逸。每日里,她陪伴孙子玩耍,教导他们,生活充满了温馨与满足。

【后记】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于上海华东医院去世,终年75岁。
数十年时光流转,孔东梅步入职业生涯后重返上海湖南路262号,并与该地员工共同拍照留念。她提及,往昔放学归家,因身高不足,需借助书包垫脚方能触及门铃按钮。
《忆伯父毛岸英》在我心中,伯父毛岸英是一位令人敬仰的长辈。他的一生,虽短暂却光辉,对我影响深远。伯父年少时便经历了许多风雨,但从未放弃过对理想的追求。他英勇无畏,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解放,毅然踏上了革命的征途。在战场上,他身先士卒,为战士们树立了榜样。伯父不仅是一位杰出的革命者,更是一位充满智慧的人。他善于思考,对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在闲暇时光,他常常与我们分享他的见解和经历,让我们受益匪浅。伯父对待生活严谨认真,从不马虎。他要求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全力以赴,不能半途而废。他的言传身教,让我们懂得了责任与担当。伯父的牺牲,让我们全家都沉浸在悲痛之中。但他为了国家和人民,英勇献身的精神,却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我们深知,伯父的生命虽然消逝,但他的精神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伯父毛岸英,是我永远的榜样。他的一生,都在为国家和人民奋斗。他的事迹和精神,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国家和民族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
李敏忆述北京科教节目《档案》片段:初遇父亲时,尽管感到有些拘谨,但仍鼓起勇气呼唤了他。